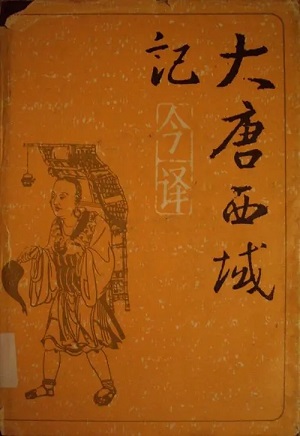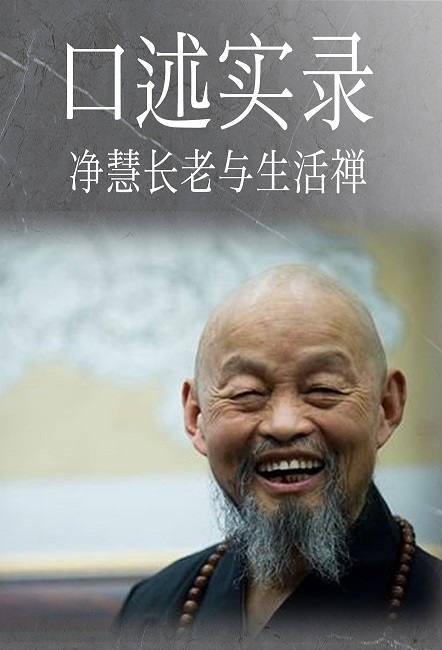第一章 初入中原
记得少年时代,老师就给我们讲闻鸡起舞的故事,说的就是祖逖和刘琨同在司州任主簿时,一大早,两人听到公鸡的叫声,就相约起身舞剑。老师的目的是激励我们发奋读书。长大了,听年长的朋友说,祖逖是定兴人,解放初期,他还见过祖村店村南的一块石碑,上书:“东晋祖逖故里”。这就又使我对祖逖产生了同乡的亲切感。我曾详细地翻阅了一些关于祖逖的历史记载,更令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对祖逖的一缕敬仰之情,把他流浪异乡近一千七百年的孤寂的灵魂带回故乡,我开始了寻找祖逖的中原之旅。
我先到芦洲。芦洲在太丘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永城市以西,谯国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亳州以东,旧日的芦洲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片土岗,土岗上长满了白杨和桐树,一棵棵挺立在冬日的阳光里。似乎在对我喊叫着:“我们就是祖逖的士卒!”只有一条浍河在土岗下静静地流着,河边长满了芦苇。广袤的豫东平原,平畴沃野。虽是冬日,树木已是光秃秃的脱下了盛装,在寒风中屹立着,但麦苗儿依然郁郁葱葱。中原是中国的粮仓,耕地里几乎全都种上了麦子,放眼看去,一片浓绿,生机盎然。
我驻足在浍河的河边上,耳边犹闻战鼓声和马蹄声。河岸上早已干枯的芦苇在风中瑟索,却仍然举着芦花的旗帜欢迎我,我想,所谓芦洲,是否就是芦花之洲的意思?我心头一热,奔到芦苇旁边,感到异常亲切。这毕竟是祖逖北伐的起点啊!这些芦花是代表祖逖迎接我的吗?
面对浍河的芦花,我捎来文天祥的一首诗,献给芦洲,回敬给我的同乡:“ 草宿披宵露,松餐立晚风。乱离嗟我在,艰苦有谁同。祖逖关河志,程婴社稷功。身谋百年事,宇宙浩舞穷。”
我采了一束芦花,珍藏起来,留作纪念。
晋元帝初年,祖逖的北伐军开到了芦洲。
渡江之后,祖逖在淮阴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在淮阴建造冶铁炉,打造兵器;抚慰农民,劝课农桑;招兵买马,组建队伍。他学习曹操的办法,部队实行屯田,他自己和家人也亲自下地耕种,抡锤打铁。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他有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和一支两千人的军队,觉得可以实施恢复中原的大计了。他决定向中原进发,开始北伐。他记得桓宣说过,他曾受元帝的委托,到谯国去说服那里的坞主张平和樊雅,虽然他们态度暧昧,总算是和朝廷的官员有过接触,口头上答应归顺朝廷,就先到谯国去吧。临行前,他安排他以前的管家李产留在淮阴,主持根据地的工作,在几年来的北伐准备过程中,他发现李产不仅可以诚实地管钱管物,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可以做他的萧何,他可以放心地把根据地和自己的家人交给李产了。他还把自己的弟弟祖约留下来帮助李产,不仅是因为哥哥临行前的警告,他也知道弟弟贪财渔色,不是一个能够担当大任的角色。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他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挥兵直指谯城。
根据事先掌握的情况,坞主张平割据在太丘,自称豫州刺史。樊雅盘踞在谯国,自任谯郡太守。两人和谢浮等十几股地方武装相互策应,拥兵数千人,形成了一个组织松散的军事同盟。一旦有事,可以互相支援。于是,祖逖决定进驻芦洲,在张平和樊雅之间揳上一个楔子,然后一个一个的对付。
北伐军在浍河边上扎营。中间是祖逖的大营,周围分别是嵩山营、明道营、淮阴营和北方营。嵩山营的士卒大都来自嵩山,虽然当时还没有少林寺,嵩山一带的习武之风已经蔚然,特别是晋廷大乱,外族入侵,嵩山人不甘受人蹂躏,为了自卫,练武的风气更盛,大多数人都有些拳脚棍棒功夫,听说祖逖在淮阴准备北伐,许多人就前来投奔,几年下来,竟达到四五百人,祖逖把他们编为一营,取名嵩山营,由武功出众,老成持重的冯铁带队。另一个是明道营,这些人分别来自各地占山为王的好汉们,为什么叫明道营?说来还挺有意思,这名字出自成语“鸡鸣狗盗”。说是战国时期的四君子之一孟尝君出使到秦国,被秦王扣留,他手下有一个门客会学狗叫,从秦王的库府里偷了一件狐皮袍子,献给秦王的妃子,才得以释放。到了函谷关,他的一个门客假装鸡叫,骗开了函谷关的城门,才逃回了齐国。于是就有了“鸡鸣狗盗”这个成语。卫策给祖逖出主意,取其鸡鸣狗盗中“鸣”和“盗”的谐音,加进了褒意的成份,就成了“明道”营,这些好汉们自己都带来了马匹,也就成了名符其实的骑兵营,这个营由曾是山大王的韩潜带领。这些人成份复杂,举止怪异,大体有横冲直撞型,横眉立目型,偷鸡摸狗型,满口脏话型,张牙舞爪型……这几年,祖逖没少在他们身上费力气,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用其所长,抑其所短,倒也大有成效,被祖逖制得服服贴贴,成了一支拉得出去的队伍。第三营叫淮阴营,是从淮阴当地的百姓中招募的,由卫策统领。卫策是晋初司空卫瓘的后代,卫瓘被楚王司马玮杀害之后,卫策随其父隐匿于故里,毕竟是名门之后,天资聪颖,熟读兵书,听说祖逖组织北伐,远道从故乡河东安邑前来投奔祖逖,倒也是祖逖的得力助手。第四营叫北方营,士兵都是追随祖逖多年的乡亲和部下,由督护董昭率领。
刚刚扎营完毕,就有一队人骑马过来,这些人衣冠不整,手中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有人扛枪,有人拿刀,斧钺钩叉,样样俱全。他们跳下马来,为首的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用脚踢踢帐蓬的拉绳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敢在这里安营扎寨!”卫策恰好在跟前,就说:“我们是豫州刺史祖逖的队伍,敢问在豫州地界上扎营有什么不对吗?”
这人“嘁”地一笑:“什么!豫州刺史?我们坞主才是豫州刺史,哪儿又来了一个豫州刺史?”
卫策说:“祖豫州可是朝廷封的,你们的什么刺史……”
祖逖听到报告,忙赶过来,向来人一拱手:“各位辛苦,在下豫州刺史祖逖,请问你们是……?”
来人上下打量了祖逖一眼:“你就是祖逖?”
嵩山营的士兵围拢过来,逼视着小头目说:“怎么说话呢!胆敢对刺史大人如此无礼,皮肤痒了?”说着欺身上来,就要动手。
祖逖喊道:“住手,来者是客,不得无礼!”待众人退下,又问,“请问各位在哪位坞主帐下吃粮?”
来人气焰收敛了一些:“我们是豫州刺史张平将军手下的士卒。”
“你们在哪儿驻扎?”
“太丘。”
“好,请捎信给你们张将军,我明天就会派人登门拜访。属下无礼,多有得罪,还望各位海涵。”
小头目对他的人马一挥手:“走!”众人上马,向东绝尘而去。
祖逖本来是要去联络张平的,既然人家找上门来了,总归是要联系的,派谁去呢?他想到了殷乂。从淮阴出发的时候,祖约听说要他留下,倒也没说什么,只对祖逖说:“哥哥,让殷乂跟你去吧,此人能说会道,也许对你有些用处,他跟随我多年,也好谋个前程。”祖逖对殷乂并不太了解,因为是弟弟举荐的,就把他留在身边。从淮阴一路走来,倒也领略了他嘴皮子上的功夫。祖逖把殷乂找来,向他交代了去游说张平的任务。殷乂听说要派他执行任务,只道是祖逖重用他,笑得合不拢嘴,他说:“没问题,朝廷大军压境,他还敢炸刺?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定会让他乖乖前来归顺。”
祖逖嘱咐他:“事关北伐大业,你要小心应对才是。”
殷乂说:“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殷乂在祖府几年,看惯了朝廷里太监宣旨的情形,他想,我是祖逖派去的,祖逖是朝廷封的豫州刺史,我就是代表朝廷的,我去张平那里,就是代表朝廷向他宣旨的。想到要代表朝廷去宣旨,他偷偷地笑了。
第二天,殷乂穿上长袍,戴上头巾,打扮整齐,看上去一表人才。骑上祖逖借给他的一匹马,出发了。祖逖还从嵩山营给他找了两个随从,一路保护他。出了芦洲,他想起太监传旨,手里总是拿着一柄拂尘,可是自己手里没有,这像什么!路过浍河的时候,看见河边的芦花开了,就跳下马来,采了一把芦花,用芦苇捆绑起来,试了试,说:“齐了。”然后 骑上马,学着太监的样子,把芦花放在臂弯里,美滋滋地向太丘方向走去。
当年的太丘不像今天的永城市,马路宽阔平整,高楼鳞次栉比。它座落在当今永城市的西北,殷乂走近太丘,注目观看,城墙倒还整齐,走进城里,街道狭窄骯脏,土坯房东倒西歪。张平的驻地在小城中央,门口有两个小卒子把守。殷乂通名报姓之后,一个卒子进去通报,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一脸麻子的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过来,向殷乂一抱拳:“在下张平。请问阁下光临敝处,有何见教?”
殷乂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把手里的芦花放在臂弯里,故意摇摇晃晃地走进门去,踏上台阶,转过身来,刚要说“张平接旨”,忽然想到自己手里没有圣旨,就拿捏着太监的声音,从嗓子里挤出话来:“你就是张平?”
张平本是太丘乡下的一个土霸王,乘天下大乱拉起一杆子人马,当上了草头王,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看殷乂的气势,不知道是什么来头,只得小心应付:“正是在下。”
殷乂把芦花拂尘向院子里指了一下,引得张平的下属们一阵窃笑。殷乂生气地说:“笑什么笑!瞧瞧,瞧瞧,偌大一个将军府,乱七八糟,没一点规矩,像个什么样子!”随即对张平说,“你进来吧。”说罢,转身率先走进屋里,张平也随着进去了。
殷乂坐下,撩了一下长袍下摆,清了清嗓子,才说道:“张平,”张平抬头看了看殷乂,自从他当上坞主以来,还没有人敢这样对他直呼其名,但他还不知道殷乂的来历,也只好忍气吞声了。殷乂接着说:“我……”想起朝廷传旨的太监都是自称“咱家”,于是连忙改口,“咱家是豫州刺史祖逖派来的。豫州刺史是朝廷封的,所以咱家也代表朝廷。”
张平听说他是祖逖派来的,底气顿时长了三分:“我才是豫州刺史,哪儿来的又一个豫州刺史?”
殷乂哼了一声:“祖逖的豫州刺史是朝廷封的,你呢?名不正言不顺!”
张平轻蔑地说:“朝廷,朝廷在哪儿?”
殷乂一时没明白张平的意思,随口答道:“朝廷在建业呀。”
“哼,建业那么远,他管得着我呀?”
殷乂也来了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眼里还有朝廷吗?还有朝廷的法度吗?”
张平哈哈大笑:“朝廷?法度?皇上都被人抢走杀了,哪儿还有朝廷?没有朝廷,哪儿来的法度?哈哈!”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这儿就是朝廷!”又指指自己的嘴,“这儿就是法度!回去告诉你们那个祖逖,要当刺史,就换个别的什么刺史当当,就是别当豫州刺史!”
殷乂甩了甩“拂尘”:“无法无天,气死我了!告诉你,限你三天时间,把队伍带到芦洲,接受改编,也许还能弄个小头目当当!咱家走了!”
走出门来,用“拂尘”指着刚才进去过的房子说:“瞧瞧,瞧瞧,这还算将军府?只配作马厩!”又指着院子里做饭的大锅,“这个,只配做猪狗食!”说完,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上了一句:“记住,三天,只给你三天,不然……”
“不然怎样?”对于殷乂的指手画脚,他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听到殷乂的威胁,逼问了一句。
“不然,大军压境,掩杀进来,小心你的脑袋!”
张平气昏了头,冷笑一声:“你摸摸‘咱家’的脑袋还有没有?”殷乂用手去摸自己的脑袋,张平手起刀落,殷乂的脑袋早已滚落在地,顺便搭上了摸脑袋的手。“拂尘”落在血迹上,染红了一把芦花。
跟随殷乂的两个士卒本想打斗一番,转念一想,双拳不敌四手,人家人多势众,占不了便宜,就悄悄溜回来了。
夜色很浓,天上没有月亮,繁星眨着神秘的眼睛。太丘城里狭窄的街道上,闪过一条黑影,黑影脚步奇快,眨眼间闪进了路旁的一家破败的酒馆。灯光下,可以看到这人中等身材,略显粗壮,脸上线条粗犷,像是雕刻出来的。一看就像是当地农民,身上也是一身当地农夫打扮:上身穿一件家织的粗布褐色的夹袄,左肩膀破了一个洞,右肩上搭着一个褡裢,腰间系一条褡包。客人和店小二招呼一声,在旯旮里找一张桌子坐下,小二上了酒菜退下,客人一边啜饮,一边看着酒馆里新贴上去的布告:“兹有太丘坞主张平,擅自诛杀官军使者,罪不容诛,限张平三日内到豫州刺史帐前自首,逾期不到,官军将进攻太丘,诛杀张平,有献张平首级者,论功行赏。 豫州刺史:祖逖。”客人边喝酒,边听着周围的酒客说话,话题也都是今天张平诛杀官军使者的事。
有人说:“该杀,谁让那使者那么嚣张呢。”
有人说:“嚣张是嚣张了点儿,可惹恼了祖豫州,城里的百姓可要倒霉了。”
“是啊,祖逖是吃素的吗?”
“应该有出头人平息一下。”
“我们谢浮头领下午就去找过坞主,劝他前去自首,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惹的祸不该让百姓承当。可坞主不去,说是豁出去拼个鱼死网破!”
“唉,太丘坞堡如果有谢头领当家,也不会弄成眼下这个局面。”
……
几个酒客散了,摇摇晃晃地走出酒馆。客人在桌子上留下一块银子,尾随出去。酒客各自向不同方向走了,客人追上其中一个酒客:“带我去见你们谢浮头领。”酒客刚要反抗,客人捏了捏他的肩膀,他就顺从地带着客人往前走了。
出了城,他们拐进一个村子,在一个高门楼下,酒客拍了拍门:“谢头领,有人找。”
房门开了。客人对酒客说:“多谢,没你的事了。”说完,纵身跳进院子里。谢浮走到大门前,问道:“谁呀?三更半夜的!”
不防身后说话了:“是啊,三更半夜的,打扰了。”谢浮扭头一看,一个人正在拱手向他致歉。
谢浮也是有一些功夫的,听到话音,立即欺身过来。客人闪身躲过,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他就知道来人的份量,只好说:“有话里面说。”带头向面屋里走去。
等客人坐下,谢浮问道:“阁下何人?”
客人拱手道:“在下豫州刺史祖逖帐下嵩山营头领冯铁。深夜打扰,还望恕罪。”
谢浮说:“阁下是为今天张平诛杀官军使者的事而来?”
“正是。听说谢头领为人正直,主持公道,在坞堡里声望很高,所以夤夜造方,想听听你的高见。”
“说实话,贵方使者也太跋扈了点儿。”
“是,使者的随从人员回去报告了。不过这不是祖豫州的意思。我们是想联络各地坞堡,共同抗击石勒,保护中原百姓。”
“是啊,同是朝廷子民,何必自相残杀!”
“那,这个张平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平只不过是太丘乡下的一个恶霸,会几下三脚猫的功夫,是谯郡太守樊雅的表弟,有这一层关系,就让他当上了太丘的坞主。”
“张平杀害官军使者,罪在不赥。”
“一定要杀吗?”
“一定要杀,否则,我们如何在中原落脚?”
“官军攻打太丘,必然会伤及百姓。”
“谢头领可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谢浮想了一会儿,说道:“这个不难,明天上午,我派人把张平的人头送过去。”
“好,一言为定!告辞。”冯铁向谢浮一拱手。谢浮把冯铁送出屋外,一转眼,冯铁已经没了踪影。
这天上午,殷乂的随行人员回到芦洲,把太丘发生的事情向祖逖汇报了。冯铁就气得拍了桌子:“无法无天!我带兵把去太丘拿下来!”
祖逖抬手止住了他:“我们刚到芦洲,不可轻易言战。我们的目标是石勒,攻打太丘,就会不可避免地伤及百姓,再说,真的要攻打太丘,樊雅必然会来援救,谯城、太丘有十几股地方武装,数千兵力,我们能不能打得过,还是个未定之数,就是侥幸取胜,也要消耗兵力,我们是来北伐的,不能拼兵力。我们只要张平的人头。张平一定要杀,不杀张平,我们就没法在中原站住脚。”
冯铁说:“这也容易,今晚我潜入太丘,把张平的人头取回来。”
卫策说:“这也不行。白天张平杀了殷乂,晚上张平丢了脑袋,太丘的军民肯定会把矛头指向我们,再团结、争取他们,可就难了。”
祖逖说:“对,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内部找到合适的人选……”
“对,”卫策说,“最好以豫州刺史的名义贴出布告,只杀张平,其余不问,这样可以分化他们。”
冯铁说:“好,晚上我到太丘城里打探情况,再想办法。”
第二天,谢浮果然派人把张平的人头送到芦洲,还送来张平的一匹坐骑,说是张平从石勒的部下桃豹手中偷来的,是西域名马。祖逖上眼看去,这匹马浑身紫红色,没有一根杂毛,鬃毛如瀑,两眼如炬,四蹄如柱,知道这是汗血宝马,他高兴地请来人向谢浮致谢。来人还转达谢浮的话,欢迎祖逖亲临太丘。下午,祖逖去了太丘,把太丘的兵马交给了谢浮指挥,任命他为太丘县令,约定共同抗拒石勒,保卫中原,保护百姓。他还特地叮嘱谢浮,杀了张平,樊雅可能出兵报复,要他做好准备,守卫太丘。谢浮点头称是。
由于当时的交通设施和通讯条件的限制,虽然两地相隔不过数十里路,张平被杀的消息,第二天早晨才传到谯城。
在樊雅的官邸里,樊雅听到下属的报告,立刻怒发冲冠,把一盏茶碗摔到地上,拿起身边的一把钢刀,挥舞着喊道:“好你祖逖,胆敢杀我的人,我要让你血债血偿!参军,马上集合队伍,攻打太丘!”
他的参军听到喊声,赶忙走进来:“将军暂息雷霆之怒。”
“我‘息’得了吗?这个祖逖,欺人太甚,到了我的地盘,动辄杀人,太不把我谯城放在眼里了!”
“是,是欺人太甚,但要想报仇,还得从长计议。你想,祖逖手下有两千多人,再加上太丘的降卒,不下三四千人,仅凭谯城这点儿人马,我们有多少胜算?”
“我就豁出去跟他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拼完了呢?仇还报不报了?你的谯郡太守还当不当了?”
樊雅听了,“唉”了一声,跌坐在椅子上:“你说,怎么办?”
“马上联络周边的坞主们,我们只有集中优势兵力,才有取胜的把握。”
“好,你马上派人去传令,令坞主们倾巢出动,全力以赴。午时出发,进攻太丘,我要让祖逖知道我樊雅不会任人宰割!”
参军领命去了。樊雅坐在椅子上。此时,他稍稍平静了一些,刚才发怒的时候,气得五官挪位,看上去既丑陋又凶恶,此刻平息了,倒还配得上他名字上那个“雅”字,只是戾气犹存。他本是一个读书人,但晋朝是士族社会,他的家族不是名门士族,书读得再多,也没有走上仕途的机会,他郁郁不得志,于是乘战乱之机,投笔从戎,拉起一支人马,耳濡目染,还学了几套拳脚刀剑功夫,以他的聪明才智当上了坞主,又自封了一个谯郡太守,过过官瘾。本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说不定还能在中原树起一杆旗帜。可恨祖逖一来就砍了他一只手臂,他能不怒气冲天吗?
樊雅的号召力不可谓不强,午时之前,果然集合了三四千人,午时准时出发,骑兵在前,步卒在后,浩浩荡荡,直奔太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