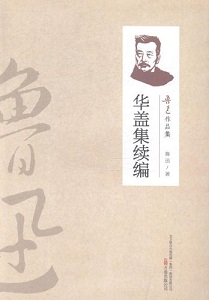队伍走到浍河,浍河水不深,骑兵稍一加鞭,就冲过去了,步卒涉水过河,速度就慢了,刚过了一半,骑兵早已经没了踪影。这时,忽然从河边的芦苇丛中涌出一队人马,好像天兵降临,冲向樊雅的步兵,举刀就砍,举棍就打,步卒毫无防备,仓促应战,不多时就处于劣势。没有过河的人急忙后退,这里,从土岗上的树林里又冲出一队人马,旋风般向他们逼过来,腿快的,跑了,腿慢的,顿时就成了刀下之鬼。樊雅的步兵四散奔逃,退回谯城去了。再说樊雅的骑兵还没跑到太丘,被一支骑兵迎面堵截,这支骑兵没有固定的打法,或直劈马头,或蹬里藏身,专砍马腿,或躲过迎面砍来的马刀,绕到身后,去砍马的臀部,战马一惊,猛然窜去,把骑手摔下马来,然后回转身来再取落马骑手的人头。这些人,好像专门和樊雅的骑兵捉迷藏。双方正在胶着之际,从太丘城里冲出一彪人马,这队人手提长刀,身穿铠甲,专砍樊雅骑兵的马腿,杀了一阵,樊雅的骑兵料不能取胜,唿啸一声,退出战斗,原路返回,在浍河边上,又被河两岸的步兵冲杀一阵,打得七零八落,狼狈而逃。
战斗结束以后,祖逖命谢浮请当地百姓来帮助部队打扫战场,收葬遗骸,并吩咐伙夫准备酒菜犒赏战士,庆祝首战告捷。
谢浮过来请示:“是只收葬我方士卒遗骨,还是全部?”
祖逖说:“当然是全部。对方士卒也是晋朝子民,他们只是受人驱使,来和我们作对,怎能让他们弃尸荒野?归葬之后,我还要祭奠他们!”
谢浮答应一声去了。
一旁的百姓互相递了个眼色,点点头,有人还翘起大拇指说:“真是仁义之师啊!”
祭奠完双方死难的士卒,天已经黑了好一阵子,士兵们在浍河里洗了手,围在饭桌前等待开宴,祖逖说:“不忙,等一等,先要犒赏有功将士。”
韩潜说:“天这么晚了,明天再说吧。”
祖逖说:“不,赏不逾日嘛!”
初战大捷,又得到了犒赏,人们尽情欢笑,吃喝,祖逖也非常高兴,频频和卫策、冯铁、韩潜、董昭以及战士们碰杯,他还特地把谢浮拉到自己身边,待之亲如兄弟。他喝得脸上有点儿红了。
大家正在欢笑,畅饮,一个放哨的士卒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敌人摸上来了!
祖逖听了,当即下令,“各营头领带领部下分头出击,不要慌乱!”说着拔剑就要向外冲。
董昭喊道:“北方营的士兵,随我保护刺史大人!”
董昭的话刚一落音,樊雅已经冲向祖逖,董昭抢先迎住,樊雅接了董昭几剑,放过董昭,驱身直指祖逖。招数狠辣,一副拼命的架式。祖逖一边招架,一边摘下腰间的葫芦,拔下塞子,喝了两口酒。
祖逖边打边说道:“兄弟,何必如此拼命?我们谈谈如何?”
“谈什么?先还我兄弟的性命!”他不再说话,一招狠似一招,直想取祖逖性命。
董昭刚要上手,祖逖说:“你在一边看着,也好学几招剑法。”
祖逖看樊雅剑法不精,又不想杀他,就慢慢和他玩下去。
好一会儿,冯铁跑过来,和董昭说了句什么,董昭上前替下祖逖,冯铁把祖逖拉到一旁,对他说:“对方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人快支撑不住了。”
祖逖问:“他们有多少人?”
“不下三四千人。”
祖逖想了想说:“撤。”
冯铁说:“往哪儿撤?淮阴?”
“不,撤回淮阴,让淮阴的百姓怎么看我们?往南撤。”
冯铁说:“你带他们先撤,我和嵩山营断后。”
祖逖说:“撤退的时候,我在前边?你去换下董昭,让北方营和淮阴营先走,嵩山营和明道营断后,轮番撤退。”还是在淮阴练兵的时候,祖逖和将士们创造了一个轮番撤退的战术,如果单纯撤退,最后的部队肯定是被动挨打,为了安全撤退,减少伤亡,最后的部队边打边撤,前边的部队在道路两旁预先埋伏,等自己的部队走过去之后,从两边向敌人的先头部队发起攻击,然后,边打边撤。轮番向敌人的追击部队攻击,这样,既减少了部队的伤亡,又阻滞了敌人的追击,还可以杀伤一部分敌人。祖逖他们就这样边打边撤,边撤边打,到天亮,对方只有少数部队跟在他们后面,祖逖决定不再和他们周旋,加快速度,脱离接触,他和冯铁断后。对方见他们不再边打边撤,放大了胆子,一直追上来,紧紧咬住不放,还不断地向他们放箭。他们好像看出了祖逖是这支部队的首领,一支冷箭射向祖逖,正中祖逖的大腿。冯铁见祖逖受伤,命令嵩山营停止撤退,回头向敌人的追击部队杀过去。追击部队的人数并不多,只是欺负他们败退,才大着胆子追上来,等到嵩山营回来和他们拼命,他们也并不经打,不一会儿就灰溜溜地逃跑了。祖逖包扎好伤口,问了一下路人,已经临近淮南。
祖逖进驻淮南。
韩潜垂头丧气地说:“唉,他娘的,出师不利,头一仗就让人给赶出来了。”
冯铁说:“头三脚难踢。”
祖祖逖笑了笑:“胜败乃兵家常事。”
说笑归说笑,祖逖的心里也很沮丧,出兵以来,先是殷乂被杀,而后是头一仗就败北,初战不利,这令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然而他不能轻易认输,这不是他的性格,好容易争得了元帝的同意,好容易组织起一支队伍,怎能轻言放弃?他要收拾起心情,收拾起信心,在失败中挣扎,站起来和他的战友们继续开创北伐大业!是的,在困难的时候,就需要挣扎!他一边疗伤,一边谋划今后的行动。
当时晋朝还没有在淮南设置官员,淮南由合肥的官府代管。祖逖派人去淮阴叫他的内弟许柳前来暂摄淮南太守,在淮南开辟另一个根据地。许柳来了,祖逖的伤也基本好了。祖逖命令部队:“继续北上,兵围谯城!”
卫策说:“行吗?”
祖逖说:“这次我们围谯城,打援兵,让樊雅和城外坞主的地方武装拧不成一股绳。”
韩潜说:“走,非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祖逖兵围谯城已经三个多月了,一直没有攻下来。说来这谯城也确实太坚固了,城墙用砖砌成,两丈多高,像冯铁这样的高手勉强能够爬上去,而樊雅又婴城固守,组织得非常严密,不时派出小股部队搔扰祖逖的军营。有时还派人深夜出城,去联络周边的坞主们,时不时跑来突击一下,打完就走,虽然赶不走你,给你添些乱,惹得你心绪不宁也是好的。祖逖虽然没有拿下谯城,却对樊雅越来越感兴趣了,这人虽说剑法不精,但却有些谋略,如果能争取过来,倒也是个有用的人才。他决定慢慢地和他耗,耗得他弹尽粮绝,自动出来投降。可是三个多月过去了,樊雅还没有出来投降的迹象。祖逖这边有李产源源不断地运送给养,不愁粮饷,可是快到年关了,城里的百姓怎么过年呢?祖逖做了两手准备,一是派人去找桓宣,桓宣曾劝说过樊雅,要他归顺朝廷,樊雅也表面上答应过,让桓宣再进谯城,说服樊雅,也许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是派人去联络远近的坞主,请他们帮助攻打谯城,虽然附近的坞主受樊雅的辖制,不得不为他摇旗助阵,远处的坞主们未必全都死心塌地得罪朝廷。无论如何,年前一定要拿下谯城。
最先到来的是浚仪坞主陈川派来的一支五百人的队伍,领兵的是个魁梧憨厚的汉子,名叫李头。他进帐后拱手对祖逖施礼:“参见刺史大人,浚仪坞主陈川派我前来支援将军,将军有何差遣,李头随时听候命令。”祖逖还礼的当儿,李头看见了冯铁,马上哈哈一笑:“师傅,你也在呀!好几年不见,想死徒儿了!”立即跑过去向冯铁跪拜。
祖逖问道:“你们认识?”
冯铁说:“李头在嵩山跟我学过几年武功。”说着扶起李头。
祖逖高兴地说:“你们师徒在战地相见,也算是一段佳话,你们好好聊聊。”
冯铁问李头:“你怎么跟了陈川?”
“我家在浚仪黄河边上,经常受到石勒军队的搔扰,为了保家,就近投奔了陈川。”
冯铁又问:“你的那个小媳妇还好吗?”
“挺好的。谢师傅挂记。”
祖逖开玩笑地说:“怎么,你这个师傅连徒弟的家眷也认识啊?”
冯铁笑着说:“他们小两口一块在嵩山跟我学武功。”
祖逖“噢”了一声说:“原来如此。”
冯铁问:“她在家还是跟你在一块?”
“她跟我在军队里,这次因为是临时支援,坞主就没让她来。”
一个士卒进来报告:“启禀将军,又有一小股兵马攻来了。”
冯铁问:“有多少人?”
“四五百人。”
李头说:“这么几个卒子,不劳师傅动手,我来跟他们玩玩。请师傅观阵。”
说着,向祖逖一拱手,算是请命。李头走出帐外,拔剑出鞘,大喊一声:“弟兄们,跟我来!”
祖逖和冯铁也跟出来观战。
双方混战中,李头高大的身影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他的士兵也如猛虎下山,威猛异常。冯铁看罢多时,高兴地说:“这小子,还行!”
祖逖没有听见冯铁的话,他也在细心地观察李头的一招一式,心里纳闷:“他的剑招怎么这么熟悉?和我的剑法如出一辙。可我的剑法是和刘琨在司州自创的一套剑法,只有我和刘琨会使,莫非他是向刘琨学的?……”
不一会儿,敌军退了,李头凯旋而归。
祖逖上前慰问:“李将军辛苦了。”
李头一笑:“打这几个小娄罗,小菜一碟。”
祖逖看看冯铁说:“果然名师出高徒。”冯铁笑而不答。
祖逖又问李头:“你的剑法也是跟你师傅学的吗?”
李头赧然,冯铁却哈哈大笑。
祖逖一头雾水:“怎么回事?”
冯铁止住笑说:“他的剑法是他的小媳妇教的。”
祖逖也笑了:“是吗?”祖逖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只能到此为止,他不好再往下问了。
桓宣仍旧是一身文官打扮,骑一匹白马,带两个随从,直奔谯城东门而去。
士卒通报之后,樊雅亲自出来迎接。谯郡太守樊雅的官邸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门,高大的门楼两边雄踞着两头石狮子,威严、雄壮、气派。门前有拴马桩、上马石,桓宣把马交给随从,随从把马系在拴马桩上,在樊雅的陪同下拾级而上,迈上七级台阶,是两扇朱红木门,门上钉满了铜钉,闪着高贵的黄色毫光。院子里方砖铺地,冬日里花木凋零,只有一丛修竹显示着勃勃生机。正房雕梁画栋,四根柱子全都漆成红色。樊雅把桓宣让进客厅,客厅里靠北墙是一张条案,条案上的掸瓶里插着几尾雉鸡翎。条案前是一张八仙桌,两旁各有一把太师椅。樊雅让桓宣坐了客位,自己坐在主位上。桓宣的随从则由士卒引到厢房里由下人招待。
上茶以后,樊雅一笑,问道:“参军别来无恙!今天,是哪阵风把参军吹到谯城来了?”
桓宣一笑:“南风。是皇上派我来求见阁下的。”
“求见不敢。皇上怎么会知道我这么一个无名之辈?”
“怎么不知道?你在谯城弄出这么大动静,天下还有谁不知道?”
“参军是祖逖请来做说客的吗?”
“不,是皇上派我来做说客的。”
“我又不是朝廷的臣子,皇上跟我有什么关系?”
“谯城难道不是朝廷的土地吗?”
“从前是,如今朝廷把谯城丢了。北边的石勒时不时地来谯城搔扰一番,朝廷管过我们吗?”
“朝廷这不是派祖逖来管了吗?”
“他来管什么?一脚踏上谯城的土地,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杀人。”
“那是因为张平擅杀官军的使者。”
“那是因为官军的使者出言不逊。”
“使者出言不逊是事实,但那不是祖逖的本意。”
“他的本意是什么?”
“他是奉皇上之命,联络中原各地的坞主,共同抵御石勒。这和你们起兵的本意不是一致的吗?你赌一时之气,贸然出兵,这不正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吗?”
樊雅说:“好,我们先不必争了,你远来是客,我们又是同乡,我先略尽同乡之谊,为你洗尘吧。”说着,拍了拍手。
一个下人进来。樊雅问:“准备好了吗?”
下人点点头。樊雅站起身来,对桓宣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率先向后面走去。
穿过正房后门,又是一进院子,院子后面是樊雅的花厅。进了花厅,一股热气朴面而来。花厅很大,里面摆满了一盆盆的芍药,一朵朵硕大如盘的芍药花儿灼然怒放,桓宣惊呆了,他知道,谯城是芍药之乡,可也只是在春天开放,这个樊雅,竟然让芍药反季节开放,看来,这家伙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人。
樊雅说:“刚才,你是朝廷派来的人,是公事。现在你是我的同乡,我为你接风洗尘,热的话,把外衣脱了,随意一点。”
桓宣脱了外衣坐下。樊雅拍了拍手,顿时,像变戏法似的,一桌丰盛的酒菜摆上了餐桌。桓宣说:“太客气了。”
樊雅笑笑说:“同乡故旧,你又是千里迢迢从建业赶来,使寒舍蓬荜生辉!自然应该盛情款待。”说着又拍了拍手,顿时,丝竹绕耳,八名长裙曳地的舞伎从里间飘出来,在芍药花间翩翩起舞。
下人给两人斟满了酒,樊雅举杯:“请!”
舞伎边舞边唱,唱的竟是曹操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桓宣说:“看来樊兄对我们这位前朝老乡情有独钟啊。”
樊雅说:“人生一世,如果能像曹孟德那样,成为一代枭雄,也就不枉此生了。来,喝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要成为一代枭雄,关键是要运筹得当。”
“当然,像我们的另一位同乡华佗,苦读医书,练就一身绝技,到头来还不是像虫子一样被人捏死。”
“所以你弃文从武,拉起一支队伍。”
“是啊,乱世出英雄,谁不想能像曹孟德那样,成就一番大业。”
“知道你想成就一番大业,所以我才说要运筹得当。”
“如何运筹?”
“成就大业之人,要懂得谋略,知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
“依靠谁?”
“上靠朝廷,下靠民众。”
“团结谁?”
“一切有志恢复中原之士。”
“也包括祖逖吗?”
“当然。还有中原各地的坞主。你看,祖逖能号令那么多坞主包围谯城,可见他比你懂得谋略。”
“可他杀了我的人,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大概忘了咱们另外一位同乡老子的话:上善若水。说一句逆耳之言,动辄赌气的人很难成就大业。”
“既然僵持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就先赌一把输赢。他把谯城围了三个多月了,也没奈何得了我。”
桓宣一笑:“你以为祖逖奈何不得你?他那是惺惺相惜,他很欣赏你。你知道城外有多少兵马?祖逖的人马,加上各地坞主的兵力,大约有七八千人,要想攻破谯城,还不是易如反掌?另外,皇上还派琅琊王司马裒率领三万人前来助战,我想已经起程了。你能支持多久呢?”
“那又能怎样?我谯城不还是固若金汤吗?”
“我知道你为何如此从容镇定。”
樊雅一愣,笑了:“也只有你知道。但我有办法。”
桓宣也一笑:“我知道你的办法。”
樊雅又一拍手,忽隆隆一阵响,舞伎们和一盆盆的芍药都不见了,眼前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樊雅扭头问桓宣:“我的办法如何?”
桓宣微微一笑:“不错,但你不敢。”
“怎么不敢?”
“我带来的一千兵马,已经把守住当年曹操地下运兵通道的所有出口,你杀了我,你出不去了,你的粮饷也进不来了,你只有困死谯城。而且你杀了朝廷大臣,也就把自己的活路堵住了,只能落得比张平更惨的下场。该怎么办,你自己选择。”
樊雅拍拍手,两边的地板合上了。“那就先听听你的高见?”
“你别无选择,归顺朝廷,投降祖逖。不仅保住了谯城,保住了你的人马,保住了你的家业,你还可以得到重用,忠勋可立,富贵可保,因为祖逖不像你那么心胸狭隘,他很欣赏你。否则,朝廷从南面攻击你,石勒从北面窥伺你,你将无立锥之地。何去何从,你自己掂量。”
樊雅跌坐在太师椅上,长叹一声:“唉,既生瑜,何生亮!”
桓宣微微一笑:“和祖逖比起来,你既不是周瑜,也不是诸葛亮。你只是一个草头王。”
当天下午,樊雅自缚出降,祖逖进据谯城。仍命樊雅暂摄谯城军事事务。太子司马裒率领的军队,走到半路,听说樊雅已经投降,就撤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