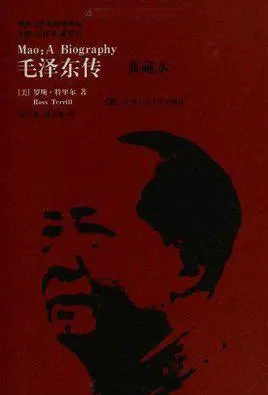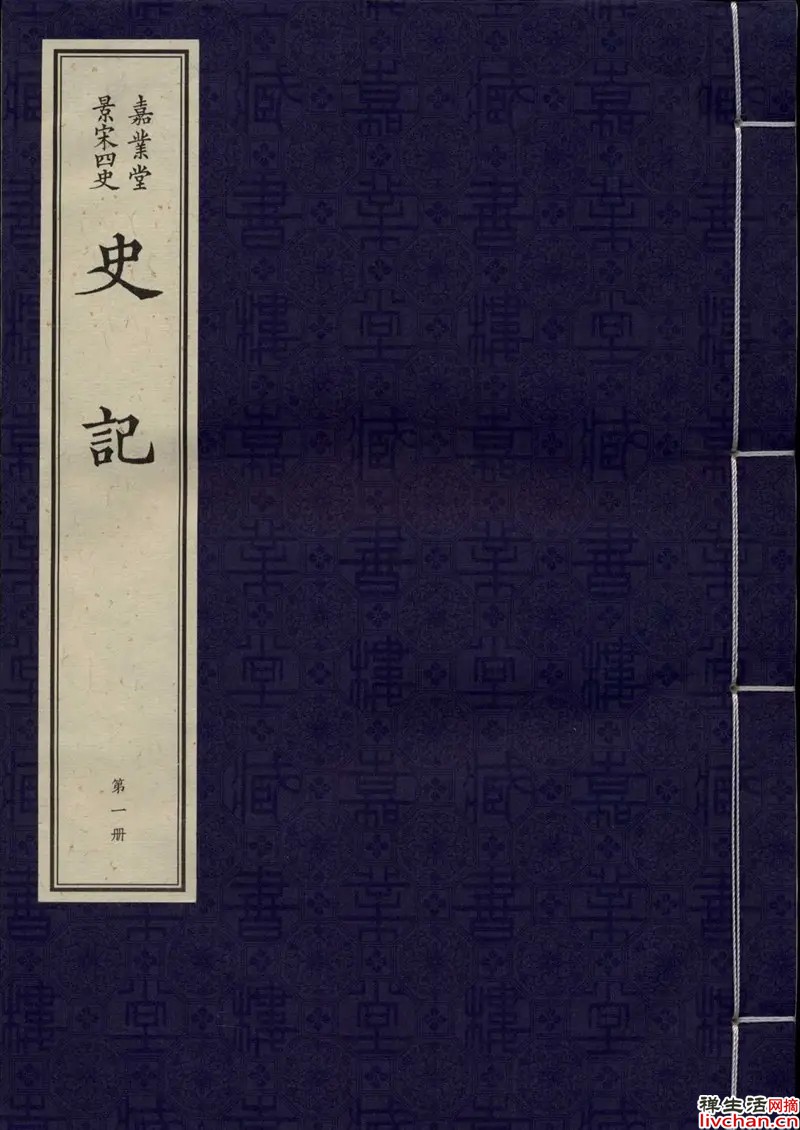村外飘来叮��凿声。 山脚将立起一座高大的石雕。
打凿的是一个胡子花白的老石匠和他的两个虎背熊腰的嫩徒弟。老石匠只让徒弟干粗凿的活儿,精雕细作的活儿从不让徒弟沾边。他认为徒弟只配干粗活。
石雕是老头的秘密构图。他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创造它。不同凡响。
徒弟们从来不知道师傅要怎么干。
徒弟凿好石雕脚的粗模,便恭恭敬敬地喊:“师傅,脚模凿好了,往下怎么干?”
老石匠颤抖抖爬上木梯, 叮��叮��一阵好凿, 那石雕的脚便出来了。石脚造型逼真,果然漂亮。
徒弟凿好石雕手的粗模,又恭恭敬敬地喊:“师傅,手模凿好了,往下怎么干?”
老石匠又叮��叮��好一阵, 石雕的手便出来了。 石手透尽鲜灵之气,栩栩如生。
石雕只剩一双眼睛没凿了。
老头却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倒下了。衰老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永远带走了一个没完工的秘密。
啊,眼睛! 石雕的眼睛!
面对老石匠弃下的残作,两位徒弟茫然不知所措。
大徒弟爬上木梯, 叮��叮��试着敲了几下, 二徒弟直摇着头喊 :“不对不对,这眼睛哪能凿得这么大!师傅要在,准不会这样凿。”
二徒弟爬上木梯,也刚敲了两下,大徒弟又在下边挥手喊 :“不行不行,这眼睛也凿得太小了。师傅会这样凿吗?”
眼睛,一个难解的谜。
两个徒弟开始争吵,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决定永久保留这座没有眼睛的石雕,各自分手,另筑炉灶。他们还约定,四十年后再回此地,届时各凿一座石雕,看谁能更完美地凿出师傅没凿完的眼睛。
山上的枝头冒了四十次芽。两个徒弟回来了。他们各自在那座没眼睛的石雕旁立起两座石块,一般高大。
他们都有了花白的胡子,并且各都带了两个徒弟。他们活脱脱继承了老石匠的怪脾性,不让徒弟干细凿活儿。
他们都憋着劲儿要较量一场。
石脚凿出来了。像师傅凿的一样逼真。
石手凿出来了。像师傅凿的一样透尽鲜灵气儿。
最后是眼睛……
当两座石雕都完工的时候,他俩不约而同地惊呆了:两座石雕的眼睛竟然一模一样,并且是那样的熟悉——
那是老石匠的眼睛。一点不错。
那座没有眼睛的石雕幽幽注视着他们。青苔无声地盖满它的风化的躯体。
选自《精短小说报》1988年第7期
【赏析】
《眼睛》是一篇关于艺术的小说。因为“眼睛” 一词作为一种意象,很多时候象征着“艺术的生命”。眼睛相当于文学理论中的 “神韵”,诗有“诗眼”,文有“文眼”,所谓点睛之笔. 这篇小说便整个儿是一篇形象化的艺术理解,是一篇关于点睛之笔——“眼睛”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小说。
因为那老石匠在一个伟大的时刻倒下去了,永远地倒下了。一座石雕,脚被雕得逼真,手被雕得鲜灵;老石匠闭上了双眼,留下了石雕上那双象征着活的生命的眼睛没有雕成。两个打下手的徒弟怎么也不能继续完成这双眼睛,这是老石匠留下的,也是小说设下的基础悬念。
然而小说并不想成为“遗憾的艺术”,老石匠的遗憾在四十年后得到了补偿。当两个徒弟又相约来到那件未完成的雕像下,各人又各立起了一座石雕,完工之后,两人石雕的眼睛竟然一模一样,“那是老石匠的眼睛,一点不错”。小说省略了两徒弟四十年来的艰苦磨炼和沧桑经历,却用这最后的一模一样的“眼睛” 证明了艺术的锤炼与老石匠精神生命对他们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当艺术的“眼睛”成功地睁开来,老石匠的生命得到了延续。
这是一种对艺术创造的简明生动的理解。而作为艺术品的小说,首先让我们感兴趣的却是它的双重的循环式的结构。这结构是一种内在的艺术。
其实当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两徒弟终于完成了艺术的“眼睛”的创造,都获得了“老石匠的眼睛”——完成了那一“点睛之笔”时,正是这篇小说本身的艺术“点睛之笔”。这篇小说中关于石雕艺术的故事情节与这篇小说本身的艺术结构形成了一个重合和一个循环,仿佛是一条互相缠绕的 “怪圈”:关于艺术的故事的表现本身就是艺术,而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为了说明关于艺术创造的过程(故事)。这种结构和叙述使我们想起民间文学中的循环故事原型,这篇小说的师徒故事的叙事方式也确有民间故事的神韵遗风。而且,这种结构还使我们想起了当代伟大的画家埃舍尔那永恒循环的绘画构图,以及哥德尔定理、巴赫的音乐——那条“永恒的金带” (参见《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我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