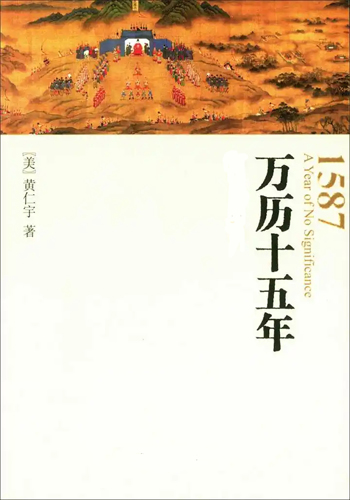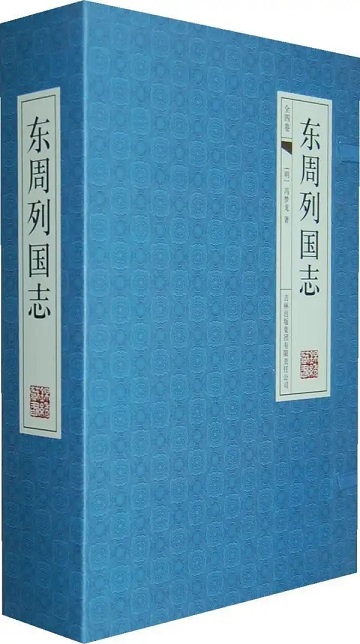乾隆在祭奠班弟和额容安的《双烈诗》末尾写到,“临奠例双忠,惜哉泪涌流”,“我岂为彼哉,长歌旌乃休”。大和卓回到乌什,和霍集斯会合,阿克苏、乌什的白山派信徒已经纠集到五千多人。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不可能形成战斗力。黑山派教徒同样是一群拿着镰刀砍人的农民,看上去气势汹汹,也是一群跳脚的菜鸟,半斤对八两。但白山派后面,有留守在乌什和阿克苏的一千多准噶尔正规军,有班弟派来督战的三百名八旗军,这两砣石头压称,武力值就不一样了。黑山派教徒还没有到阿克苏地界,就被迎面而来的白山派势力打败,一路溃逃到叶尔羌。
黑山派首领玉素甫以为革命就是比比拳头大小,没想到真刀真枪地拼命,受了惊吓,暴病而死。喀什的玉素甫死了,叶尔羌的牙合甫接任黑山派总首领。牙合甫是一个著名经师和学者,在新疆伊斯兰教史上的地位很高。据说,白山派围困叶尔羌的时候,白山派和卓波罗尼敦给黑山派和卓牙合甫写过一封信,大讲白山派教义,劝他放下武器,弃暗投明。牙合甫写了一封回信,把白山派辩驳得体无完肤。在这场书信辩论战中,牙合甫大获全胜。波罗尼敦恼羞成怒,下令攻城,黑山派叛徒打开城门,白山派几乎没费什么力气,轻松占领叶尔羌。
黑山派和卓家族在叶尔羌被俘虏,怎么处置的,没有记录,多数人从此再没有了下落。牙合甫有一个独生儿子,叫纳扎尔,战乱后出逃到今天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他是黑山派确定的、活下来的后裔,他和他的家人再没有参与过后来的南疆暴乱。白山派夺取了南疆政权,北疆的太上皇准噶尔突然诈尸,阿睦而撒纳在伊犁叛乱,波罗尼敦的弟弟小和卓霍集占也参与进去。阿睦尔撒纳给波罗尼敦派来信使,要求他率领白山派教众赴北疆聚合,一起围攻清军。
卫拉特蒙古的两个反贼,罗布藏丹津和阿睦尔撒纳,都是蒙古人中走出来的吴三桂和汪精卫,他们为清王朝带路,消灭掉自己部族的当家人,企图给清朝当个儿皇帝,却不料清朝的帝王们早已经准备好了变天帐,铁了心要给蒙古人改换中央帝国的字号,两个带路党的目的都没有达到,前赴后继走上了反叛的不归路。波罗尼敦对伊犁的情况无从判断。波罗尼敦在伊犁见到阿睦尔撒纳的时候,阿睦尔撒纳还是班弟帐下的清朝平准北路军左副将军,怎么就反了?他的弟弟霍集占又怎么卷进这场反叛中?波罗尼敦一脸蒙圈,不敢贸然下注,他把跟随监军的清朝八旗军软禁起来,好吃好喝招待着,反复向八旗军统领托伦泰说明,这是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的命令。
波罗尼敦虚与委蛇的观望态度,为后来的南疆之乱留下了空间。
不久后,策楞和玉保率领清朝平叛大军,以雷霆之势攻入伊犁,霍集占从特克斯出逃,阿睦尔撒纳叛军迅速崩盘。如此变化莫测的形势,连清朝平叛大军都搞不清霍集占到底是黑是白、站在哪个阵营了。霍占集逃到叶尔羌,大和卓波罗尼敦当着八旗军的面,杀掉阿睦尔撒纳派来的信使,将托伦泰和三百名八旗军官兵释放。白山派的表现让清政府产生误判,以为白山派已经归附清朝,南疆不会再有大的问题,坐等大小和卓前来觐见,接受册封。大小和卓叛乱初期,并非白山派公开举旗,造清朝的反,而是当事双方都出现了错误的政治判断。
大小和卓的反叛理由,和黑山派玉素甫叔侄三人如出一辙。南疆的和卓们大半辈子被准噶尔人圈禁在伊犁,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哪有什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他们以为清王朝屠龙之怒,主要针对北疆的准噶尔人,中原王朝对天山以南地区不会有兴趣,表态站队结束,南疆从此就是他们的地盘。
他们哪里知道,康雍乾祖孙三代,个个都是血脉偾张的政治家,满清入关以后,反反复复向汉人们表白,他们是中华民族天选的正统皇权。以正溯自居的王朝,可以割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巴尔喀什湖地区,但昆仑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线,除非彻底灭国,底线牢不可破。
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他的怀里揣着一个十全武功的账本,每天早晨起来,都会手指蘸着唾沫,一页一页翻看一遍账本。大和卓波罗尼敦在伊犁的时候,曾经提出要去北京觐见皇帝。阿睦尔撒纳叛乱前,小和卓霍集占也恳切请求要去北京觐见,并且把自己最心爱的小老婆送到北京,觐献给乾隆皇帝。大和卓离开伊犁去北京的路上,被班弟拦下来,打发到南疆出差。
班弟答应他们,南疆的黑山派叛乱平定以后,立刻护送大小和卓去北京觐见皇帝。谁会想到,放出去的鸽子再也飞不回来了呢!这时候,北疆领军人物已经是清朝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名将兆惠。兆惠对南疆事务也不了解,按照清朝规矩,白山派想要当好南疆的掌门人,应该送来一封言辞恳切的请降书,然后到北京出一趟皇差,接受乾隆皇帝的觐见和册封,把西藏喇嘛们的套路走上一遍,这才符合大清国礼制。
兆惠在伊犁苦苦等待,花儿谢了,眼睛绿了,南疆毫无音讯。
《清实录》记载,小和卓霍集占极力劝阻他的哥哥大和卓波罗尼敦归附清朝。
霍集占说,“甫免为厄鲁特(准噶尔)役使,今若投诚,又当纳贡。不若自长一方,种地守城,足为捍御”。我们给准噶尔人当了几辈子的孙子,如果归附清朝,还是当孙子的命,还要缴税纳贡。不如我们占据南疆,种好地,养好兵,和他们对着干。波罗尼敦不同意霍集占的意见,“从前受辱于厄鲁特,非大国(清)兵力,安能复归故土?恩不可负,即兵力亦断不能抗”。我们过去被准噶尔人奴役,如果不是天朝上国出兵征伐,我们怎么能回到自己的故土?天恩不能辜负,再说我们也干不过啊!霍集占执意要和清朝决裂,大和卓波罗尼敦最后一次规劝弟弟,“我兄弟自祖父三世,俱被准噶尔囚禁。荷蒙天恩释放,仍为回部头目,受恩深重。若尔有负天朝,任尔自为,我必不能听从”。
意思是,要反你自己反,我不跟着你趟这个浑水。
这是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叛乱分子交代的供词,不一定可信。但总体来说,大小和卓叛乱,由小和卓霍集占带头挑起,各方证据都能对应这一事实。叛乱初期,清军一直把大和卓波罗尼敦作为争取对象,但波罗尼敦已经被白山派信徒们裹挟,在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的双重逼迫下,他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兆惠是清朝军事将领中的一个奇葩,笔帖式入仕,早年一直干文书的活。平定大小金川的时候,才转入军职,长期负责粮草筹划,天生一双打算盘的手,平准战争前期被调到巴里坤前线负责后勤工作。阿睦尔撒纳叛乱,班弟自杀殉难,兆惠挽起袖子要求上战场杀人,被授予定边右副将军,随军进驻伊犁,一代战神就此诞生,成为准噶尔灭族当仁不让的刽子手。大和卓波罗尼敦返回南疆后失去音讯,小和卓霍集占又跑了,派到南疆的清军将领托伦泰还没有回来。
清军不了解南疆情况,从南疆回来的准噶尔人也说不清楚南疆情况。兆惠找到从拜城过来给准噶尔当人质的噶岱默特,请他出于对维吾尔人的了解,分析南疆,到底什么风向?噶岱默特判断,白山派很大概率要反叛,他们以为清王朝对南疆地区兴趣不大。噶岱默特建议兆惠,把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乌什、阿克苏、拜城、库车、库尔勒这些地区先控制下来,立足观望,进退有余。
如果大小和卓前来归降,清军顺势接应,把南疆拥入怀抱。如果大小和卓有反叛之心,清军随时可以举兵南下,扫平叛乱。兆惠听从噶岱默特建议,派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阿敏道率一百索伦兵,派投降过来的准噶尔宰桑锡克锡尔格率两千准噶尔兵,翻越天山,前去接管南疆东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派去南疆的这两个军事主官,各有各的来头,阿敏道是蒙古名将阿吉斯的儿子,锡克锡尔格是准噶尔末代汗王达瓦齐的宰桑,相当于中原王朝过去的宰相。
阿睦尔撒纳带领清军灭掉准噶尔汗国,锡克锡尔格投降清军,反过来成了围剿阿睦尔撒纳叛匪的排头兵,满世界追杀阿睦尔撒纳。兆惠认为,南疆过去是准噶尔人的领地,准噶尔汗国已经不在了,清军收复南疆地区顺理成章,不需要动武。兆惠甚至给两个军头交代,如果大小和卓要造反,不要伤害他们,直接抓起来,押到北京去觐见皇帝,牛不喝水强按头。南下清军出发不久,班弟派到南疆的托伦泰领着三百名八旗军突然回来,向兆惠汇报了大小和卓诛杀阿睦尔撒纳信使等等情况。
这瞬息万象的变化,让兆惠彻底迷糊了,大小和卓好像没有反叛的意思啊?兆惠怀疑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时候,天山以北地区再度叛乱,这一次的乱,铺天盖地。在南疆,小和卓霍集占坚持要和清廷决裂,白山派信徒们被打了鸡血,呜哩哇啦靠拢在霍占集一边,大和卓波罗尼敦被完全架空。
霍集占掌控了南疆权力,腾笼换鸟,把与清军关系密切的乌什白山派首领霍集斯调换到和田,把阿克苏白山派首领、霍集斯的哥哥阿不都瓦哈甫调换到叶尔羌。白山派血洗黑山派,南疆各地黑山派长老被捕杀,叶尔羌黑山派麻扎被灌入泥土封埋,南疆最大的黑山派长老、库车的鄂对和卓逃入深山躲藏起来。霍集占紧锣密鼓控制权力,做反叛准备的时候,从伊犁南下的清朝接管军队抵达库车。这是一个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位置像个鸡肋,闹事却总是冲在前面。霍集斯的儿子呼岱巴尔氐恰好在库车留守,他命令白山派教众封闭城门,拒绝清军进入库车。清实录记载,呼岱巴尔氐“诡称因畏惧清军中的准噶尔兵,不敢归降”。而实际情况是,呼岱巴尔氐已经收到他老爹的秘密口信,小和卓霍集占利令智昏,很可能要对清军动手。
霍集斯是那个时代白山派头脑最清醒的长老,他知道反叛必定是自寻死路,他从和田派人到库车,给呼岱巴尔氐传信,告诫儿子,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清军不理解呼岱巴尔氐的怪异举动,坚持要进城。跟随清军南下的拜城维吾尔首领噶岱默特也感觉到形势异常,他通过当地维吾尔人得到消息,北线的乌什、阿克苏、库车等地区已经被霍集占势力控制,小和卓霍集占很可能发动叛乱。他劝告清军主帅阿敏道,返回伊犁,请大部队过来控制局面。
阿敏道不信这个邪,在这位蒙古悍将眼里,南疆不过是一群举着砍土曼气势汹汹叫喊的农民,狼一样的准噶尔人都被他们灭了,一群农民能闹出多大事?阿敏道豪言壮语地说,“吾招抚回众,惟期于国有济,何暇他虑?”阿敏道率领一百索伦兵进入库车,噶岱默特则坚持不进城,说服锡克锡尔格,跟随准噶尔军返回伊犁,请求援兵。这时候,北疆已经大乱,狼烟再起,遍地烽火,兆惠自顾不暇,再也腾不出手来解决南疆的事了。
喀尔喀蒙古部落首领青衮扎布首先造反,清政府从平准前线抽调一万二千将士前往喀尔喀草原平叛。准噶尔部落的两个头领噶勒藏多尔济和巴雅尔,再度率部攻占伊犁,大魔王阿睦尔撒纳趁机返回博尔塔拉。兆惠经历了他一生中最惊险、也最闪光的一次地狱绝杀,率领二千二百名八旗军孤军奋战,从伊犁成功突围出来,千里奔赴巴里坤。兆惠被准噶尔叛军围追堵截在特讷格尔(阜康),两千多八旗军和一万多准噶尔人苦战一个多月,不分昼夜的搏杀,兆惠的战马活活累死,兆惠带领队伍一直坚持到巴里坤援军到达。清军主力在阿尔泰山以东的喀尔喀地区,兆惠大军撤退到巴里坤。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北疆,已经没有了清朝的军事力量。被打成烂泥的阿睦尔撒纳不再是准噶尔部落认可的首领,叛乱以后的准噶尔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
小和卓霍集占在伊犁长大,耳目和眼线众多,北疆沦陷的消息传到南疆,霍集占下定决心,抓住这个窗口期,举旗反叛。以当时的局势而论,霍集占的判断也没有错,他认为清军已经被驱赶出北疆,就算准噶尔人以后还能捏合到一起,经过清军几十年打击,已经失去继续控制南疆能力。阿敏道率领索伦兵城进后,被全部缴械软禁。阿敏道被拘禁在库车的几个月里,清朝政府想尽各种办法营救,乾隆皇帝甚至派人给霍集占下达谕旨,要求他无条件放人。
霍集占叛乱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远在和田的霍集斯敏锐意识到,霍集占如果举旗反叛,必定要杀害阿敏道,向清政府和白山派教徒公开宣示分裂决心。霍集斯再次派人给库车的儿子送信,想方设法,安排阿敏道跑路。呼岱巴尔氐接到老爹的指示,悄悄把武器发还阿敏道和索伦兵,安排他们连夜出逃。库车城大门紧闭,清军杀死三十多个白山派教徒,夺门出城。霍集占闻讯,命令库车白山派叛党骑马追杀,步行跑路的一百名索伦兵,被三百多维吾尔骑匪围攻砍杀,全部死难。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阿敏道被抓获,押回库车。
1757年(乾隆二十三年)三月,阿敏道在库车被斩杀。当时的霍集占人在哪里,没有确切记录,但处死阿敏道的命令是由霍集占发布的。这一事件,标志着大小和卓与清朝决裂,南疆新一轮叛乱正式开始。
当年六月,清政府调集满洲、索伦、蒙古、察哈尔、吉林等地八旗军,再度出征准噶尔。中路军由定边将军衮扎布统率,北路军由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统率,兵分两路,杀回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沙俄境内。北疆局势稍有稳定,南疆传来消息,大小和卓叛乱,阿敏道在库车被杀。成衮扎布和兆惠联名上书,提出平定南疆建议,兆惠请求前往南疆,镇压叛乱。乾隆下旨斥责,“闻回人霍集占等扰乱,戕害副都统阿敏道,俟大兵至伊犁,即前往回城剿灭等语。所奏非是。
此次进兵,专为剿灭厄鲁特贼众,其回部事宜,俟荡平伊犁之后,原可从容办理。至于擒拏阿逆,原议定明岁再行进兵,岂料阿逆自投罗网,由哈萨克逃回。适遇大兵击败。率众数十人奔窜,此正机会可乘,时不宜失。现在两路大兵,应已会合,即当竭力搜捕,明正典刑。其余贼众,尚可徐徐办理,何论回人?纵回人妄逞鸱张,俟平定厄鲁特后,再行办理,亦有何难?……”兵凶战危,却能从容若定,这是政治家和军人的区别。
在乾隆皇帝看来,南疆维吾尔人叛乱不算事,一举根除准噶尔叛乱,才是大事。他铁了心要把阿睦尔撒纳抓获正法。至于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反复交代,不要急,慢慢来。如果前线军事指挥官班弟和兆惠都有这样的政治眼光,不在准噶尔覆灭后的南疆窗口期急于动作,让黑山派在南疆掌权一段时间,或者在任用大小和卓这个事上,向朝廷请示、沟通一下,南疆后来的祸乱都有可能避免。
乾隆的这份谕旨中,透露出另一个信息,“至霍集占使人涉呢雅斯,已派员送还回部。如恐其洩漏军情,则即行正法。其五十六、托伦泰等,亦即追回,毋庸遣至回部”。乾隆说,霍集占派到北京的投降代表,我打发回去了,如果你们感觉他有可能泄露军情,直接截拦下来,杀掉算了。我已经派五十六(人名)和托伦泰到南疆慰问,赶紧把他们追回来,免得又去送死。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大小和卓叛乱以前,霍集占已经向北京派出投降代表,乾隆也派人到南疆地区慰问。大小和卓对清朝中央政府在南疆的权力合法性没有质疑,阿睦尔撒纳二次叛乱造成北疆地区政治和军事真空,使霍集占产生错觉,他错误地认为,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收复新疆的能力。他更大的错误,是误判了中央政府收复新疆、统一新疆的强大决心!大小和卓叛乱后,南疆地区陷入白色恐怖,不但黑山派被全面清洗,白山派内部也出现分裂。霍集占依靠宗教极端思想蛊惑信众,他不得不把极端宗教的旗帜举起来、扛下去。他组建了一支宗教卫队,类似于今天中亚某些地区的宗教警察,所有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行为,如男人不蓄胡须,女人不戴面纱等,一有发现,当众处死。宗教狂热一旦被点燃了,就再也遏制不住,这把火终于烧到大小和卓自己头上。
这帮被赋予神权的宗教徒认为,大和卓波罗尼敦和小和卓霍集占两个人,出生在伊犁,从小和准噶尔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也是“叛教者”和“异教徒”。一帮宗教狂热分子纠集起来,对波罗尼敦和霍集占组织暗杀。行动失败后,霍集占迅速反制,出动卫队进行肃反,大肆抓捕和处死叛乱分子,白山派内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1757年(乾隆二十三年)九月,霍集占完成对南疆宗教势力的清洗,全面掌握了南疆的控制权,在叶尔羌(莎车)建立分裂政权,自称“巴图尔汗”,史料记载为“汗和卓”或“和卓汗”。这是一个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合二为一的名称,和伊斯兰教惯用的“帕夏”、“苏丹”、“哈里发”等名称不一样,很明显受了准噶尔汗国的文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白山派领袖自居的霍集占,已经背叛了他祖上信奉起家的纳格什班迪耶教派,成为一个混杂着世俗血统的“异教徒”。
1758年(乾隆二十四年)二月,沙俄交还阿睦尔撒纳尸体,历时78年的平准战争宣告结束。大清王朝终于腾出手来,开始解决南疆问题。
乾隆皇帝钦定的南征队伍,是一支由各民族融合组成的联合团队:靖逆将军雅尔哈善任南征军统帅;吐鲁番额敏和卓、镶黄旗汉军都统哈宁、巴里坤领队大臣爱隆阿,为参赞军务大臣;一等侍卫顺德讷、哈密维吾尔王子玉素普、库车黑山派掌教米尔扎·鄂对和卓、肃州总兵阎相师、镶黄旗察哈尔总管端济布,为各军统领;熟悉南疆事务的拜城维吾尔首领噶岱默特,为随军幕僚。在平叛战争中大放异彩的名将兆惠和富德,都没有进入第一梯队,他们被留在伊犁打扫卫生,干刽子手的勾当。
1759年(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清军抵达喀什,大小和卓逃亡到浩罕国被处死,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战结束,延绵于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之间的南北疆地区,完整回归祖国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