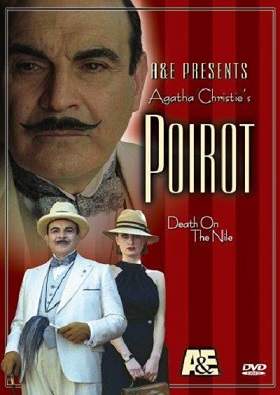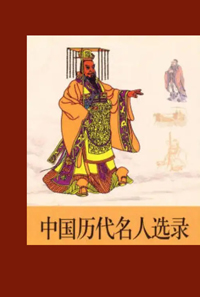今天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关于纳粹的。
01
我对纳粹史一直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纳粹的大屠杀不是孤立突发的事件,它人类黑暗面的一个象征,一个深渊,隐藏着某些人性的秘密。所以碰到关于这方面的书,一般都会拿来翻翻。今天这个文章就源于理想国出版的一本书《纳粹医生》。几年前我读过一遍,感觉就像体验了一场噩梦。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愿再想起这本书。最近这些天,我偶然又翻读一遍,觉得还是有必要说说这个问题。
说起来,这本书里有一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深。
大家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习惯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但是毒气室操作起来有些麻烦,适合批量处理,不适合零星杀戮。所以,奥斯维辛还有另一种杀人技术:往心脏注射石碳酸。一开始是注射静脉,后来发现见效太慢,就直接往心脏里打。
纳粹医生就坐在手术室里,犹太人排队在走廊里等。犹太囚犯助手会把他们一个接一个领进去。进去以后,坐在凳子上,往心脏里一针打死。每个人大约花费两分钟。走廊里的犹太人有的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有的则知道。但不管知道不知道,他们都在那里静静等待。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个景象,但我确实被这段描写给惊住了。在我看来,这比毒气室还恐怖,比随机枪毙还恐怖,这种井然有序的注射有种比地狱还恐怖的气氛。
一个叫韦斯的犹太人助手,负责守在手术室里抬尸体。一次,他看到门打开,自己父亲走进来了。纳粹医生说:“我要给你打一针抗伤寒的药。”韦斯站在旁边默默地哭。一两分钟以后,他把父亲的尸体抬走了。
第二天,那个医生问韦斯:“你昨天为什么哭?”
韦斯说:“因为那个人是我父亲。”
医生说:“要是你当时告诉我,我会让他活。”
这句话的可信度不好说,可能是医生故意让韦斯难受,不过也可能是真的。但无论如何,后来法官审理奥斯维辛案件的时候,问过韦斯当时不说出来。维斯说:“我害怕说了以后,他会让我也坐在旁边打一针。”
这是怯懦吗?也许是。但未曾体验过地狱的旁观者,恐怕很难评价。比如还有一个事例。奥斯维辛医生数量不够,所以要从犹太囚徒里召一些医生助手。有位荷兰籍犹太人回忆说,他们刚被押运到集中营的时候,德国人喊:“医生出列!”他没有多想,本能地朝前走了一步。然后,他就被推到一小群人里,原地等候。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告诉他们,押运车厢里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孩子、父母、岳父母、妹妹,全都被送进毒气室杀死了。又过了一小会儿,他成了纳粹医生的助手,为自己的仇人们服务。
那是什么感受呢?他回忆说:“我仍然想活……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朝前走那一步。”

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在奥斯维辛,生存成了压倒性的东西。有位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纳粹说:“你见到的所有幸存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夺取过别人的食物,否则他们不可能幸存。”
他的话里有一种蔑视,但是谁又把这些人推到如此境地的呢?
02
不过,我这篇文章想说的不是幸存者,而是纳粹医生。他们的工作有很多种类,比如有人会拿囚徒做医学实验;有人会负责安排毒气室;也有人负责医疗部门,治疗那些生病的囚徒(如果发现他们短期内无法回到工作岗位上,就打发进毒气室);而所有的医生都要参与“筛选”,把体弱者、孕妇、老人挑出来,送进毒气室。
他们是医生,都做过希坡克拉底誓言,那么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呢?
绝大部分纳粹医生都有强烈不适应期。

筛选
他们来到奥斯维辛以后,很快就得参加“筛选”,这是刻意安排的见习实验。有人呕吐,有人震惊得无法行动,有人在“筛选”后酗酒大骂。但是,最终所有人都能适应。整个奥斯维辛,只有一个叫恩斯特的医生完全躲过了“筛选”。他在柏林有人脉,所以走了后门。上司让另一个叫德莫尔特的医生顶替他。
德莫尔特的反应很激烈。第一次“筛选”时吐了一地,第二天上午没能走出房门,因为他患了紧张性精神症,浑身完全僵硬了。他是有医学理想的年轻人,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的想象。等他知道自己是顶替恩斯特的时候,开始破口大骂,说“既然你不愿意去做筛选,那我也不去!”他拒绝上岗。
奥斯维辛的领导就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讲到了国家和职责,讲到日耳曼民族的未来,也讲到了人道主义,“既然这些犹太人注定要死,把他们筛选出来其实更人道”。两周以后,德莫尔特乖乖地进行“筛选”了。
恩斯特不乐意做筛选,德莫尔特不乐意做筛选,但也有乐在其中的——比如著名的恶魔医生门格勒。
门格勒是整个奥斯维辛最出名的魔鬼。读过奥斯维辛历史的人,未必记得住集中营最高长官是谁,但都能记住门格勒。他长得不错,重视仪表,总是一尘不染,很有派头,集中营的囚犯说他有点像克拉克.盖博。大家都在电影上见过那种挺拔英俊的党卫军军官吧?门格勒就是这种形象的典范。

门格勒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不折不扣的变态狂。对于“筛选”之类的事情,他总是乐在其中,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喜欢充当上帝,充当死神,享受生杀予夺的快感。至于他在医学实验里做的事情,更是骇人听闻。在这里我没法转述那些细节,只举一个例子好了。
他曾经和别的医生产生争执。门格勒断定两个八岁的孪生男孩有肺结核,可是其他医生并没查出迹象。门格勒勃然大怒,当即转身离开。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平静地说:“你是对的,没有肺结核。”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是的,我把他们俩解剖了。”——他用颈部注射的方法杀死了那两个男孩,然后“趁他们身体还热的时候”,做了解剖。
门格勒有非常诡异的一点,他对受害者有时会显得很好,然后又会转眼把他们弄死。就像被他解剖的这两个孩子,人们都觉得门格勒平时很宠他们。事实上门格勒对很多孩子都挺好。比如,他去见吉普赛孩子(吉普赛人像犹太人一样,也遭到了大规模屠杀)的时候,总是带着糖果和玩具,还会领他们出去转转。那些孩子一见他就会大喊:“门格勒叔叔!门格勒叔叔!”但是门格勒哄他们玩的时候,就会同时做筛选,决定哪些孩子应该送去毒气室。有的孩子藏了起来,门格勒还会搜遍各区找他们,然后开着汽车把他们送去毒气室,一边开车一边告诉他们,要去的地方好极了。
这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恶魔。他对那些孩子是真心喜欢吗,还是像猫杀死老鼠前的捉弄?门格勒的有些同事认为,他是真心喜欢那些孩子。这么说让人吃惊,但是事情也许确实如此。他喜欢孩子,但是又会毫不在意地杀掉他们。在门格勒心中,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
人心就是这么奇怪。
03
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里,有德莫尔特这样的人,有门格勒这样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总的来说,绝大部分纳粹医生跟普通人差不多。自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以后,“平庸之恶”渐渐成了老掉牙的话题,而且被很多人诟病。但是,看完《纳粹医生》之后,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很多医生并不是没有人性。他们大多都经历过强烈的心理排斥,他们喝醉酒的时候也会痛骂“这个该死的地方”,他们偶尔也会做一些小小的善举,而且他们和犹太助手之间,也会有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关系。
有位囚犯医生就回忆说,管理他的纳粹医生遇到他时,居然会和他握手!这个小小的举动让他极其震惊,几十年后还在感慨说“这真是人性啊”。还有位女犹太医生回忆说,她的上司两次帮助她,托关系把她母亲从死亡名单上撤了下来。而且当囚犯们被迫裸体从纳粹医生面前排队走过时,他“只是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决不看别的地方”,用这种方式,他努力为对方保留尊严。
还有一位纳粹医生发现某位囚犯助手是医学院校友,他兴奋地向她打听母校的教授、餐馆和小店,长时间地怀旧。当她得了斑疹伤寒的时候,这位纳粹医生把她救了下来,还送给她一件衣服,而且还带来了一副胸罩。这位囚犯助手不是犹太人,而是因为帮助犹太人才进了集中营,纳粹医生听说这件事后,四下努力活动,要帮她重获自由。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份努力还是让她充满感激。至于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德莫尔特,犹太助手甚至成了他的导师。那位犹太助手是一位名教授,无论岁数还是水平都高出德莫尔特很多。人们回忆说,德莫尔特把他当成了“父亲般的人物”。
这种零零星星的故事有很多,它们可以说是在这座地狱里的“人性孤岛”。有了这些孤岛,地狱就不是一片彻底的黑暗海洋。但是,它们的意义被幸存者们夸大了。不管这些纳粹医生闪现过什么人性火花,他们还是凶手,是屠夫。他们筛选,他们杀人,他们做各种各样邪恶的事情。
就像有位叫叔帕的纳粹卫生员,他被公认为“正派人”,对囚犯彬彬有礼,从不打人。当他进来的时候,会说“早上好”,走的时候,会说“再见”。跟集中营的坏蛋比起来,他“简直就是个圣人“。1943年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同事被派去杀害120个波兰儿童。做到一半的时候,他从房间里走出来,坚决不再干了。回到营房以后,他整个人崩溃掉了,脸色极度苍白。他找到上司说自己无法下手杀儿童。上司同意了,把他调到了其他岗位。
听上去,这里确实有人性的成分,对吧?可是在战后,法庭经调查发现他参与了至少200起屠杀,被杀掉的人数至少有900人。他确实不情愿,也确实对囚犯友善,但他也确确实实杀了这么多的人。
这些“人性孤岛”对我们能够起到一点抚慰作用,让我们相信黑暗中总有微弱的闪光。但除此之外,它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勇气作伴的善良,总是泯灭得太快。
04
这里不免说到一个最常见的问题:为什么?纳粹医生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纳粹医生》给出非常复杂繁琐的论证,牵涉到了一系列心理学上的角色转换。这些论证不能说不对,但还是有点太形而上。其实最简单也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怯懦。
这倒不是说不去杀人,就会被上司枪毙。没有这样的事情,纳粹德国虽然残暴,但行事逻辑倒不是这个样子。当然环境压力当然还是广泛存在,而且这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因素:呆在奥斯维辛,就不用上东线战场。
这是肉体上的怯懦,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怯懦,那就是思想上的怯懦。这种怯懦看不见摸不着,但可能起到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什么叫思想上的怯懦呢?首先是没有质疑的勇气,然后是没有质疑的能力。没有勇气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有位纳粹医生说的,“我们那个时候就不问问题。”服从已经成了习惯,自然也就没了质疑的勇气。
那么什么叫没有质疑的能力呢?简单地说,就是那些纳粹医生即便想反对屠杀,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
在纳粹德国,有三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类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种族斗争;犹太人是日耳曼人的种族敌人;日耳曼种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些观念哪儿来的?当然主要是希特勒的推动,但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希特勒是恶魔。但即便是恶魔,没有燃料的话,他也点燃不起这么一大团火焰。
当时,整个欧洲思想界都出了点问题,而德国出的问题最大。大家都知道德国哲学很高级,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人也许很了不起,但是他们也给德国人心灵里注入了某些毒素(对于康德是有争议的,为什么要把他放进这个名单里,大家可以参看伯林的《自由及其敌人》一书,我这里采用的是他的说法)。有人争辩说政治是政治,哲学是哲学,不能让德国哲学背这个黑锅。但这个说法不对。德国那套哲学不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好,在这个问题上绝对起到了坏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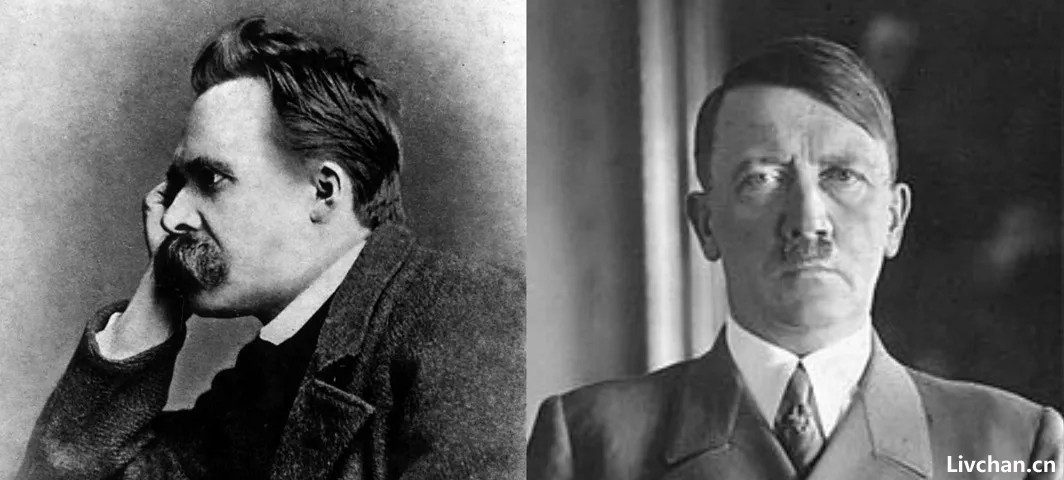
希特勒背后也是有思想谱系的
那些思想家当然不会赞同希特勒的做法,但是其中有草蛇灰线的影响
总之,德国人渐渐相信有一个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充满旺盛意志的集体存在。
个人无足轻重,而日耳曼精神长存不朽,个体只有融入它、服从它,才能实现自我。
当时的德国人不对头,这么说也许有点标签化,但不对头就是不对头。
他们和英国人、法国人不一样,和意大利人、东欧人也不一样,他们的思想就是邪门,你可以说这种邪门里有种深刻,但邪门就是邪门,奥斯维辛就是它的证明。
好吧,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不管怎么说吧,纳粹德国盛行这三个观念,那么如果你接受了它们,你怎么去有理有据地反对奥斯维辛?
你说杀人不对,杀害儿童不对,那么好,我们应该任由犹太人危害德国种族吗?犹太人不该灭绝吗?日耳曼种族利益不是高于一切吗?你要站在什么立场上呢?只要你赞同那三个观念,你就没有办法正面反对这些逻辑。你最多说:“犹太人当然应该清除,但也要采取更文明的方式啊,可以驱逐他们,也不用斩尽诛绝呀!”要注意,只要你接受那三个观念,这已经是你可能有的最强烈的抗议了。
“虽然…..但是”。可只要有了前面的“虽然”,后面的“但是”就不堪一击。
好几个纳粹医生都使用过这种“虽然.....但是”抗议过,但是很快就被驳得哑口无言。不是因为畏惧住口,而是真的哑口无言。他们觉得自己理亏了,自私了,多愁善感了,逃避责任了,不肯为日耳曼民族献身了。
只要你接受了那套话术,你就根本不可能驳倒对方,而只能把这些事当成“必要的邪恶”。那些纳粹医生基本也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也知道这是邪恶的。所以这帮纳粹医生大多都不愿意让妻子儿女探望自己,因为这里的一切确实太可怕了。妻子问起自己的工作时候,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只是负责治疗,不管别的事情。会不会杀人?噢,你怎么会有荒唐的念头!”但是他们也接受了这种邪恶是“必要的”。
有位助手问过纳粹医生一句话:“你不记得自己从医时做过希坡克拉底誓言吗?”那位医生回答说:“我当然记得。我要保存生命,有时就不得不从病体切掉坏东西,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上的坏东西。”换而言之,这就是必要的残酷。
如果想要真的在道德上反对屠杀,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否认那三个观念——至少要否定其中的某一个:不,人类没有你死我活的种族斗争;不,犹太人不是日耳曼种族的死敌;不,日耳曼种族的利益不是高于一切。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否定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纳粹德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大环境都在这么说,书上这么说,学校里这么说,邻居们这么说,所有人都在这么说,哪怕是不那么喜欢希特勒的人也在这么说!这几乎已经刻进了脑海深处,人们怎么可能去否定呢?要想否定它们,就得在思想上另起炉灶,这太考验人们的思想勇气了。拒绝一套思想,有时候比拒绝杀人,需要更大的勇气。
所以他们在杀人时会找到种种托词:也许这件事不太好,但对德国来说它是必要的,再说,我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说到底,现在是战争年代,而且我只是在服从命令…….等等等等。
在纳粹德国,天主教徒的平均表现往往比较好一点,这也跟他们的信仰支撑有关。对天主教那套东西,大家当然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它在黑暗时代确实提供了一种力量。即便他们承认三个观念中的前两个,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内心深处否认第三个:日耳曼民族当然不是高于一切的,上帝才是高于一切的!这种传统教义就给他们一种道德上的勇气,虽然每个人表现得可能不一样,但是它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05
那些纳粹医生当初没有拒绝的勇气,事后也往往没有反思的勇气。
在所有的纳粹医生里,口碑最好的是恩斯特,也就是那位走后门逃脱“筛选”工作的人。所有幸存者都说他的好话。无论是书面记录还是口头讲述,都把他说成一个大好人,简直是“奥斯维辛之光”。他没有去做筛选,他把囚犯当成人看待,他用工作之便救了不少人。
曾经有一阵子,恩斯特也用囚徒做医学实验,因此战后法庭要审判他。结果好多幸存者都出来作证,说他做实验只是个幌子,其实是在用这种办法来挽救病人,否则那些人就要被送去毒气室了。恩斯特还拿实验做借口,搞来大块的肉分给病人呢。幸存者们力挺恩斯特,他最后被无罪开释,平平安安地回老家做了个医生。
这听上去像是个弱化版的辛德勒,对吧?可是《纳粹医生》作者采访他的时候,却大吃一惊。没错,他确实干了那些好事。他自己的描述跟作者的多方取证也对得上,幸存者们的证词也是真实的。
但是,六十多岁的恩斯特不肯去彻底否定奥斯维辛。
他口口声声说那个恶魔医生门格勒是个天大的好人,他从没见过如此正派的人物了。门格勒是个好同事、好领导、好士兵,也是个好医生。门格勒把毒气室、实验室都炸毁了,想要销毁罪证,恩斯特说这是正确的。一个好的德国人,怎么会愿意把德国不好的东西展现给外界呢?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忠诚。至于门格勒干的那些丧心病狂的事情呢?大规模筛选,随心所欲的杀人,挖空心思的实验……恩斯特含糊地解释说:“这要放在奥斯维辛那个大环境下去看。”
关于奥斯维辛,恩斯特说这件事情很复杂。它确实有点邪恶,但是大家应该考虑考虑当时的种族意识呀。当时大家都觉得应该把犹太人消灭掉呀。但到底该不该消灭犹太人呢?恩斯特认为这是善良人们应该去沉思的一个严肃问题,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和“理性的讨论”。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时人们有理想,相信纳粹道路是天赐之福,而犹太人是根本之恶。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可能“有点过头”了,但是——这里面毕竟有一种理想主义,毕竟有一点正确的东西。说到底,纳粹也有自己的优点呀。可你再看看现在的德国年轻人!他们缺乏理想,缺乏献身精神。这样下去,社会成什么样子了?一点都没有凝聚性。
恩斯特的言论真是让人震惊。
幸存者心目中的大好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难道他当初的善良都是伪装出来的?这倒也不是。恩斯特确实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无法摆脱“奥斯维辛时代”的烙印。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他可能没彻底摆脱当年的洗脑,或者他思想和行为存在撕裂等等。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就是他不愿意否定自我。
彻底否定奥斯维辛,彻底否定纳粹德国,彻底否定反犹主义,就等于否定了当年的自我。否定了当年的自我,就等于说自己前半生活在一场大错误里。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不管在我们看来,反犹主义是多么可恶,纳粹德国是多么邪恶,但是对于恩斯特来说,那总是和他的青春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在他脑子里,三四十年代一定跟活力、荷尔蒙、爱情、友谊、运动、张狂、滚烫的热血有关。他肯定快乐过,甚至肯定幸福过。如果把那些日子说成一片漆黑,那么他怎么解释自己的青春呢?他又怎么解释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呢?
他忍不住去为纳粹辩护,为魔鬼医生门格勒辩护,甚至为灭绝犹太人辩护,但说到底,他是在当年的自己辩护。
德国青年里就有人说,“没有希望把那一代人救回来了”。这话有些偏激,但里面也不无道理,那一代德国人和黑暗世界纠缠得太深,以至于很难去做切割。当然,他们大部分不会像恩斯特这样公然辩护。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保持沉默。
06
这篇文章写得有点太长了,过于考验读者耐心了,那么就在这一节结束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准确描述自己的感受。纳粹德国的出现是极端事件,奥斯维辛的出现也是极端事件,就像是魔鬼策划的恶毒实验。但是,那些纳粹医生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被推到了一个极端的环境里,就去努力适应这个环境,变成屠夫。等这个极端环境消失了,他们可能又会变成普通人的样子。就连那个恶魔医生门格勒,也会消融在日常生活里,可能性格略微有点古怪,但不会让人联想到邪恶(他潜伏在南美洲的后半生就相当平庸)。说到底,在大家身边说不定就有这样的人物,只是他们没有碰到门格勒的环境而已。
但正因为这一点,才更让人觉得恐怖。
这些纳粹医生差不多都犹豫过,咒骂过,抵触过,但最后他们都顺从地去杀人了。他们当然是一步步走到这个境地的,就像当年他们都为反犹主义鼓掌过。可是,当他们被带到奥斯维辛的时候,他们震惊了。有位医生回忆说:“每个人都听希特勒说过,犹太人必须被消灭。每个人都听到了,可是没人相信这会变成真的……然后,我的天啊!一个人习惯以为不过是宣传废话的东西,现在忽然变成了完全的、彻底的、整个的真实了!而且在操作上很具体。这是最让人震惊的……”
看,他们以为是说说而已!
当然他们就震惊了。震惊之后,他们就乖乖拿上皮鞭和针头,去干那些反人类的恶事。
这么多医生里,没有一个真的去抗争过。一个都没有。
来源:押沙龙yashl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文/郭歆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攻势凶猛,国军节节败退。1938年春,日军计划南北夹攻,打通津浦铁路,合围徐州时,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4月7日,蒋介石收到了“台儿庄大捷”...
文/郭歆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攻势凶猛,国军节节败退。1938年春,日军计划南北夹攻,打通津浦铁路,合围徐州时,遇到了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4月7日,蒋介石收到了“台儿庄大捷”... -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中式”服装、发型、妆容火爆出圈,这种将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流行元素结合的风格受到众多年轻人的喜爱。中国专家和年轻人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都表...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中式”服装、发型、妆容火爆出圈,这种将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流行元素结合的风格受到众多年轻人的喜爱。中国专家和年轻人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都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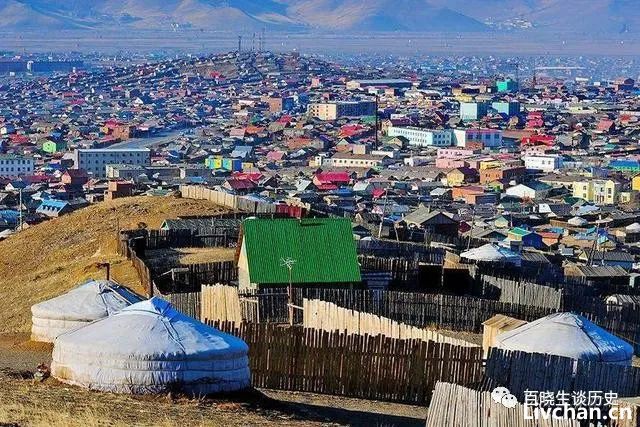 蒙古国和我国的内蒙古历史上都曾是蒙古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发生之时,北洋政府在国内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声浪的压力下,与沙俄进行了艰难的外交交涉,最后于1915年与俄、蒙达成...
蒙古国和我国的内蒙古历史上都曾是蒙古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发生之时,北洋政府在国内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声浪的压力下,与沙俄进行了艰难的外交交涉,最后于1915年与俄、蒙达成... -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外界发布录音广播,宣布日本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公告》,正式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获得了最终的胜...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外界发布录音广播,宣布日本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公告》,正式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世界反法西斯联盟获得了最终的胜... -
 在吴彪60年的人生中,他已至少三次掀起社会影响的涟漪。第一次是在1995年。那年2月,吴彪为总裁的宁波金鹰集团总公司以1380万元“天价”在北京拍下两只从天安门城楼上换下的旧...
在吴彪60年的人生中,他已至少三次掀起社会影响的涟漪。第一次是在1995年。那年2月,吴彪为总裁的宁波金鹰集团总公司以1380万元“天价”在北京拍下两只从天安门城楼上换下的旧... -
 如同一条有关流量和网红的生产线。对于想要成为“网红”的人而言,杀出重围是难题;对已经成为网红的人而言,如何安全地活下去是难题;而对一个“被驱逐”的网红而言,二度东...
如同一条有关流量和网红的生产线。对于想要成为“网红”的人而言,杀出重围是难题;对已经成为网红的人而言,如何安全地活下去是难题;而对一个“被驱逐”的网红而言,二度东... -
 2024年8月29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就日本驻菲大使有关南海的错误言论做出严正回应:“难道忘了日本侵略菲律宾,将马尼拉夷为平地并造成超过10万名平民死亡的马尼拉大惨案...
2024年8月29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就日本驻菲大使有关南海的错误言论做出严正回应:“难道忘了日本侵略菲律宾,将马尼拉夷为平地并造成超过10万名平民死亡的马尼拉大惨案... -

《宋史·奸臣传》收录的二十二人都是谁?谁是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
在历史的长河中,像和珅、秦桧一样的真奸臣确有其人,但其实也不乏被历史记载有误解的“假奸臣”,比如被记入宋朝《奸臣传》之一的章惇,而... -
 2019年5月3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悼念泰国前总理时,发表言论称:越南军队在1979年的干预是入侵柬埔寨。此言一出,激起柬埔寨和越南的强烈反应。柬埔寨首相洪森反驳道:李显...
2019年5月3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悼念泰国前总理时,发表言论称:越南军队在1979年的干预是入侵柬埔寨。此言一出,激起柬埔寨和越南的强烈反应。柬埔寨首相洪森反驳道:李显... - 早就注意到,有那么一些自称“研究”“国学”的人,跳出来恶毒攻击西史辨伪。其中有一位宣称要重新注释解读“六经”的“大师”,公开撰文(《“伪史论”批判——信息时代的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