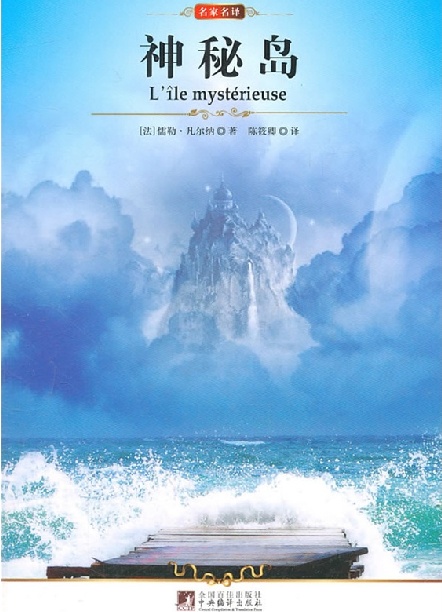在许多人看来,周扬和陈伯达,一个是著名的“红色评论家”,一个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两人的生平经历、性情为人可谓是相差甚远。然而,在历史光晕交错的角落,迟暮之年的两人却有了交集。
早年交情:多有接触,私交如水
陈伯达年轻时颇为喜爱文艺作品,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他与周扬在上海相识,但两人的交情应当不算深厚。
全国解放后,陈伯达和周扬同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两人在工作上虽说分工不同,但都一度住在北京中南海,且还是邻居,可两人秉性皆非豪放善徕一派,因而交情上终究是清淡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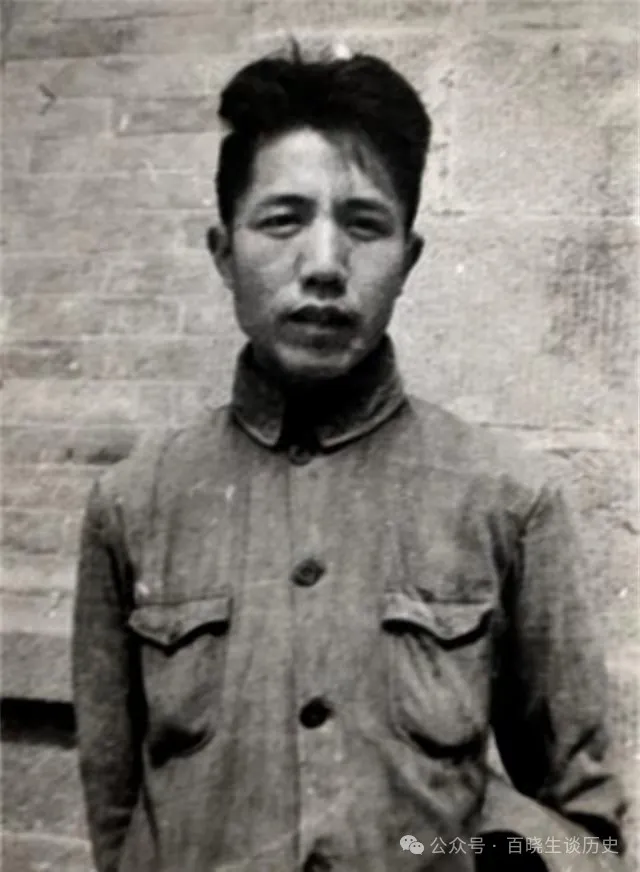
周扬
在他人看来,陈伯达行事和性格总有些古怪,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室内户外,他总是戴一顶帽子。曾有人说笑:“不是伯达的妻儿,怕很难知晓他的头发是白是黑。”
其次,陈伯达从不问别人姓名。他到首钢多次,军管会的几位领导人迎送陪同,向他汇报工作,几人交谈许久,但陈伯达始终是“只认其面目,不知其姓名”,也不知道谁担当何种职务。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其傲慢的一种体现。
20世纪60年代时,毛泽东对文艺界的工作颇有微词,数次指出“文艺应当为工农兵服务”,并认为周扬的工作并未很好的落实这一政策导向。
不久后,毛泽东便要求陈伯达转告周扬,“准备下去,到农村接触一下实际的生活。”
陈伯达后来回忆:“毛主席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时,还说了一句很严厉的话,他说:“如果周扬不愿意下去,可以派解放军的一个连护送他下去。””诚然,这是一句气话,但依旧让陈伯达感到主席严肃的态度。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陈伯达很快就找时间和周扬谈了。

他那一口福建话,听起来实在费劲。平日里,周扬为听不懂他的话而着急,他也为周扬听不懂自己的话而着急,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
谢富治懂得他的话,常常与陈伯达同行,替他当翻译。他便对谢富治表示感谢,连连拱手道:“你是不杀(菩萨),你是不杀!”
但这一次,周扬并非花太大的功夫就听懂了这番劝诫。
下基层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身为推动者之一,陈伯达只能尽可能让这位老同事心里好受点。
周扬下农村经历较少,身体素质也一般,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陈伯达便主动和天津的同志去商量:“能不能给周扬同志安排在小站镇的西右营。”

周扬下了农村之后,陈伯达也常去看望他,他并不是会宽慰人的性子,只是偶尔听一听周扬的工作经历和感悟。
周扬劝他不必常来,他只是推说:“我喜欢平房,出来走走挺好。”
“特殊时期”到来:先后遭难,双双陷落
1966年6月的一日,王文耀接到了江青的电话,她点名要找陈伯达。
王文耀觉得电话里的口气不对,赶忙请陈伯达接电话。
王文耀站在一边:“江青的声音很大,似乎也不打算避讳些什么,我听到她说要发表一篇关于什么人的文章,后来才知道,是要批判周扬。”

这时,陈伯达听到江青要公开点名批判周扬,他有些犹豫道:“他才刚做完肺癌手术,现还在休养,这样子,他的身体怕是受不了吧?”
江青却置若罔闻:“你这都是小问题,我们这才是大事,一切都要从大局出发……”
王文耀曾在周扬麾下工作过,听到这一信息心情十分复杂。直接告诉周扬夫妇?两人的身体都不好,恐怕受不住。
当时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保春,保春也惊讶地小声说:“唉呀,周部长做了大手术不久的呀,这能受得了吗?”他也直摇头。
对江青他们以何名义在报上点名,两人不得而知,只能担心地等待着。
几天后,《人民日报》第二版、第三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周扬颠倒历史的第一支暗箭一评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条注释》。
那天以后,《人民日报》接连刊登多篇批判周扬的长篇文章。
7月28日,中宣部召开大会批判周扬。周扬夫妇年初在北京做完手术,其后去上海休养,随后又转到天津休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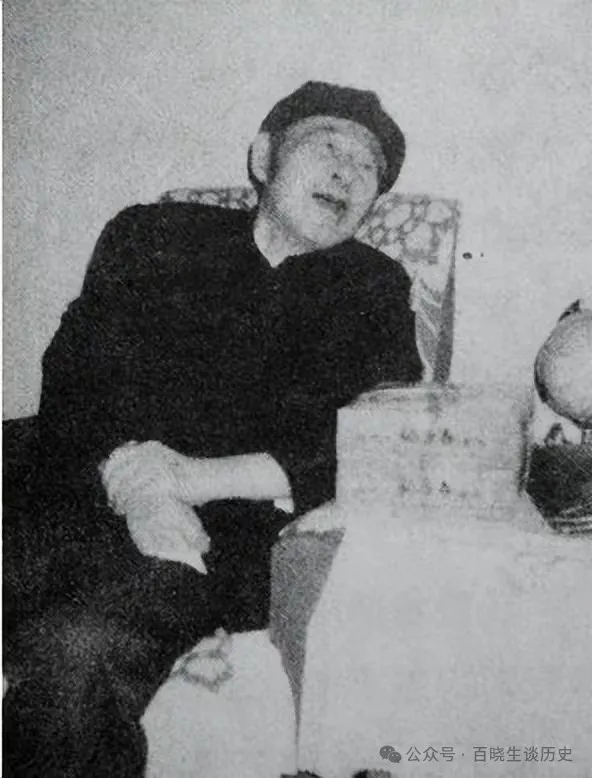
外头处处喊打,两人拖着病弱的身体,无处藏身。此时,天津市交际处的李松茂得知此事,打电话通知了王文耀和王保春:“天津交际处已不能待了,每天都要揪人出来批斗,我已经将他们藏在了一个地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王保春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陈伯达,陈伯达只得犹疑道:“他们俩身体不好,先让小李照顾他们一下,藏起来吧……”
后来,李松茂同志又来过几次电话说,他实在顶不住了。
王文耀回忆道:“他当时说了,他为周扬夫妇买的粮食已经吃完了,他们吃饭也成了问题,最重要的是,周扬他们自己也想回北京。”
听闻这个消息,陈伯达只得同意让他们回北京。
一回到北京,周扬夫妇就被造反派给抓走了。直至1975年6、7月间,周扬才被释放。
恰好此时,被关押五年之后的王文耀也被无罪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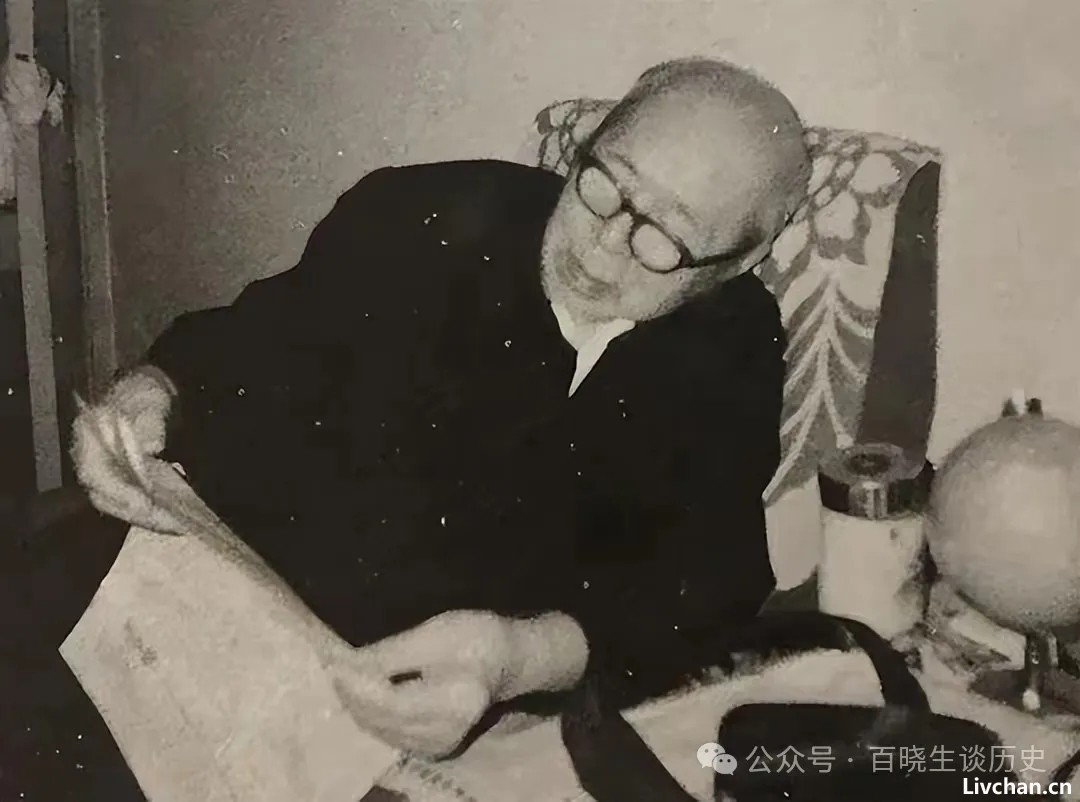
两人见面后,周扬第一句话就问起陈伯达。老人眉头紧皱,不住叹息道:“他后来职位那么高,怎么就……这么不谨慎呢。他出事后,我也很难过。”
周扬此言,指的是陈伯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后不久就遭到批判,从此下台的事情。
对此,王文耀只能感叹:“一言难尽啊,不由自己。”
迟暮之年再会晤:一谈泯恩仇
了解到陈伯达的一些情况,周扬决定与陈伯达见上一面——这在当时是相当需要勇气的。
而在陈伯达的晚年,周扬是第一位以朋友的身份主动约晤他的高级领导人。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回忆,那天傍晚6时,公安部门派出两位工作人员来接陈伯达,深夜11时,陈伯达才回到家中。
两位老人阔别16年,一见面竟谈了近5个小时。
不同于想象中的激动泪目,两人再相见,情绪都十分稳定,可当周扬说出第一句话,两人便流露出了几分伤情。
“我被关起来后,在监狱里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听不到有你的名字,我就知道,你倒了。”
闻言,陈伯达低低地摇下头。
周扬继续说:“后来我知道,你的帽子戴得最多了。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
陈伯达坦言道:“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救过毛主席。1948 年,国民党轰炸阜平,那早,我听到飞机响……是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才离开的,那时候啊,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中,屋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
周扬怔了怔,他当时也在阜平,听说毛主席那次很危险,但不知道是陈伯达救了毛主席。
两人皆是苦笑,周扬又问道:“你现在写些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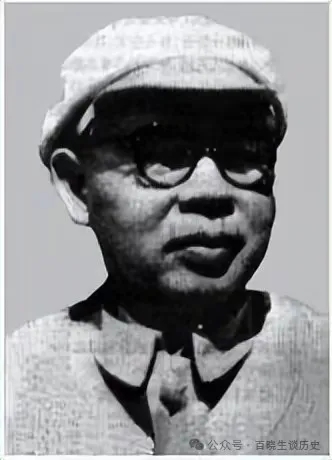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没有?”
周扬倒有些意外:“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将来如果能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
周扬只推说:“这到时候再说吧。”
陈伯达又问:“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这本书值得看一看,作者很熟悉19 世纪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接触过很多作家。书里讲了屠格涅夫很多事情,也有其他文学家的事情。”
陈伯达做了介绍,周扬让秘书记下了书名,他解释道:“我现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很多时间都花在这件事上。”
陈伯达听了似乎很感兴趣:“你的书出来以后可不可以送给我一本?”周扬自是应允。
后来,陈伯达所写的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交到了周扬手中。
陈晓明回忆,1982年11月的一天,有两位曾经来访过的老朋友,他们经过公安部门的同意,再度前来看望陈伯达。
他们刚刚入座,那位与周扬相熟的朋友,便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送给陈伯达。告知陈伯达道:“这是上月10日出版的第10期《读书》杂志,上面刊登了《求知难》,署名“纪训”。《求知难》是经过周扬阅后发表的。”
1989 年,7月31日,周扬辞世。同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
陈晓明透露,对于《求知难》的发表,陈伯达几度动情,“在他的晚年,长期处于极度孤独之中,周扬不避嫌,还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这让他时常感动。”
来源:百晓生谈历史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武则天晚年,极为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张“年少、美姿容、善音律”,日夜陪伴武后,仗势专权,嚣张跋扈。武后宠爱二张,不仅为肉身之欲,更重要的是确保权力上的绝对安...
武则天晚年,极为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张“年少、美姿容、善音律”,日夜陪伴武后,仗势专权,嚣张跋扈。武后宠爱二张,不仅为肉身之欲,更重要的是确保权力上的绝对安... - 从二战之后,中国的模式和西方的模式就格格不入了。虽然中国的家底是以前苏联为模板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又不完全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国家模式。而且到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了二十...
-
 关于大旅行家徐霞客,多数人往往只记住了他的“光鲜”,而不晓得他身后事的悲催:他去世后仅仅4年,徐氏家族就发生了灭门惨剧,几乎全家都被家仆屠戮殆尽,这是当时震惊江浙的...
关于大旅行家徐霞客,多数人往往只记住了他的“光鲜”,而不晓得他身后事的悲催:他去世后仅仅4年,徐氏家族就发生了灭门惨剧,几乎全家都被家仆屠戮殆尽,这是当时震惊江浙的... -

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一天,乌克兰为何能扛住打击并扭转局势?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情报局如何在俄罗斯海陆空打击中力挽狂澜乌克兰武装部队不成功的炸桥行动让俄军长驱直入2022年2月24日,驻守在琼哈尔大桥的第137海军陆战队独立营的士兵... - 汉中城靠近水边,因而城里地势平坦的地方,过去很有几处泉眼,或成一塘碧水,或成饮水的井口。城里最有名的泉水是太白泉,时间太久已找不到痕迹,在城里东边的一片城中村中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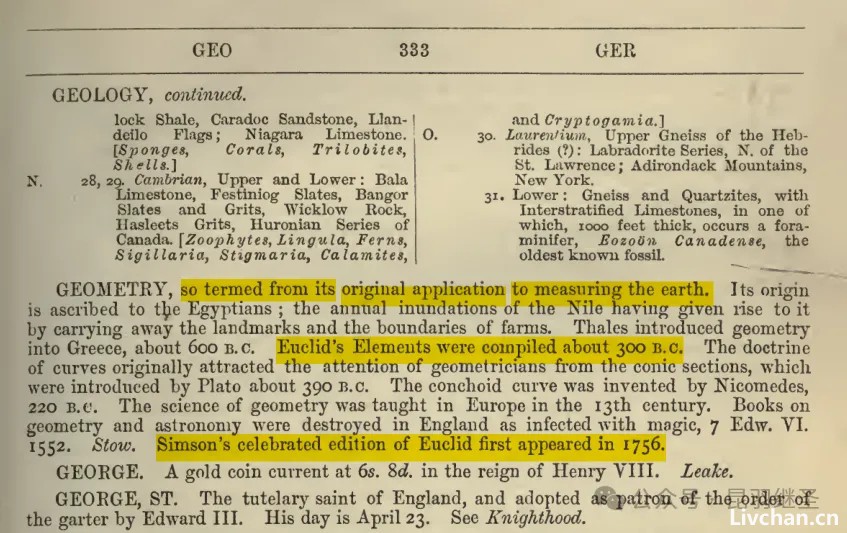 国外号称原版的《几何原本》是如何发现的?1897年,两名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闲得没事,专门跑到埃及亚明省俄克喜林库斯市的郊外去翻露天垃圾堆。注意,是露天垃圾堆。冥...
国外号称原版的《几何原本》是如何发现的?1897年,两名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闲得没事,专门跑到埃及亚明省俄克喜林库斯市的郊外去翻露天垃圾堆。注意,是露天垃圾堆。冥... -
杜车别——许倬云大师的《朱元璋对中国民族性的伤害,至深至巨》一文中谬误有多少?——兼评鹦鹉式史学
许倬云大师的朱元璋一文中谬误有多少?——兼评鹦鹉式史学(一)有朋友让我看一篇许倬云写的公号文:《朱元璋对中国民族性的伤害,至深至巨》。点进去一看,劈头是一个秃顶长... -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开国,其创立者都是极其重视国号命名的。每朝的开国皇帝都希望拟定一个好的国号,能使王朝国运昌隆 ,千秋万代。国号的确定基本上汇集众多能人...
- 1964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据曾志回忆,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
-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去世,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统治中国长达53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少数几个皇帝之一。...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去世,16岁的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统治中国长达53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少数几个皇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