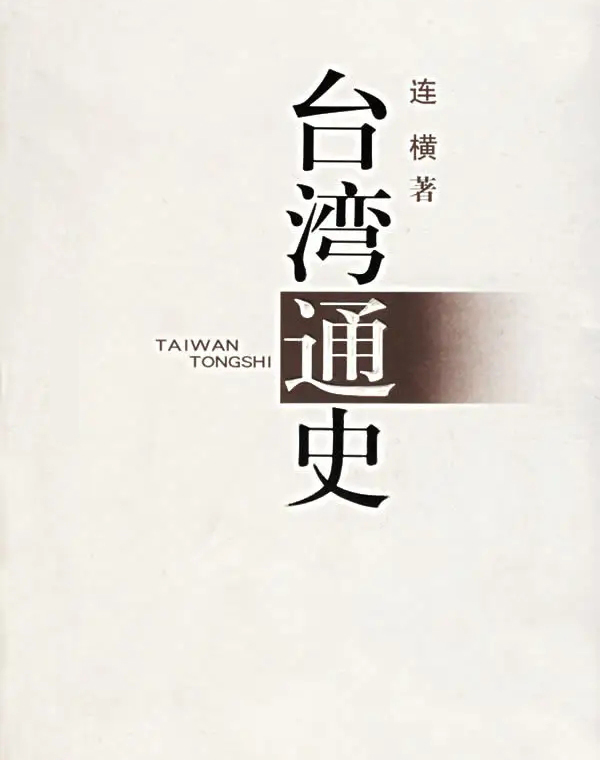据慈庆(王钟儿)墓志,王钟儿入平城宫之后,第一份工作是服侍景穆帝拓跋晃的妻子斛律氏,然后(也许是因为斛律氏去世了),“共文昭皇太后有若同生”。“文昭皇太后”是指宣武帝元恪的生母高氏,《北史》卷一三《后妃传》有传。高氏生前因生皇子为贵人,后因其子宣武帝元恪被立为太子而加昭仪之号,追谥为文昭贵人,宣武帝即位后又追尊为文昭皇后,孝明帝时更尊为文昭皇太后。幸运的是,高氏的墓志也于1946年在洛阳出土,出土地点为洛阳城北官庄村[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第21页。],志石今存洛阳王城公园碑林,真实性应无问题。墓志颇有残损,好在大部分尚可释读[墓志拓片的图版见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8页;墓志录文及简单考证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中华书局,2016年,第86—87页。]。墓志称:“皇太后高氏,讳照容。”由此知道宣武帝的生母就是高照容。
高照容十三岁以“德色婉艳”被冯太后亲选入宫,目的就是作配孝文帝。《北史·后妃传》:“孝文文昭皇后高氏……父飏,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于东裔。孝文初,乃举室西归。”高飏的七个子女都生在“东裔”,即高丽。据《北史·外戚传》,高飏的高祖高顾在西晋末年避乱入高丽,孝文帝初年,高飏和弟弟、乡人等举家西归,得北魏“俱待以客礼”,高飏自己拜厉威将军、河间子。北魏以客相待的都是异国来投者,视情形分为上、中、下多个等级。高飏的女儿有资格选入掖庭,说明他享受的是上客待遇。据高飏长子高琨的墓志,高飏的妻子姓袁,史书误作盖氏,也许因袁、盖二字形近致讹[高琨墓志的出土情况、墓志录文及基本研究,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71—73页。]。《北史·后妃传》说高照容被龙城镇推荐到平城后,冯太后“亲幸北部曹见后,奇之,入掖庭”。高照容获如此青眼,或许和冯太后的龙城乡思有关。
幸运之星照耀高照容,她不仅很快怀孕生子,而且生育日期惊险地略晚于孝文贞皇后林氏。如前所述,林氏生元恂在太和七年闰四月五日(483年5月27日),而《魏书·世宗纪》称“太和七年闰四月,(高照容)生帝于平城宫”。可见元恂、元恪兄弟同月出生。如果出生日期略有颠倒,可以想象高照容会遭遇什么。因为不是皇长子,元恪的出生日期没有出现在官方文书里,后来魏收编写《魏书》时,竟不知宣武帝出生在哪一天,只好笼统地说是闰四月。
元恪出生时,王钟儿已入宫十五年。这时斛律氏很可能已不在人世,而四十五岁的王钟儿算得老资格的宫人,大概在高贵人怀孕时就被派来服侍她。慈庆墓志说王钟儿与高贵人“有若同生”,当然是多年后追述的话,其实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且有主仆身份的鸿沟,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若同生”的。但王钟儿服侍高贵人至少有十三四年,如果双方建立了深厚的主仆之情,那也是不难理解的。
王钟儿的同事——一起服侍高照容的宫女中,有一位前面提到过的杨姓宫女,比王钟儿年轻十四五岁,同样是在刘宋丢失淮北四州的大动荡中从南朝官贵家庭沦为魏军俘虏,成了平城宫的宫女。她的墓志(志题“大魏宫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杨氏墓志的录文,请参考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69—170页。])称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刘宋在青齐地区的中上层官员(祖父杨屈为北济州刺史,父杨景为平原太守,当然州郡名和官职都未必可信,比如刘宋并没有北济州),家在清河郡(刘宋在今山东淄博所设的冀州清河郡,北魏时属齐州东清河郡)。墓志说:“皇始(当作皇兴)之初,南北两分,地拥王泽,逆顺有时,时来则改,以历城归诚,遂入宫耳。”可见杨氏是在历城沦陷后被俘入魏的,那时她“年在方笄”,也就十五六岁。墓志赞扬她“虽遭流离,纯白独著,初入紫闺,讽称婉而(尔)”,当然都是套话,不过套话也是我们想象往昔的一种依据。
杨氏墓志记她服侍高照容的经历,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文昭太皇太后选才人,充官女。”据此,十三岁的高照容被冯太后看中纳入掖庭时,二十七八岁的杨氏就在为高照容配备的宫女中,她的职级是才人,比奚官奴高了一个等级。墓志没有说她在高照容身边工作了多久,只记她后来步步高升,在宣武帝时获得宫女最高的职位内司。毫无疑问,服侍高照容、参与抚养宣武帝的经历是她后来被重用的主要原因。杨氏在高照容身边时,年长得多的王钟儿可能职级更高些,也就是说,可能与高照容的关系更亲密些。慈庆墓志说王钟儿“共文昭皇太后有若同生”,夸张后面的真实,或许就是她在服侍高照容的宫女里地位比较高。
宫女王钟儿和杨氏这样服侍后妃抚育子女者,那时有专门的称呼,即育母、保母或傅母。孝文帝诸子中,年龄仅次于元恪的是元愉(他的生年一定比《北史》所记要早几年,论证见本书第22节)。元愉的育母王昙慈的墓志,已于2018年在洛阳出土,提供了另一个研究标本[陈花容:《新见〈北魏王昙慈墓志〉考释》,《书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4—131页。]。因有“予以鞠养之恩”等语,知墓志由元愉本人撰写。据墓志,王昙慈和王钟儿、杨内司一样,出自官宦家庭(祖父是平州刺史,父亲是长乐太守),“中因家难,遂步紫庭”。值得注意的,王昙慈一直和元愉在一起,最后死在元愉的京兆王王府。墓志:“以正始元年岁在甲申十二月癸酉朔廿二日甲午(505年1月12日),春秋五十九,寝疚薨于国第。”元愉出生时,王昙慈已过四十岁,这一点和王钟儿的情况也很接近。可以推测,如果元恪后来没有被继立为皇太子,而是以亲王终其身,那么他的母亲高照容会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因而王钟儿也会一直生活在元恪的王府。
孝文帝显然是喜欢高照容的。生下元恪后,高照容又生了一儿一女,即广平王元怀和长乐公主元瑛,二人的墓志都已出土[元怀墓志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修订本)第127—128页;元瑛墓志见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第114—115页。]。据元怀墓志,元怀死于熙平二年(517),年三十,其生年当在太和十二年(488)。据元瑛墓志,元瑛死于孝昌元年(525),年三十七,则当生于太和十三年(489)。元怀墓志说元怀是“高祖孝文皇帝之第四子,世宗宣武皇帝之母弟”,元瑛墓志说元瑛是“高祖孝文皇帝之季女,世宗宣武皇帝之母妹”,但关于他们的母亲却一字不提。
慈庆墓志说王钟儿“侍护先帝于弱立之辰”,是说王钟儿从宣武帝一出生就参与了养育,是属于贴身且责任较大的宫人。太和七年元恪出生时,王钟儿四十五岁;太和十二年元怀出生时,王钟儿五十岁;太和十三年元瑛出生时,王钟儿已五十一岁。与高照容建立了一定主仆感情的王钟儿,大概一直在高照容身边,也就是说,王钟儿还参与了元怀与元瑛的养育。从元恪出生到太和二十年(496),王钟儿一直在平城宫照料高照容和她的儿女们。尽管这十几年国家多事,宫里也不太平,太和十四年冯太后之死是平城宫的一场大地震,随后孝文帝推动的许多制度变革也影响到宫中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新名号和新礼制),但对于高照容及其子女来说,同样对于王钟儿来说,这些年算得上是太平岁月。
至少从高照容的个人体验来说,这样的太平岁月一直延续到太和二十年她动身前往新都洛阳。迁都之议正式确定在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当时集大军于洛阳的孝文帝以停止南伐换来御前会议同意迁都。一个月后,孝文帝从邺城派遣叔祖安定王拓跋休“率从官迎家于代京,车驾送于漳水上”。拓跋休的“迎家”,如果是与孝文帝后宫有关的话,那也只限于地位最高的昭仪冯氏等很少几个人,与高照容这样的一般贵人无关[《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说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从平城出发“南伐”时,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从”,被孝文帝以“临戎不语内事”为由拒绝。拓跋丕所说的宫人,应该是指已被立为皇后的冯氏(冯太后的侄女)。孝文帝拒绝带她同行,有多重考虑(见后),其中之一是提防她在迁都之议中发挥负面作用。及迁都议定,孝文帝才派人去平城接她南来。]。到太和十八年二月甲辰(494年3月21日),孝文帝才正式“诏天下,喻以迁都之意”,算是正式向外公布迁都的决定。一个月后,孝文帝返回平城,“临朝堂,部分迁留”,这才正式布置大搬家。年底孝文帝到洛阳时,平城官署机构及其下属的杂役百工已经或正在南迁,但大多数官员家属都还没有动身。十二月戊申(495年1月19日),孝文帝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大概是对那些被迫突然南迁、势必遭受多方面损失的普通民众做一点点补偿。
太和十九年八月,“金墉宫成”。金墉宫既已竣工,洛阳宫也应大致完成。因此,《魏书·高祖纪》记太和十九年九月庚午(495年10月8日)“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不过,这并不是平城“六宫及文武”抵达洛阳的日期,而只是孝文帝发布诏书的日期。待诏书传达到平城,相关官民人等开始准备,不久即入冬季,平城上下至少十多万人的大搬家正式展开。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即便再仓促、再雷厉风行,隆冬祁寒,并不利于旅行,更何况老老少少家当负累。尽管各类人员中有一些很早就已络绎上道,很可能六宫出发要等到第二年春天。高照容肯定是跟着六宫大队一起行动的。正是因此,她走到黄河以北的汲郡共县(今河南新乡辉县)时[从平城宫人员南迁要经过汲郡共县,可知南迁路线是经灵丘道到定州、邺城再转向洛阳,而不是经晋阳向南到洛阳。],是太和二十年。
《北史·后妃传》记高照容之死云:“后自代如洛阳,暴薨于汲郡之共县。”高照容墓志则说:“以太和二十年……四更时,薨乎洛宫。”《北史》不具年时,根据墓志可知为太和二十年,可惜月日信息因墓志残断而不备。二者最大的差异是死亡地点,《北史》记作汲郡共县,墓志记作洛阳宫。按墓志刻写于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去高照容之死已有二十三四年(墓志称“两纪于兹”),有点差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高照容的死亡地点应从《北史》,即汲郡共县,其地距洛阳已不过数日路程,只是高照容再无机会活着进入洛阳宫了。墓志保存了她死亡的具体时间,即“四更时”,这个信息很重要[后世民间有一种说法:“一更人,二更锣,三更鬼,四更贼,五更鸡。”四更在天明之前,人的睡眠最深沉之时,所谓“窃得狐裘转四更”。《缀白裘》卷三《雁翎甲》之“盗甲”有这样的念白:“阿呀,你听,已是四更了。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见汪协如点校本《缀白裘》,中华书局,2005年,第152页。],说明对她的谋杀发生在夜深人静之时。执行谋杀的人来自洛阳(至少他的使命来自洛阳),他在共县等到了平城宫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然后在人人熟睡的四更时分进入营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这时元恪十四岁,先应已到洛阳,可能正在对自己突然被优待大惑不解、受宠若惊,却不知道自己成了一场宫廷阴谋的重要棋子,更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会是这场阴谋最主要、最无辜的受害人。元恪的弟弟元怀这时才八九岁,妹妹元瑛七八岁,大概都是和母亲在一起的。有理由相信,王钟儿是跟着高照容及其子女一起南迁的,这时正在汲郡共县的大营里。高照容遇害后,王钟儿必定是最早见到不幸场面的人之一。她虽然在平城宫为奴近二十七年,经历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不过高照容的惨死一定是她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的,因为和元恪一样,她哪里知道这竟是一场大阴谋的第一步。
这时王钟儿已经五十七岁了,在她为高照容之死唏嘘伤感时,她肯定想不到,造成高照容惨死的这场阴谋也会牵扯到她,以至于她不得不出家为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