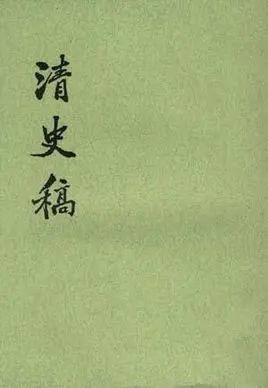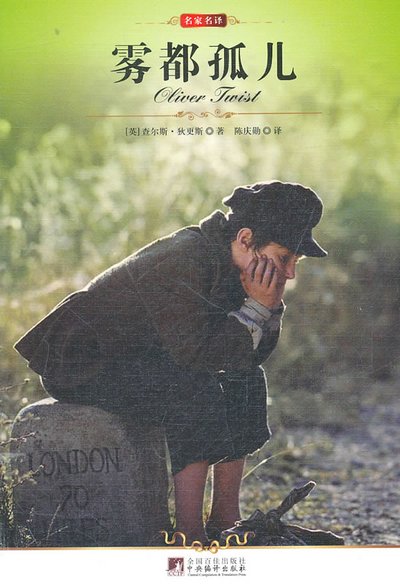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也曾记述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一些情况,他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后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
那个时候,江青虽然还没有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她常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本传前面已经讲到了。因此,她对戚本禹叙述的那种情形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1949年7月选入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5月4日调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任见习秘书;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历任秘书、《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成员、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当局强行为他办理了一个“戚文”的身份证,那承想这易名竟成谶语,后来果然以“文”闻名于世。他与关锋商定在文化战线上继续革命,编著了近200个历史人物、计200余万字的《中国历史人物论集》,与关锋等人合作编撰了《中华易学大辞典》、《论语释说与孔子批判》,还出版了他撰写的、与人合作的十几本著作。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就在他逝世前一小时,他曾花费了5年时间撰写并抱病审定的《戚本禹回忆录》,由香港友人出版了。
这正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 龚自珍诗)
且说在5月20日,毛泽东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说:
“徐州失守(5月19日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中主动撤离徐州,向西向南突围。见上一章——笔者注)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中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5月26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他的开篇语讲的是“问题的提出”,他说: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么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花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
毛泽东的这个讲演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全部结束。他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战争双方的基本条件,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一客观规律。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抗战必将出现的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一科学预见最终被历史事实所验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论持久战》之后,曾这样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再说5月26日晚,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及其外婆周陈轩、舅父周颂年,已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回到韶山定居,但生活困苦;毛家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还询问他的侄子毛远耀等在延安的情况。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时绥!
弟 毛泽东 5月26日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闻知开封失守,大吃一惊。这个早年曾4次东渡日本深造并先后毕业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校的炮兵生、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的士官候补生,为阻止日军西进占领郑州,竟生出了一个馊主意,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可非同小可,瞬间便造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
这正是:倭寇铁蹄踏开封,吓煞当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兀自生出个“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还有什么愚蠢之举?请看本传后面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满城遭焚之惨状。
东方翁曰:本章前面说到了毛泽东在1938年5月初会见美国情报官卡尔逊时谈到了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则说:“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后来的情况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就在毛泽东发出这一预言之后不久,极力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9月同法、德、意首脑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签订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以此推动德国向苏联进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此后,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9月1日又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但并未组织进攻,出现了前线无战事的“奇怪战争”。1940年4月,德国军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占丹麦、挪威,5月10日至5月28日,攻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其间在5月13日大举入侵法国,驻防法国的英军这才慌忙从敦刻尔克大撤退,损失惨重。你看,毛泽东不寻常的预言,不仅仅是结果,连方位都说准了。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说过,毛泽东早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高兴和沉痛》一文中,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他说:“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10年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说来真是太神奇了,就在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在巴黎和会上参与分赃活动20年之后,法国被迫在一战结束时德国向其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这岂止是大大的头痛,简直是亡国灭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