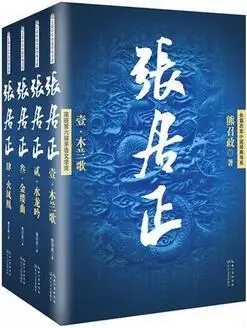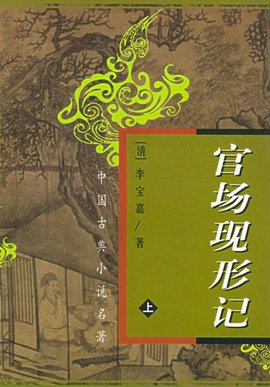毛泽东话头一转,又说道:
“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派的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嘛。”
再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
7月26日这一天,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学开会。他准时到达后,发现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声问康生:
“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的会?”
康生说:
“我也不清楚。”
江青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学校的两大派别辩论工作组的错误,让一些学生控诉工作组的罪行。
康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1、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2、北大50天来,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国际歌中是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线要在实践中证明,张承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文革委员会,有人说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张承先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吗?北大是执行新市委的领导,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他就不是党的领导。请问:你们对北大的情况了解,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陆平、彭佩云黑帮是张承先了解,还是你们了解?斗争陆平不是靠几个秘书整理材料,而是靠你们来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赞、李世雄、冯定,开展和他们斗争是你们了解,还是张承先了解?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还是张承先看他的书多?你们说靠谁斗?靠你们!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江青接着也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十分鲜明的讲话。最后她提议说:
“欢迎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面对群众热烈的掌声,毫无准备,不知该讲些什么,他站起来说:
“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江青马上插话说:
“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李雪峰说:
“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提,但应该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来提,因为工作组毕竟不是黑帮嘛。你们不要工作组,工作组可以撤离,也可以留在学校,你们什么时候要揪去批判,我们随时到场。”
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
“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
李雪峰主持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并作了几句检讨。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话。刘少奇说:
“工作组这个方式现在看来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要靠你们来搞。靠我们不行。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现在看来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周恩来、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大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与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见了面。尔后他告诉刘少奇等人说:
“你们都要到前线去看大字报。不然,没有资格领导运动。”
会后,中共中央将这次大会的录音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关于这次大会,《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3楼。这样一来,3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 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自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3楼,然后3楼、1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就在这7月底,刘少奇开始写他的检查,题目叫:《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在这份检讨提纲草案中,关于他的履历部分写有这样一段话:
“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
这一段文字扯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61人的“叛徒集团”问题。很明显,刘少奇在这里不但把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柯庆施,还推给了当时的中央主管人张闻天和康生,而身为北方局书记的他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不久,这一公案便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恐怕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正是:剑走偏锋,一石激起千层浪;招出奇险,城门失火殃池鱼。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不少列席人员。这些列席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
关于高校师生代表,《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师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论。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入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3、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手续。4、通过会议公报。
接着,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他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他说:
“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插话说:
“怎么会中断呢?”
陈伯达在刘少奇的报告结束后作了发言,他说:
“派工作组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插话说:
“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接着说:
“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就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陈伯达又讲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泽东插话说:
“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7月31日,他收到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于7月28日要江青转呈的6月24日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4日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他们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很好,便在回信中写道: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由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有直接寄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
8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陶铸在文化革命小组中排名在康生之前。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以后,参加全会的代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分头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主要是去看大字报。
8月2日和3日上午,李雪峰陪着刘少奇、陶铸陪着邓小平去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
据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我陪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搞调查看大字报的时候,刘少奇还在为工作组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有成绩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可以继续辩论。历史和实践将会继续检验这个问题。’当时我一听就为他着急: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讲这个话,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不是继续在坚持错误吗?我曾经劝刘少奇先别谈什么工作组的功过问题,但刘少奇似乎听不进去。他还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希望你们要团结。’3日到学校的时候,他和两派都谈了话,也是要求他们讲究政策,等等。其实这时他的一切活动都显得多余了。到这个月初,他的儿子刘允斌回家来,向刘少奇汇报工厂的情况,他竟然问道:‘你们厂没派工作组,为什么也镇压了群众?把一些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有没有死人呀?’实际上,他从心里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压得他不能公开说话,只好闷闷不乐。在那种气氛下,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只好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刘少奇气坏了。他激动地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刘少奇开会的时候,把我叫到休息厅,悄悄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看你们都检查吧,能够认识到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不要违心地说什么,但是也不要公开地顶他们。连我的女儿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何况你们呢?等党内的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也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只认识新市委主持工作时的错误,我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这点,请少奇同志放心。’”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得多,说的少。”
8月3日, 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 给他们看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那一封回信 。
这样,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中国。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各地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造反有理”的思想,从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 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同时,这封信一经公布,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红卫兵的根本对立的态度,也就清楚地摆在了全国人们面前。在红卫兵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更加强烈起来。更加明显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自此以后,凡是与工作组和“老文革”对立的反对派“新文革”,均自称为造反派,而把“老文革”称之为“保皇派”。“老文革”和“新文革”两派之间又发展到互相攻讦,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以至于扩展到社会上,人人都以能获得造反派的头衔而引以为荣耀。于是,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这是毛泽东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只有主义之争,辨明是非尔后宽以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