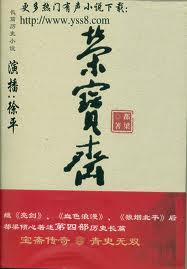切·格瓦拉(上)

当埃内斯托于1928年出生在阿根廷时,他的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小不点将和千里之外的古巴革命产生联系。
他们家世代贵族,出过总督、首富、将军,就是没有诞生过任何革命者。
“革命”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
然而,天上的星星有时也会落在地上,有的人就是会背叛他的阶级,这种人极其少见,但他们出现时也格外耀眼。
列宁的父亲是沙俄官僚世袭贵族,恩格斯的父亲是工厂主,但他们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埃内斯托也终将追随他们。
那时他会有一个新名字——
切·格瓦拉。

童年 切·格瓦拉 图源:网络
01
埃内斯托·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这位未来古巴革命的领导者一开始甚至不是古巴人。
他出生于阿根廷的上流阶层,父母都是贵族,他们一家人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丰厚的遗产。
虽然格瓦拉的父母多次投资失败,但在他们最穷的时候,他们依然住的是别墅,有自己的汽车,外出度假要雇三个佣人,他们还有一大帮富翁亲戚。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格瓦拉本该无忧无虑,但他天生患有一种很麻烦的疾病——哮喘。
直到今天,哮喘都是无法根治的。格瓦拉的父母遍寻医生,花了无数钱,也无法帮儿子免除病痛。
格瓦拉的哮喘没有什么规律,随时都有可能发作,而且发作起来非常严重,屡屡出现窒息的症状。
在哮喘的折磨下,格瓦拉的童年时光有些孤独,每次哮喘稍有发作,他都得待在家里,不得走动,读书成了唯一的消遣,也正是这些与世隔绝的时光,让格瓦拉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他的阅读量一直远超同龄人。
而只要哮喘不发作,格瓦拉就会跑到外面去玩。
作为一个哮喘病人,他的胆子大得惊人,他踢足球、打乒乓、上山远足、下河游泳,甚至还会打群架。
这其中他虽然多次因呼吸困难而倒下,被朋友送回了家,但他下一次还是一定会跑出去玩。
格瓦拉的父母渐渐意识到,他们的孩子是一个热爱冒险、精力异常旺盛的人。
在上流阶层中,格瓦拉的父母也算是很特立独行的人,一般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和底层人民有来往的,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用一系列严格的社交礼仪来维持他们所谓的贵族范。
但格瓦拉的父母不是这样,他们随意和各色人等交朋友,也从来不会限制孩子去交什么朋友,不论是高尔夫球童还是贫民区的孩子,只要跟着格瓦拉走进家门,都会受到款待。
格瓦拉的母亲还经常开车送他们上学,她堪称是一个先锋女性,她是当地第一个开车的女人、第一个穿长裤的女人。她还自掏腰包在学校开创了“每日一杯奶”的活动,让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保证营养。
他们一家人还不信教,这在当时是很少见到。
他们不会去做弥撒,不会去参加宗教活动。只是顶着一个徒有其表的“天主教徒”名号,以防被当时的保守社会所排斥。
在父母的要求下,格瓦拉没有上过宗教课程。
就是在这样一个开明、无拘无束的资产阶级家庭中,格瓦拉一点点长大。
他无所畏惧、固执、热爱竞争、喜欢领导别人,他对外面的世界有着无穷的好奇。
1938年十岁的格瓦拉发现他们城市里来了一伙外国人,一群流亡的西班牙左翼。

02
西班牙内战是格瓦拉人生中经历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虽然这件事发生在遥远的地球的另一边,但阿根廷和西班牙之间特殊的文化纽带也让这个十岁的孩子有了感同身受的体会。
阿根廷曾经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殖民时代早已过去,但文化、血缘上的亲近仍然保留了下来。
大量的阿根廷人都是西班牙后裔,甚至连阿根廷的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
所以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阿根廷成了西班牙左翼流亡者首选的避难地之一,他们带来的政治氛围迅速影响了格瓦拉一家。
格瓦拉的童年玩伴佩佩·阿奎拉尔,他的父亲就是西班牙左翼的一名海军军医长,这个男人一直坚持战斗到了1939年1月,直到巴萨罗那都沦陷了之后,才赶来阿根廷和家人相聚。
在这些左翼流亡者的影响之下,格瓦拉也变得反对起法西斯来了。
他给自己的宠物狗取名内格林娜,以此向左翼政府总理胡安·内格林致敬。
他还对战争形势格外感兴趣,会用小旗子在地图上标注出左翼军队和右翼军队的位置,虽然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最终输了,但在小小的格瓦拉心中已经播种下了一个反独裁、反法西斯的种子。
西班牙内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也爆发了。
虽然阿根廷没有受到战火摧残,但纳粹势力仍然对这个国家有所渗透。
当时阿根廷的副总统拉蒙·卡斯蒂略就表现出了亲轴心国的倾向,他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和德国有利益往来,为纳粹势力在阿根廷的渗透、宣传大开绿灯。
还有一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希望阿根廷能彻底倒向轴心国。
格瓦拉追随父亲参与到了与他们的斗争之中。
格瓦拉的父亲是阿根廷行动党的成员,这是一个反法西斯、亲同盟国的党派。
格瓦拉在11岁时就加入了阿根廷行动党的青年团,并颇为骄傲地展示他的团员证。
父亲记得:
“除了娱乐和学习之外,他都一直和我们待在一起。”
在监视纳粹分子盘踞的宾馆时,格瓦拉还遭到过枪击,所幸对方没有击中他。
这些年少时惊险刺激的经历,塑造着格瓦拉的性格。
他对政治还谈不上有多么了解,但已经有了一种朴素的正义观,他关心世界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格瓦拉成长的另一种途径是通过书本。
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的阅读量就已经足以让成年人咂舌了。
他的橄榄球队教练发现,每当他们在等球场空出来时,格瓦拉就会坐在一旁看书。教练自己也很喜欢读书,但他无法理解格瓦拉怎么会读过这么多书。
这个15岁的孩子已经读完了左拉的大部分作品,他还看过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以及威廉·福克纳和斯坦贝克创作的当代美国文学作品。
因为母亲从小教他法语,所以他还读了大仲马、魏尔伦和马拉美的法语原版著作。
眼下,他正在读佛洛依德的书和波德莱尔的诗。
据朋友佩佩回忆:
“他渴望阅读,完全占领了父母的书房。”
等到17岁的时候,格瓦拉读过的书就已经很难一口气念完了。
这些书的作者中,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马克思。
是的,在17岁的时候,格瓦拉就已经读过《资本论》了,但他发现自己读不懂,一方面是马克思厚厚的三卷本巨著确实不太易懂,另一方面是格瓦拉也没有动力去研究他们,他毕竟是出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对于残酷的现实还没有多么深刻的体会。
那时,他只是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诸多政治派别中的一种,甚至于在他总结的第一版哲学笔记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都是来自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个荒谬的程度就类似于从宗教典籍中了解自然科学。
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格瓦拉纠正了这个错误,并且对马克思和列宁的生平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但他仍然没有想过要把共产主义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他只是对这些人感到好奇。
格瓦拉的这种态度也可以理解,因为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满。他出身富贵,考上了首都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医学院,他有着大好前程。
他的国家是南美洲数一数二的大国,正在胡安·庇隆的领导下,向着经济独立和工业化迈进。

胡安·庇隆(1895年10月8日—1974年7月1日) 图源:网络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格瓦拉心中的火苗从未被点燃,直到某一天,他决定去外面看一看。
03
当熟悉的城市被抛在身后,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多么辽阔。
格瓦拉热爱旅行,热爱这种不断前进、探索世界的过程。
他一开始只是在往返两个熟悉的城市时采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比如明明可以直达,但他非要用步行和搭顺风车的方式过去。平常十小时的车程他要花上72个小时,但他就是如此享受这个过程。
旅途上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新鲜的,只有在旅游的时候,格瓦拉才感到最自由。
1950年1月1日,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他骑着自行车一路向北,在六周的时间里穿越了阿根廷的12个省。
这一路上他有很多奇遇,他曾搭在一辆车后面,以60公里的速度向前狂飙,结果自行车的前轮爆了,格瓦拉摔在了路边的一个草垛上,吵醒了正在那里睡觉的流浪汉,最后两个人反倒聊了起来,流浪汉还为他泡了茶。
他曾在科尔多瓦北部的瀑布区露营,爬上高处,又跳进水潭之中,差点被山洪冲走。
在这些惊险刺激的事情之外,也有一些事情开始触动格瓦拉的内心。
当一名医院员工问他在旅途中看到了什么时,他说:
“我看到的和一般游客不同,在游客指南上,有祖国祭坛,有大教堂,有祭坛珠宝,还有布兰科河圣母和庞贝圣母。但是,不应该通过这些东西来了解一个国家,这只是一个华丽的外表,而反映它灵魂的是医院里的病人、警察局里被拘留的人,还有碰巧认识的过路人,就像格兰德河的河底才显示出它的湍流一样。”
格瓦拉还发现,在阿根廷贫穷的北部有大片土地无人居住,人口主要聚集在了几个城市里,而这些城市被少数几个政治家族把持着,他们享有无限的财富和特权,他们先辈在几百年前建立的殖民体系至今仍然持续着。
印第安人只能住在自己搭建的、简陋的棚屋里,他们要么当佣人,要么在工地上干体力活,并且饱受白人的歧视。
戈瓦拉自己也属于白人精英,但这一次他远离家庭,独自旅行,所以常常身处在这些贫穷的印第安人中间。他第一次没有把这些人看成是仆人或者抽象的符号。
他意识到,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
这次长达4000公里的旅程让格瓦拉收获颇丰,他的眼界被大大拓宽了,对冒险的热情也被进一步激发了。
虽然他眼下不得不返回学校继续学业,但他盘算着未来还要进行一次更遥远的旅行。
在政治上,格瓦拉也表现的非常有主见了,他不再轻信长辈的话,而是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谈起刚刚爆发的朝鲜战争时,他的父亲支持美国人,而格瓦拉则坚决反对,他指责美国人摆出了一副帝国主义姿态。
还有一次,他去女朋友家里做客,他女朋友一家都是亲英派,在饭桌上,每个长辈都讲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关于丘吉尔的故事,而格瓦拉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在听故事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之情,最后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这个备受你们崇敬的人物,只不过是另一个作秀的政治家。”
他女朋友的父亲听到这话后,气得直接离开了饭桌,而格瓦拉却笑了起来。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格瓦拉已经变了,他没法再融入贵族中间,高谈阔论,惺惺作态。
他仍然在继续学医,按照大家期望的、为一种体面的生活而努力,但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课程和考试,真正让他向往的是远方、是流浪。
而他的朋友阿尔贝托(Alberto Granado)正好在准备一次远行。
阿尔贝托是一家诊所的药剂师,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花一年时间穿越整个南美洲,最后抵达美国。
他的家人都将其视作白日梦,只有格瓦拉会认真和他讨论。
“我们幻想到达遥远的国都,航行在热带海域上,游览所有的亚洲国家。突然间,一个想法浮现出来,如果我们去北美呢?去北美?怎么去?骑‘威猛’去啊,朋友!”
——切·格瓦拉《摩托日记》
“威猛”是阿尔贝托的一辆老式摩托车,排量500CC,英国诺顿牌。
这辆12年前产的摩托车,是这两个男人仅有的交通工具,他们要骑着这一辆摩托在20世纪50年代穿越地形复杂、基建极不完善的南美洲。
这个计划简直是疯了,但格瓦拉和阿尔贝托正好是疯子。
阿尔贝托马上就要30岁了,他意识到自己再不趁着年轻的时候行动一次,就永远无法实现这个计划了。
而格瓦拉也已经受够了医院和考试,受够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他们两人一拍即合,一起喝着马黛茶起誓:
“不达目的地绝不回头。”

04
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所有的路线都是靠拍脑袋决定。
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但当他们跨上摩托车点燃引擎的时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真的上路了。
“此刻,不在乎前方会有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眼里只有飞扬的尘土。在这满天飞尘中,我们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向北驶去。”
这一次,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走得更远。
他们花了四周多的时间穿越祖国,他们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奔驰,在大湖区狩猎野鹿,最后抵达了森林密布的安第斯山脉。
翻过这座雄伟的山脉,他们就跨过国境线,抵达了智利。
此时,他们的钱已经快花光了,两个人只能骑着摩托车到处蹭饭,格瓦拉将其称为“机动化乞讨”。
经过不断实践,他们很快成为了吃白食的专家。
他们会故意在智利人面前用夸张的阿根廷口音交谈,以引起智利人的注意,这通常会打破沉默,令双方开始交流,他们正在进行的旅途是一个很好的话题,聊着聊着,阿尔贝托或格瓦拉就会开始提起他们的困难,而另一个人则补充说,今天“刚好”是他们出来旅行的一周年纪念日,接着他们就会感慨没办法庆祝这个日子。
他们的表情是如此遗憾,让智里人感到必须得请他们喝上一杯,而两个人则不停推辞,这怎么能行呢、这多不好意思呀、我们也没法报答你呀,直到智利人再三坚持,他们才“勉为其难”地不再推辞。
上了酒桌后,刚喝一点酒,格瓦拉就不喝了,请客的人当然会劝格瓦拉接着喝,格瓦拉则毫无理由地继续拒绝。
在不断逼问之下,格瓦拉才会“十分不好意思地承认,我们阿根廷人的习惯是一边喝酒还得一边吃饭。”
除了这种套路外,格瓦拉和阿尔贝托还善于利用人们对医生的尊重,他们一个是还没毕业的医学生,一个是药剂师,都不算是专业医生,但他们脸皮很厚,在拜访报社时,他们狠狠地自我吹嘘了一番,说自己是“麻风病专家,在附近几个国家都做过研究”。
智利的记者完全相信了他们的话,在报道中写道:
“他们在我国短暂停留期间,深入考察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卫生问题。”
报纸上还附有他们的照片。
格瓦拉和阿尔贝托就拿着这份报纸到处骗吃骗喝。每当他们拿出报纸表明自己“医学专家”的身份时,对方往往都会流露出敬佩的神情,然后把他们热情招待一番。
格瓦拉得意地将这份报纸称为“我们厚颜无耻的精华”。
然而,装医生装久了,也真的会有人来找你治病。
在圣地亚哥,格瓦拉就被请去给一个老妇人看病,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躺在一个小小的、肮脏的房间里。
格瓦拉一走进去,就闻到了浓烈的汗臭味,那里面只有几把落满灰尘的椅子,把老人的腿都弄脏了,她的家人对她也不好。
“在这些贫困家庭里,病人往往被家人粗暴地对待,这时他(她)已不再扮演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的角色了,而是变成了一个被健康家人所怨恨的负面人物,因为他(她)不仅不能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反而需要别人来照顾。”
——切·格瓦拉《摩托日记》
格瓦拉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进行诊断,发现老人患有慢性哮喘,心脏也很不好,已经没救了,她快要死了,她操劳一生,最后却只能在这个小小的、肮脏的房间里,在家人冷漠的眼神中,毫无尊严地死去。
这一幕深深地刺激了格瓦拉,他意识到:
“这便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经历的深刻悲剧,他们的生活被掩埋,看不到未来。在这些垂死病人的眼睛里,有一种祈求原谅的屈服的神情,很多时候还有一种渴求宽慰的绝望的神情。
但他们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他们的身体也很快将被周遭的世界所吞噬。我不知道这种可笑的、基于阶级分层的社会秩序还要持续多久,我无法回答。”
格瓦拉力所能及地给老人留了一些药,但他也知道这些药已经没什么用了。
“面对这些底层的人民时,我多希望能改变他们的状况,能消灭这些不公。”
格瓦拉默默离开了房间,那一年他23岁,心里有一团火在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