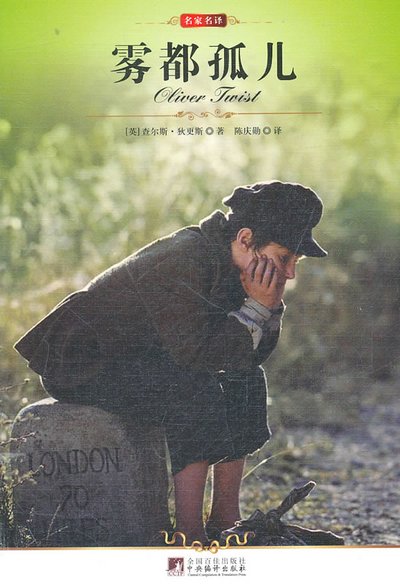中原的早春,虽然还是寒风料峭,却已经悄悄地染上了一抹春色。路边的草儿钻出了嫩黄的芽儿,柳树的枝条迫不及待地换上春装,抖落出一串鹅黄。一大早,祖逖和银屏带着两个侍卫出了雍丘城,扬鞭西去。马踏晚霜,留下一行蹄印。
他们要去尉氏,赶在春播之前看看王玄,也看看童建。童建去尉氏一个多月了,不知他和王玄合作得如何?
上元节之后,祖逖又一次找到童建,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意干什么?童建直截了当地说尉氏缺一个督护,愿意去尉氏。祖逖想问,是钱凤说的吧?话到嘴边,最终没有问,同意了他的要求。尉氏的几百名士兵是陈留太守王玄亲自招募的,也是他亲自训练,虽说这位年轻的官员恪尽职守,不辞劳苦,但政务、军务一肩挑也够他劳累的,派童建去分担一些,也能减轻他的负担。祖逖征求了一下王玄的意见,王玄没有什么异议,祖逖就亲自把童建送到尉氏。在尉氏的一个多月里,童建一直没有提委任状的事。
百十里地,一个时辰之内,尉氏的城池已经遥遥在望了。
城外的一块空地上,童建正在率领士卒训练,祖逖他们走近训练场,下马驻足观看。童建也发现了他们,但他没有停止训练。童建在上大木山之前,也在军队里当过下级军官,只因为抢人妻子,和人斗殴,破了相,没脸在军中呆下去了,才上了大木山占山为王,干起了没本的生意。训练几百个士卒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你看他推、挡、劈、刺,闪、转、腾、挪,一招一式,不厌其烦,还真像那么回事。刚刚改变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倒也很卖力气,把棉衣都脱了。直到训练告一段落,他才走过来和祖逖他们见礼。祖逖邀他一同去见王玄,童建把训练士卒的事交给下属,穿上棉衣,陪祖逖进城去了。
祖逖和王玄虽然年龄差了二十来岁,但因为他们在洛阳时早就认识,在抗击石虎的战斗中,王玄又慨然相助,而尉氏又在豫州管辖范围之内,他俩已经成了有别于上下级关系的忘年之交。中午,王玄留祖逖吃饭,祖逖也就没有客气。王玄让童建作陪,童建犹豫了一下,祖逖开玩笑地说:“你我都是为朝廷卖命的,我们是一家人,你还客气什么?”这句话,让童建很感动,他留下了。
席间,祖逖问了一些尉氏的情况,然后他说,去年的水灾、沥涝把我们弄得很艰难。今年一定要鼓励老百姓把地种好,只要老百姓手里有了粮食,官府的仓库里才有粮食,我们才有力量渡河北伐,消灭石勒。目前,豫东、豫南都是我们的地盘了,豫西有李矩、郭默、赵固他们顶着,黄河以南几乎没有石勒的势力了,一旦今年老天开眼,粮食丰收,明年我们就联络黄河以南所有的坞主和豫西的李矩、郭默、赵固他们,大举渡河。北方的刘琨、段匹磾一定会遥相呼应。两面夹击,不愁石勒不灭。然后,南北军队合二为一,西征诸胡,一举荡平北方,晋朝的失地就全都收回来了。说到这里,胸中豪气勃发,端起酒碗,一饮而尽。
王玄知道祖逖是如何争取到北伐的使命,也知道他这几年是怎样转战中原,为收复失地鞠躬尽瘁的,他对祖逖佩服之至,敬仰之至,所以在石虎大举进犯的紧要关头,他才倾其所有,支援祖逖。今天,他听到祖逖发自心底的豪言壮语,深为感动,他也端起酒碗,诚恳地说:“眉子甘愿听从祖豫州驱策,但有战事,尉氏的兵马任由祖豫州调遣,你的北伐大业,将永远有了追随。”
祖逖听了,深受感动,他站起来,端起酒碗和王玄碰了一下,一口喝干了。
最后,祖逖嘱咐童建:“既然来到北伐军,就是一家人,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好好干,我们不会亏待你,王玄更不会亏待你。”
送走祖逖,童建回到自己的住处,心里很矛盾,祖逖的心,日月可鉴。王玄对朝廷忠心耿耿。而且王玄又是王家族的成员,是王敦、王含的侄子,一家人为什么还要这样防范呢?钱凤临走的时候一再叮咛,要他密切注意祖逖的动向以及祖逖和王玄的关系,随时向他报告。祖逖的战略意图,已经当着我的面毫不掩饰的倾吐无遗,王玄的表态已经说明他和祖逖结成了联盟,共同北伐,收复中原。他们光明磊落,我为什么要向大将军他们报告呢?可是他又不得不时时记着钱凤对他的威胁:“如果你知情不报,或者背叛我们,你将会死无葬身之地,王大将军在朝廷中的分量你不是不知道。”钱凤他们要干什么?这个头脑简单的前山大王困惑了。
一夜无眠,童建不得不从自身的安危考虑,他不想死无葬身之地,好死不如赖活着,他最终还是写了一份报告,派他的心腹给钱凤送到武昌。
钱凤接到童建的报告,忙不迭地给王敦送去。王敦看了,怒火中烧,一拍桌子:“好个孽子,竟敢投靠祖逖!告诉童建,把他宰了!”
王敦身材高大,一发怒,横眉立目,倒也有些将军相,只是太胖了点儿,眼睛也凶了点儿。
钱凤听了,犹豫了一下:“这……王玄可是王氏家族的人,大将军的侄子。”
王敦瞪了钱凤一眼,凶相毕露:“管他是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钱凤不敢再说什么,慌忙出去布置。剩下王敦独自在大厅里生气。
王敦是琅琊王氏家族的成员。我们说过,晋朝是士族社会,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制度,只要是士族家庭的子弟,不管是否有能力,都要给个官儿做做。琅琊王氏是高级士族,是汉朝谏议大夫王吉的后代。往近里说,大家还记得王祥卧鱼的故事吧?王祥就是王敦的叔伯爷爷。王祥幼年丧母,父亲给他娶了个继母,继母不喜欢王祥,经常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因此父亲也就不喜欢他了,常常让他打扫牛棚马厩。但王祥很孝顺,父母有病,他亲尝汤药;继母想吃鱼,他到结冰的河面上,脱掉衣服用自己的体温破冰求鱼,这时两条鲤鱼跳出冰面,他拿回去给继母吃;继母想吃黄雀,就有数十只黄雀飞到屋里。家里有一棵沙果树,继母让他去看守,每逢刮风下雨,他抱着树哭泣也不敢回家。父母死了,王祥在坟前守孝,弄得身心憔瘁,扶着拐杖才能站起来。王祥的孝行使他名声大振。徐州刺史吕虔请他做别驾,把州里的事委托给他。当时强盗横行,王祥率兵士讨伐,屡屡获胜。徐州社会稳定,政治清明。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曹魏时期王祥就官至太尉,到了晋朝,做到太保,兼睢陵公。活到八十五岁才去世。
王祥有一个继母所生的弟弟,叫王览,字玄通。他对王祥很好,幼年时,母亲虐待王祥,王览就经常劝说母亲,王览怕继母在王祥的饭里下毒,吃饭时王览就拿过来先嚐,母亲只好夺下来倒掉。王览怕母亲杀害王祥,就每天抱着王祥睡觉。王祥被鞭打时王览就抱着王祥一起承担。继母让王祥做力所不能及的事,王览也和王祥一同去做。继母虐待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也一同承受。
由于王览孝悌,在当地也很有名气,仅次于王祥。王祥进入仕途以后,他也进入本郡官府,后来当了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泰始末年,任弘训少府。转太中大夫,奉禄与卿同。咸宁初,朝廷下诏:“览少笃至行,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其以览为宗正卿。”后转光禄大夫。
徐州刺史吕虔有一把佩刀,有擅长算卦的人告诉他,必登三公之位,方可佩此刀。吕虔对王祥说:“不配佩戴这把刀的人,拥有了它,可能成为祸害。休徵有公辅之量,所以我把刀赠给你。”休徵是王祥的字。王祥再三推辞,吕虔一定要送给他,王祥才勉强接受了。王祥临死,把刀送给了王览,说:“你的后代必然兴旺,足配此刀。”王览的后代果然位极人臣,把持朝政,支撑起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当时有一句谚语:“王与马,共天下。”王,是王氏家族,马,就是晋朝皇帝司马氏。
王览有六个儿子,王敦就是王览次子王基的儿子,字处仲。王导是王览长子王裁的儿子,字茂弘。王玄的父亲西晋太尉王衍是王祥的另一个兄弟王雄的孙子,和王导、王敦是同一个辈分,而王玄则是王敦的侄子,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同辈。
王敦年少时人还不错,从不言财色,他的眼睛特别锋利,和常人不一样。娶晋武帝的女儿襄城公主,官拜驸马都尉,太子舍人。只是有些残暴,通俗地说就是心太硬,当时王恺、石崇互比豪侈,王恺设宴,王敦与王导都在座,有女伎吹笛稍有差错,王恺便把她杀了,在坐的人都为之动容,唯有王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访王恺,王恺让美人行酒,怪美人不能令客人尽兴,又杀了。酒至王敦、王导那里,王敦故意不肯端杯,美人又悲又惧,而王敦视而不见。太子洗马潘滔说:“处仲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
在晋元帝司马睿初临江左,避乱建业的时候,王敦和王导是出了大力的,他们一文一武,帮司马睿树立威望,招揽人才,统领兵马,等到大业初成,司马睿登基做皇帝的时候,还拉王导同坐龙床,王导坚辞不受,司马睿这才作罢,以王导为丞相。
元帝以王敦为安东军谘祭酒,后又任命他为扬州刺史,加广武将军。不久为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平定杜弢以后,又进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封为汉安侯,坐镇武昌。这时,他实际上已经把持了东晋的军权,于是他的野心开始膨胀,《晋书》上说:“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专任阃外,手控强兵,群从显贵,威权莫贰,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在他的辖区里,他竟然自作主张安排军队和地方的官员,培植自己的势力,而不必经过朝廷批准。他经常在酒后吟唱曹操的乐府《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唱,一边用如意敲打唾壶,即痰盂,把痰盂的边打出许多缺口。有一次他的堂兄王澄路过武昌来看他,他历来不待见王澄,竟亲手杀了王澄。
王敦素来忌惮刘琨,他在后汉国都之侧,卓然独立,可见此人非同小可,王敦既有问鼎之心,就必须想办法除掉此人,好在刘琨丢了并州,投奔段匹磾,帮他找到了口实,于是他以朝廷的名义,下诏给段匹磾,让他杀掉刘琨。
他起初并没有把祖逖放在眼里,但祖逖在中原的日渐壮大,使他意识到了祖逖很可能成为他实现其野心的巨大障碍,但他对祖逖暂时还无计可施,恰巧这时候传来王玄要和祖逖联手的消息,他岂能容忍!一怒之下,他下达了杀掉王玄的命令。
王玄被害的消息传到雍丘!
祖逖感到震惊,他刚刚从尉氏回来不久,在尉氏,他和王玄谈得很融洽,王玄决心投身到祖逖的旗下,参与北伐,使这一对忘年之交的友谊更加深厚了。目前暂时没有战事,祖逖从尉氏回来,除了命冯宠、樊雅、谢浮和董昭等人密切监视黄河沿岸之外,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一方面鼓励农民多种粮食、棉花,一方面把剩余的土地分配给北伐军各营和各地的地方武装,把因战乱撂荒的土地尽量屯垦出来。一是解决因为去年的水灾所造成的饥馑,二是要聚集大量的粮草,为明年的北渡黄河做好物质准备。为此,他把谢浮、桓宣、冯宠召集到雍丘,冯铁、卫策和韩潜就在身边,祖逖和他们商讨屯垦事宜。
春节过后,他的儿子祖涣从淮阴来到雍丘,祖涣也参加了会议。这小伙子十七岁了,长得很像祖逖,只是略显单薄,胡须还没长出来,嘴唇上只有一些浅浅的绒毛,自幼经祖逖亲自指点,再加上他勤学苦练,武功倒也不弱。
听到王玄被害的消息,祖逖匆匆结束了会议,命谢浮回太丘,冯宠回浚仪,冯铁守雍丘,自己带着桓宣、韩潜、卫策和祖涣急急忙忙奔赴尉氏。
王玄的灵柩停在太守府邸的大厅里,厅里院内一片凄然的白色。王玄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在灵前守灵,两眼哭得红红的。丧礼由王玄手下的小头目料理,没有主事的人,显得有些零乱。
祖逖取出在雍丘准备好的挽联,由操办丧事的人挂在厅外的明柱上:
公去大名留史册 悲声难挽流云住 翠色和云笼夜月
我来何处别音容 哭声相随野鹤飞 玉容带雨泣春风
祖逖等人在灵堂为王玄烧化纸钱,上香,祭奠,王玄的妻子还礼。
祖逖走到王玄妻子面前,悲痛地说:“夫人,请节哀。”
王玄的妻子弯腰施礼:“谢刺史大人。”
祖逖问:“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昨天晚上因为公务繁忙,太守没有回后院,今日清晨就有下人报告说……”
祖逖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问道:“童建在哪儿?”
下人禀报:“从早晨到现在都没见到督护大人。”
韩潜脑子里飞快地旋转,从大木山上发现童建和王含、王敦兄弟的关系到钱凤神秘地现身雍丘……这里面有什么联系吗?于是他对祖逖说:“咱们到童建屋子里看看。”
祖逖看看韩潜,很快地把听到和看到的几件事链接在一起,点了点头。
童建的住所在府衙的厢房里,门锁着。下人打开房门,迎面一股血腥味儿扑来,地上一块拭刀的抹布上沾满了鲜血,桓宣捡起来一看:“看来童建并不想掩饰。”
童建的屋子很简单,床上只有简单的被褥,几件衣物已经被他带走了。褥子下面有以朝廷的名义下达给他的诏书。桓宣拿起来看了看,递给祖逖,说:“一切都明白了,是王敦幕后指使的。”
“王敦想干什么?”
“以后你就知道了。”
韩潜说:“童建一定是投奔王含去了。”
桓宣说:“王含已经不在扬州,到朝廷里当光禄勲去了。他的去向只有两个,一是去武昌投奔王敦,一是去投奔石勒。”
韩潜说:“我向武昌方向追。”
祖逖对卫策说:“你去通知冯宠,命水兵营在黄河沿岸堵截。”卫策应命去了。
在操持王玄后事的空档时间里,桓宣问祖逖:“尉氏的人事你准备怎么安排?”
祖逖想了想说:“你来收拾这里的残局如何?”
桓宣说:“我还是在谯城吧,那里可是你的第二后方啊。这里交给卫策吧。”
祖逖说:“也好。督护由谁来干呢?”
桓宣说:“眼前就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谁?”
“祖涣。”
“他还嫌太嫩。”
桓宣说:“在淮阴他不就一直跟着你操练吗?有个担子压着,他很快就会成熟起来。”
祖逖说:“也只好这样了。”
桓宣说:“事不宜迟,我马上去建业,从朝廷里弄个委任状来。不然,让别人抢了先,尉氏就不是你的了。”
祖逖说:“这是豫州的管辖范围,谁敢!”
桓宣说:“你又来了。”他派人把祖涣找来,对他说:“好好照顾你父亲,我有事去了。”说完,拱手告辞。
童建在哪儿?此时他正在北渡黄河的船上。
接到王敦的命令以后,童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王玄可是王敦的侄子啊,一家人干嘛要刀剑相向呢?为什么要他下手呢?杀了王玄之后,自己会是个什么结局呢?自从来到祖逖的旗下,祖逖对他不错,给了他一个督护的官职。王玄也没有拿他当做曾经打家劫舍的土匪,给了他充分的信任,把尉氏的军队交给了他。他已经相信了郭璞的话,不再作非分之想,就在祖逖的军队里作一个下级军官,了此一生。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钱凤又逼上门来,把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他,令他左右为难,杀王玄,对不起祖逖,更对不起王玄,此后,自己何以在人世间立足呢?不杀吧,钱凤留下的还是那句话:你将死无葬身之地!并且答应,事成之后,就到武昌来,王敦自会保护他。
童建被逼到了墙角,身不由己,他不得不服从了钱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