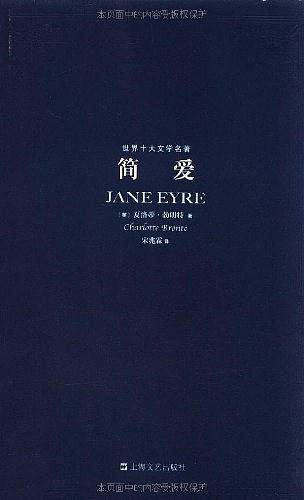节选自《这不是手艺,这是生活》作者: 赵勤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疆姑娘李若梅二十一岁的时候,遇见了诗人十一。诗人向她展示了那个有着海风气息的远方世界。
她因此喜欢上读诗。因为想要看看海,她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辞职离开新疆外出打工。
几经辗转,李若梅在南宁的米粉馆里刷过盘子,在桂林的街边卖过袜子,在北京的后海当过导购,在上海的淮海路上发过传单。最后,她落脚在南方以南的广东,开始在一家豆腐店里工作,一边做豆腐,一边读诗,成为了别人口中的“豆腐西施”。
在她看来,过了三十岁之后,她终于“在做豆腐这件事里找到自己、成就自己的,如今她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独立、恣意……”
在本文作者赵勤的眼中,李若梅是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做一块小小的豆腐,同时也依然秉持着当初爱诗歌的初心。她用诗歌来温暖日常,又将豆腐做得饱含诗意。
下文选摘自《这不是手艺,这是生活》,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读诗·点卤
文 | 赵勤
一、诗歌是生活最后的暖意和悲悯
沿着友谊南路,向北,穿过巷子,直走。左手边,就是李若梅的豆腐店。巷子深,两边摆满了蔬菜、水果,流淌着熙熙攘攘的人。
李若梅是个做豆腐的女人,开着一家豆腐店。不做豆腐的时候,她就读诗。这个习惯让她和左邻右舍的小商贩有点不一样。
南方的下午,阳光已西斜,热浪却依然咄咄逼人。店里开着空调,很凉爽。房间不大,前半截是店面,后面是操作间,中间隔着实木柜台,柜台上面是装饰墙,隔开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一扇小门连通着前后。一张实木茶台旁,李若梅坐在一把竹椅上发呆,另一把空着的椅子上放着一本诗集,是余秀华那本《月光落在左手上》。白色的封面有点灰扑扑了,翻看得多了,书有些旧。没有顾客,一切显得安静。只有巷子的嘈杂偶尔夺门而入,钻进耳朵。
每天这个时候,李若梅最惬意。早上的繁忙过去了,豆腐也已经卖完了,案台已经收拾干净,明天要用的物件也已经准备好了。她终于可以歇歇了,时间是半下午,又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她不急着接孩子、回家做饭。这个时间是她自己的,她会给自己泡一杯茶,看上几首诗。最近她喜欢上了余秀华的诗,她喜欢诗中那种粗砺而灵动,真切而深邃,生命的质地惨淡中透出华贵的表达。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读到这一句,李若梅被打动了。在李若梅看来,好的诗歌读起来一定是让人感同身受,身体疼痛或情感共鸣。无论写的是什么,不能打动她的诗歌便不是她心目中的好诗歌。李若梅喜欢余秀华诗中那种雅俗共赏的感情深度,她总是能在诗中照见自己,好像是在说自己,不由得就被打动了。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
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
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
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
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这首《我爱你》,李若梅早已经可以背下来了,可还是喜欢,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李若梅觉着自己曾经也是一棵稗子,怀揣着爱情。诗集后面的跋中,余秀华说:“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这段话,李若梅也觉得是在说自己,虽然李若梅一直在生活的尘埃里摸爬滚打,从事着和诗歌相去甚远的职业,也不会写诗,可是她觉着读诗就是在清洁自己,这个爱好就是生活给她的最后一点暖意和悲悯。
做豆腐和读诗有什么关系?没有一点关系。可就是挡不住李若梅喜欢。她说她读过的诗集有十几本了,木心的《云雀叫了一整天》,海桑的《我是你流浪过的一个地方》,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还有海子、食指等诗人的诗集。
诗,实在是个没有用的东西,尤其在佛山这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诗歌显得更为无用,不当吃不当穿。读诗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好,但也没有更坏。自从那年在阿瓦提,她开始读诗,她就再也没有放下过。读诗至少让她觉得活着不是那么难,还有一点意趣。

二、爱与诗,让她有了向往的远方
二十一岁的李若梅,没有去过太多的地方,在乌鲁木齐上完中专,就回到了生她养她的阿瓦提县。这里是刀郎人的发源地,这里有地道的刀郎歌舞和穆塞莱斯(葡萄酒)。如果那个秋天,她没有在胡杨林里遇见一个叫十一的诗人,她的命运也许和现在完全不同。
那年,县里为了扩大宣传,搞了一场名为“刀郎劲歌舞,情醉阿瓦提”的文化活动,请了一些文化名人和微博达人来参加,十一就是请来的嘉宾之一。
当时李若梅在村里的小学代课,报名参加了文化活动的志愿者服务工作。活动期间,她忙着给人带路、讲解,招呼大家休息、吃饭,做一些具体的服务工作。
十一是位诗人,开幕式过后,在一系列参观刀郎民俗活动中,他丝毫不显眼。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有点旧的白衬衣,因为近视而戴的眼镜,沉默不语的微笑,腼腆又有些羞涩的面容。这些都是李若梅不熟悉的,却也吸引着她不时看向他,而彼时他刚好也在看着她。
晚上的篝火晚会上,刀郎人尽情地唱歌跳舞,那些歌,唱得撕心裂肺又一往情深。唱歌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白天还拿着锄头在地里干活,或者在胡杨林里放羊。夜晚,在篝火旁,他们却都是歌者、舞者。他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旋转起来,却比年轻人还轻盈。
他盘腿坐着,像个真正的刀郎人那样,一杯一杯地喝着只有阿瓦提才有的穆塞莱斯。那天他喝多了,站起来说了好多话,有关生命、爱和死亡,都是她听不懂的话。
很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那个夜晚,想起他说过的那些话,她又觉得那些话都是说给她听的,说给她一个人听的。
秋天的胡杨林里,金黄的叶子掉了一地,踩上去窸窣作响,树上的枝头间,还有更多金黄的叶子,等着掉下来。
活动很快结束了,十一要走了。分别时,他们一起又去了胡杨林,走了很多路,说的话却不超过十句,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对白,他们都是羞涩的人。但还是有些微妙的情绪在滋生、酝酿,虽然只有他俩知道。最后,他送给她一本自己的诗集。
她读他的诗集的时候,他已经回到了他在南方海边的家。她读到了海的腥味,潮水的喧哗,空气中的咸味,那是潮潮的海的味道。
这一段没有开始就结束的恋爱——如果这也能称为恋爱的话,彻底改变了李若梅。她是因此才喜欢读诗的。她是因为想要看看海,才不顾家里人的反对,辞职离开新疆外出打工的。

十一像古代的行吟诗人一样,到处参加活动和体验生活,他的诗里也就有了很多地名。李若梅的生活是不用体验的,而她想体验他的生活,于是这些年她追随着他的脚步去了很多地方。
她在南宁的米粉馆里刷过盘子,在桂林的街边卖过袜子,在北京的后海当过导购,在上海的淮海路上发过传单。当她终于明白,她和十一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她流落到了南方以南的佛山。她累了,想要稳定下来,想要有个家。
三、豆腐店的师傅支持她看诗集
她在佛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豆腐店里打工,跟着师傅,学会了做豆腐。豆腐必须当天做,隔夜就馊了,所以,每天凌晨三点,当别人还在熟睡时,李若梅就得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帮师傅舀水、烧水、磨豆子、做豆腐。等做好豆腐,已经差不多六点了,接着打扫店面,收拾桌椅,开门营业——卖豆腐。
师傅做事麻利,性情温和、开朗。没有事情的时候,她喜欢摆弄一下花草。例如给“非洲堇”控型,剪掉“花月夜”长出的准备开花的那一部分,因为它一开花,整棵植株就要死了,师傅不想让它死……店里还种了很多多肉植物,师傅打理它们时,总是屏住呼吸又小心翼翼,害怕弄伤了多肉小小的茎和叶子。三十多盆多肉都摆在向阳的那一面窗台上,阳光充裕,多肉们色彩斑斓,萌到人心里。
只要不耽误做事,师傅支持她看诗集。师傅对她说,这个世界的人分两种,一种是有趣的人,一种是无趣的人。有趣的人对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而且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制造乐趣,欣赏得了平凡,也把握得住繁华;无趣的人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更不会制造乐趣。其实人生的快乐时光,大部分是在看似无用的事情上度过的。

师傅不过四十几岁,有时候却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妇人,有时候又简单得像个孩子。她教李若梅磨豆子时说,磨豆子的过程,也是一个审视自己内心,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寻找出来,再消化掉的过程。磨个豆子,也能被她说得这么文艺,李若梅不由对这个四十几岁的女人好奇。
师傅一个人带着个小女孩生活,她从来不肯对人讲自己的过去。有时候,她会在没有人来的时候发一会儿呆,李若梅看见她微微扬起的嘴角,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过去一段美好的时光。但她不说,李若梅就不问。
李若梅在店里工作了三年,完全学会了师傅的手艺,和师傅相处得也好。师傅把自己的表弟介绍给了她。师傅的表弟在东莞的一家私立学校搞管理,忠厚实在。
他们交往了大半年,见过双方家长后,就毫无悬念地结婚了。房子是按揭的,在东江边。据说地铁要通过这里,几个月之间房价一平方米就涨了好几千,他们好像凭空成了富人,可因为是唯一的住宅,无法变现,高兴归高兴,日子还是那么过。
李若梅有时候想起这几年的事情,感觉有点恍惚。自己居然就在此结婚了,居然做了母亲,自己真的在这个叫东莞的地方扎下根了?
女儿出生后,李若梅心里慢慢开始踏实起来。丈夫天天去上班,下班回家又买菜做饭,偶尔也出去喝个酒、打个牌,但都不上瘾,晚饭后他会带孩子在小区里转转。他像一个丈夫该有的样子,他不读诗,但也不反对李若梅读诗,他能理解妻子有时候需要一个人待一会儿。这样的日子就是普通人的日子吧,可是谁不是过着普通人的日子呢?
孩子快要三岁了,可以送幼儿园了。师傅帮她在相隔着半个城区的友谊南路盘下这个店,看着她添置了家什,进了豆子,帮她理顺了进货的渠道,就由着她自己干去了。

四、做豆腐,说简单也很简单
李若梅最讨厌人家叫她“豆腐西施”,她觉得这个名称充满暧昧,不好。有那大大咧咧的顾客,一进门,就大着嗓门喊着:“哎,豆腐西施,来块豆腐!”她冷着脸,手起刀落切着豆腐,并不看来人,然后不温不火的一句“拿去”,常常教来人意识到自己唐突了,下次来就规矩多了。
附近很多人喜欢吃她做的豆腐。想吃,要来得早,下午来常常就要空跑一趟了。
豆腐营养丰富,价廉物美,是普通人家的家常菜。比起鸡鸭鱼肉山珍海味,豆腐和白菜一样,都属于“寒品”,清代何刚德《客座偶谈》卷四载:“科举时代,儒官以食苜蓿为生涯,俗语谓之食豆腐白菜。”
李若梅说,这多像我啊,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儿,在这个城市里打拼。
李若梅尝试用各种豆子制作不同的豆腐。原材料很好找,去杂粮店买来黑豆、青豆、红豆等,经过磨豆浆,过滤,冷却,点卤,按压成形等一系列操作,最后终于成豆腐了。最近她又准备研制一下胡萝卜豆腐、牛奶豆腐等,总之,加什么料可以任意发挥。

李若梅说店小,有些做法就行得通,哪怕我今天做绿豆豆腐,明天做黄豆豆腐也无妨。顾客虽然少,却能细水长流,只要喜欢吃我做的豆腐的人一直在,我就能一直做下去。我愿意把时间用在挑选豆子,清洗豆子,磨碎豆子,看着豆子变成豆腐的这个过程中,虽然有辛苦,但也有快乐。
豆腐可以炸、煎、烩、炖、炒、煨、烤,成为油豆腐、臭豆腐、卤豆腐等。豆腐走出作坊,出现在餐桌上,人们会说它味道有多么好,但对于李若梅来说,乐趣只在制作的过程。人们其实根本不知道,一个女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多少秘密,它的秘密比它成为菜肴的一刻更为美妙。
做豆腐,说简单也很简单,首先要洗豆腐包。这要分是做干豆腐还是做大豆腐。做干豆腐,那要用长长的粗纱白布,大约半米宽,几十米长。做大豆腐的豆腐包,则是很大很大的方形,也是粗纱布,边长大约两米。把豆腐包洗净后,晾干备用。
黄豆大约要泡一个晚上才能泡开,上磨磨成豆浆,再把豆浆放在很大的锅里熬,直到熬开,停火。这时,要过包,使豆腐渣和豆浆分离。在棚上吊一个十字架,将一块方形的豆腐包吊在十字架的四个角上,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网兜。将熬开的豆浆一瓢一瓢地舀进豆腐包中,另一个人需要一摇一摇地晃动着豆腐包,使纯豆浆从豆腐包中滤下来,流到放在下面的大缸里。到一定的程度时,要用夹板夹住豆腐包中剩下的豆腐渣,将残留的豆浆挤出。直到所有的豆浆都过完包,豆腐渣就和豆浆完全分离了。
将豆浆稍微凉一下后,就开始点卤水了。李若梅将卤水盛在一个小碗里,往豆浆里倒一点,就用勺子把豆浆搅一搅,她的眼睛始终注意着豆浆的变化。再倒一点卤水,再搅一搅,直到认为满意为止。这是做豆腐最关键的手艺。
点好卤后,把缸的盖子盖上,等一会儿,看到豆浆已经成了“脑”,里边有一朵一朵的豆腐花与清水相伴的时候,也就是豆浆分离为豆腐花和清水的时候,就可以压豆腐了。
压豆腐前,先将压大豆腐的木框摆好,把大豆腐包,即极为宽大的方形豆腐包放在木框之中,将豆腐花一瓢一瓢地舀到木框里,水哗哗地从下边流出来,豆腐花沉积在木框里。等到木框里的豆腐花积满了,就将豆腐包的四角翻过来,将豆腐花包住,上面用木板压好,再用石头压实。等到豆腐不老又不嫩的时候,揭开木板和豆腐包,豆腐就做成了。用刀划成一块一块的,就是好吃的豆腐了。
李若梅说自己是在做豆腐这件事里找到自己、成就自己的,如今她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样子,独立、恣意……她说做豆腐是一个慢慢明晰的过程,在繁复的忙碌之中,味道得以慢慢展现,就像自己的人生,从三十岁开始,她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做豆腐最关键的是点卤。卤水是从盐井中打上来的盐卤,与石膏一样,点在豆浆中可以起到凝固的作用。点进去就会凝起豆花,将豆花用布包起,挤出水,压实,就成了豆腐。水留下得多就嫩,水留下得少就老。北方人喜欢老豆腐,南方人喜欢嫩豆腐。南北豆腐不是以用什么东西点浆来区分的,而是以嫩和老,另外工艺有点不同。现在工厂生产的豆腐已经没有用卤水点的了,都是用石膏。
李若梅坚持用卤水点豆腐,也许是坚持那么一点点心意。她说想要做出人们心目中最好吃的豆腐,从来都没有捷径可走。它首先需要你拥有良好的味觉,知道哪种才是最能打动人的豆腐;其次,它需要你夜以继日地锤炼,寻找最适合的豆子,一次次改进软硬的比例,反复调整点卤的技巧。看着李若梅神情专注地点卤,有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奇妙感觉。这让我想到在平庸而繁忙的生活中,偷闲读读诗,看似没有用处,可对李若梅来说却是必需的精神生活。
再平凡普通的人,内心也有一点点和别人不一样的精神需求吧?也许就是那一点点,让他们独特起来,让他们之所以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
五、做豆腐的卤水,也是生活的光
夏天的正午,太阳毒辣,吃过饭的人们都去午睡了,一个孩子偷偷溜出房门,站在院子的大太阳下。四处静悄悄的,躲过了大人的看管,孩子有点兴奋又有点无聊,突然院子里飞来一只蝴蝶,吸引了她的目光。她追逐着,想要抓住它,蝴蝶在刺玫院墙的花上飞飞停停,逗弄着孩子。她好几次差一点就要抓住它了,可是它嬉闹一番最终还是飞走了。孩子绊倒在刺玫院墙边上,哇哇大哭起来,到底是为被刺玫扎着了的疼痛而哭,还是为蝴蝶飞走了的失落而哭,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哭声越来越大,所有的委屈和失落都化成越来越撕心裂肺的哭声。孩子的哭声,惊醒了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老奶奶拍掉孩子身上的土,安慰着孩子:蝴蝶的天性就是要围绕着鲜花飞舞,就是你一时抓住了,它最终也会飞走的。奶奶给你折一只属于你的蝴蝶,它可以一直陪伴着你。
孩子依然不依不饶地哭闹着,老奶奶回到屋里,打开木头柜子,拿出一些大小不一的红色的纸,摊开在吃饭的小台子上,又拿了剪刀,然后坐下来,比画着纸,折折叠叠,不一会儿,一只栩栩如生的纸蝴蝶就折好了,蝴蝶的翅膀颤动着,马上就要飞起来的样子。老奶奶拿在手里,逗弄着刚才还抽抽噎噎的孩子,此刻孩子已经惊讶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在孩子的心里,老奶奶太神奇了,像个老仙女,可以变出会飞的蝴蝶。
老奶奶后来还给小女孩折过飞机、蜻蜓、青蛙……这些折纸是小女孩寂寞的童年中最好的玩伴。老奶奶折这些物什,大多在睡完午觉以后,只见她颠着小脚,走到柜子前,吱吱呀呀地打开柜子门,从最上面一层拿出平常存下来的报纸、抚平的包装纸、写对联剩下的红纸等各式各样的纸头。而后,她坐下来,拿起剪刀,随意抽出一张纸来,先剪去毛毛角角,把纸修剪成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然后放下剪刀,拿着纸在手里转来转去比画一番,再歪着头想上一想,过一会儿才开始折起来。
一旦她开始折,她的眉眼仿佛舒展开了,微微笑着,眼睛随着手中的纸转来转去,整张脸仿佛被笼罩在一种光晕中,神采奕奕。有时候嘴角还会随着手里的动作轻微地抽动一下,仿佛是在用力,折纸的手也灵巧起来。这时候她全心沉浸在手上的动作中,完全没有注意到小女孩不错眼珠地盯着她看,眼神里满是崇拜……

老奶奶是甘肃人,不识字,老伴去世得早,没有子女,她一个人住着,手脚利索,性情开朗。小女孩的父母要上班,早上天还没有亮,就把小女孩送到老奶奶家,晚上天已经黑透了他们才下班,再把已经睡着的小女孩抱回家。
老奶奶家穷,一间屋子,中间用土块砌的火墙隔开,冬天火墙接了炉子在前面,做饭兼取暖,后半间一张架子床就占去了大半,墙角立着粗壮的木头柜子,是她家唯一像样的家具了,前半间是土灶台,土块垒起来,表面用草泥磨平,垫上报纸,就是饭桌。老奶奶爱干净,尽管家徒四壁,但床上单子抻得平平展展,窗户玻璃擦得像没有玻璃,地上没有铺砖,也没有抹水泥,就是裸露的土地,但扫干得净,没有碎屑杂质。老奶奶对小女孩很好,吃食不够,她还拿出自己的口粮给小女孩子做吃的,给她讲故事,教她背属相口诀:
老鼠前面走,跟着老黄牛。
老虎大声吼,兔子抖三抖。
天上龙在游,地上蛇在扭。
马儿路边遛,羊儿过山沟。
猴子翻筋斗,公鸡喊加油。
守门大黄狗,贪睡肥猪头。
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如今过去了三十几年,老奶奶早已经入土为安了,我也已经人到中年,老奶奶折纸时的一颦一笑却还印在心里。
和李若梅在一起的这个下午,我又想起她来。
李若梅和教她做豆腐的师傅,还有我的老奶奶,都是普通人,却也都是心里有光的人。那一点点的光,像做豆腐时的卤水,经由它的点化,我们平凡的人生也有了意趣和快乐。
聊了一个下午,大部分是李若梅在讲述,我在听。要走了,我却想起余秀华还有一首诗——《九月,月正高》,它的最后几句是:
月亮那么白。除了白,它无事可做
多少人被白到骨头里
多少人被白到穷途里
但是九月,总是让人眼泪汪汪
田野一如既往地长出庄稼
野草一直绵延到坟头,繁茂苍翠
不知道这枚月亮被多少人吞咽过了
到我这里,布满血迹
但是我还是会吞下去
就是说一个人还能在大地上站立
你不能不抬头
去看看天上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