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自《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与其同出一篇的名句还有“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在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中,这两句诗歌往往被用来当作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祝福。
然而,如果细考《击鼓》的诗意,就会发现这两句“祝愿”的背后却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也是一段永远无法完成的诺言。

《击鼓》:我独南行,不我以归
《击鼓》全诗共五章,每章四句,以一位普通士兵的视角来阐释其对战争生活的厌倦。文思婉转,声韵悲戚: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诗歌的第一章是全诗的背景,战鼓声声,战乱频仍,这些普通的士卒们开始了自己生死未卜的征程,其中就包含着写下这首诗歌的主人公。
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其经历却也比较特殊。其他的部队都驻扎在国境之内,“土国城漕”指的就是卫国,但他所在的部队却要“南行”。这是越出国境之后的作战,生死未卜。
悲壮、畏惧、恐慌、无奈等等复杂的情绪,尽在“我独南行”四字之中。
诗歌的第二章交代了此次“南行”的目的,原来是调停宋国和陈国的争斗。这是承接上文“南行”一句来展开的,说明这位士卒所在的部队已经介入了战争。
在经过战火之后,他发出了感慨,奉命驻守异国的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家了。

于是第三章画风一变,开始通过戍卒的眼睛来写战后戍守的场景。有人永远也回不来了,也有的人战马都丢失了。通过这种细节的描绘,在读者的眼前展现了一个经历过惨烈战事之后小人物的悲伤。
见多了死亡,人心会变得麻木,于是在第四章的时候,戍卒想家了。
他想起来,自己在出征之前曾经对妻子说过的话。他说自己要牵着她的手,陪着她慢慢变老,一同享受世间的诸般美好,就连死亡都无法把他们分开。这是一段多么感人至深的情话呢,但如果不是在当下的境况就好了。
于是,这位戍卒突然变得歇斯底里了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场战争呢?让他面对随时都要死亡的危险。
但他认为即使自己死亡了也不可怕,重要的是自己无法兑现曾经的誓言了啊!
他无法再见到自己的妻子,更无法陪她走过之后的日子,甚至连在她身边死去都是一种奢望。
整首诗歌就在这种激愤的情绪下完结了,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普普通通的戍卒在心理崩溃的瞬间,听到他呼天抢地的悲号,更能体会到其激愤的内心与深沉的哀痛。

其实,当他成为一名“戍卒”的时候,这种悲剧就变得无解了,甚至要比战死更为可怕。
《击鼓》:戍边士卒的普遍悲剧
这位“南行”士卒的身份是有所转变的,其任务从作战变为了戍守,他也就成为了一名戍卒。
关于这一次的战争,《毛诗序》中认为写的是州吁时期,也就是卫前废公,春秋历史上第一位弑君篡位成功的公子。其性格好战,这一次是出兵攻打陈国和宋国,当时人们怨愤其勇而无礼,所以创作了这一篇《击鼓》。
但《郑笺》里却认为,这场战争是州吁联合陈、宋、蔡等国一同伐郑,双方打了多次战役,主人公就是一名在陈、宋边境戍守的士卒。
但这些说法也被很多解诗者驳斥,认为它既不符合历史记载,也不符合诗歌内容。

从具体诗句来看,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发生在卫国、陈国和宋国之间,所以才会说“平陈与宋”,并没有提及蔡国。且围困郑国只不过五天就返回了,更谈不上“不我以归”。
比较可信的推断是,这场战争发生在卫穆公时期,晋楚争霸的大背景下。
晋楚作为两个大国,为了拉拢盟友,一直争取周边的郑国、宋国等国家的依附。所以这些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诸侯们常常处于风雨飘摇的位置,依附其中一个就会受到另一个大国的攻打。
晋楚之间刚刚打了一场邲之战,晋国被打败了,郑国等国家最终依附了楚国。为了找回场子,晋国举行了一次“清丘会盟”,目的是“恤病讨贰”,即帮助有困难的盟友,讨伐有二心的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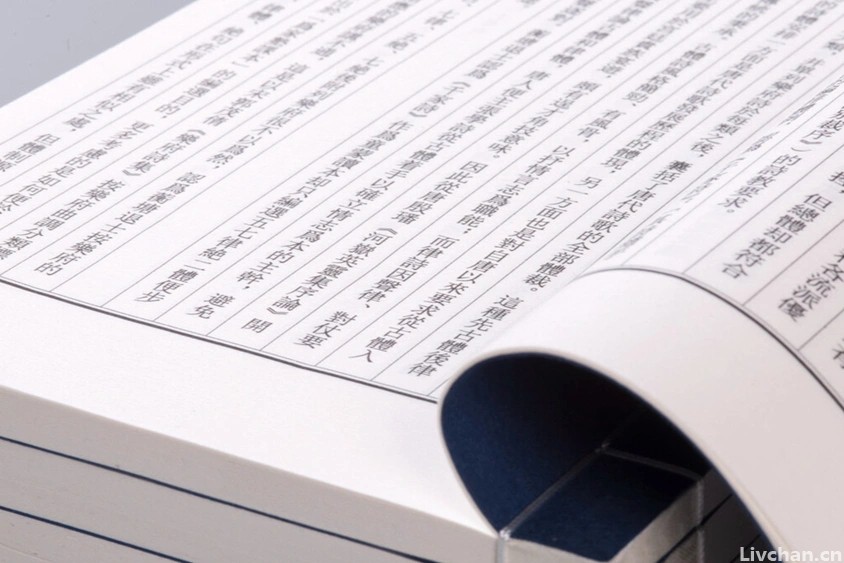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国便攻打了反复不定的陈国。而卫国却在此时背弃了“清丘之盟”,出兵援助陈国,与宋国交战。这一举动自然是狠狠地得罪了晋国,甚至也可以被划入“讨贰”的行列里。
《击鼓》中的诸多诗句都和这一事件相吻合,所以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下了结论: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
从这一背景来看,这位写诗的“戍卒”处境可以说是非常不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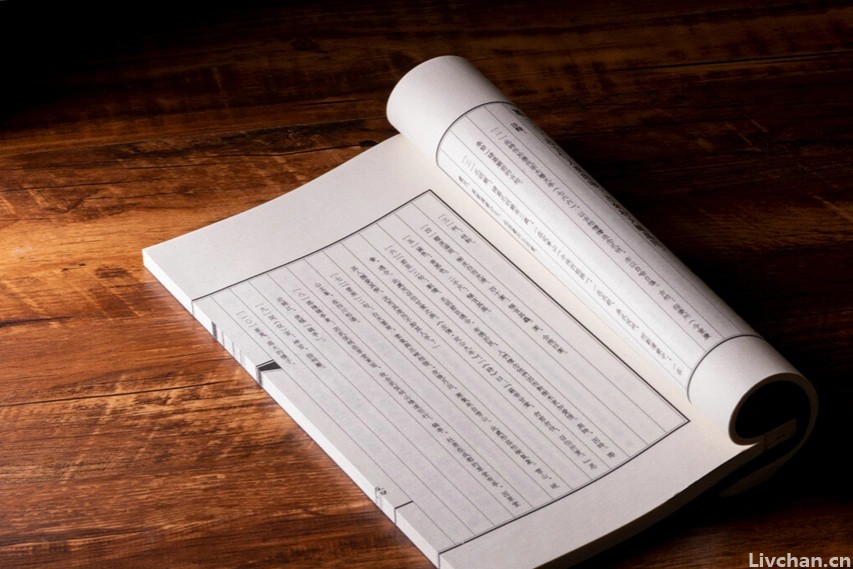
从战争的性质来说,戍卒所在的国家不仅介入了他国之间的争斗,更是背弃盟约,引起了晋国以及周边的诸侯国不满,必然会遭到诸多抵抗,让本来就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更为动荡。
而从其个人的角度来讲,戍守的期限是不定的,这也是戍卒的普遍悲哀。这些人往往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驻扎,没有具体的归期,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几十年之久。来时正青壮,与妻子告别,而白首之时尚不得还乡。
这种痛苦在《击鼓》当中有一个流变的过程。
“我独南行”等诗句表明了这位士卒是奔赴异国进行了一场实力并不对等的不义战争,其心理便有所抵制。
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士卒所在的部队经过了惨烈的厮杀,他们的任务也逐渐变成了戍守,日复一日的煎熬下,对随时死亡的恐惧终于被极度思乡的痛苦所取代。
原来,对于戍卒来说,“死别”已经变得并不可怕,让其感到畏惧的是“生离”。
《击鼓》作为一首描写戍卒军旅生活的诗歌,对战事的残酷和惨烈不做过多着墨,而是选择了戍卒对妻子的爱恋作为主体,重点写他在情感诉求与现实场景上的矛盾和冲突,显然更容易让读者产生情绪上的共鸣,从而更同情其戍卒生涯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