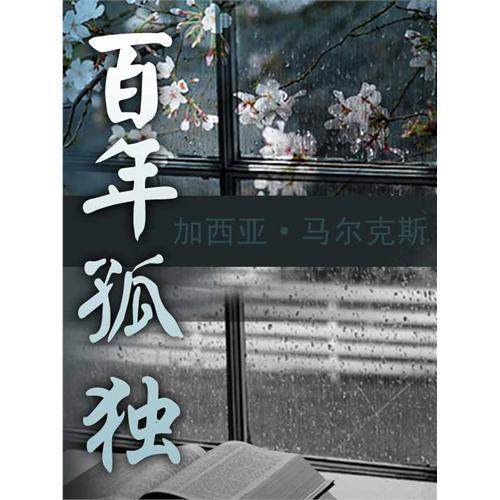有一次,他把思嘉惹火了,因为他冷冷地说几年以后共和党的统治要在佐治亚州倒台,民主党人要重新掌权,到那时候,他就该替她后悔了。
“等将来民主党人有了自己的州长,自己的州议会,所有你新结交的这些庸俗的共和党朋友就全得倒台,重操旧业,开酒吧,倒污水,他们也就配干这样的营生。你就会孤零零一个人,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没有民主党的朋友,也没有共和党的朋友。唉,这都是将来的事,现在不必担心。”
思嘉听了,大笑起来,她是笑得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布洛克在州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州议会里已经有了二十七个黑人,佐治亚州有数千名选民失去了选举权。
“民主党人永远不会重新上台了。他们只会刺激北方佬,这就只能推迟他们重新上台的时间。他们就会夸夸其谈,晚上出去搞三K党的活动。”
“他们会回来的。我了解南方人。我了解佐治亚人。他们很坚强,很倔犟。如果非得再打一仗,才能重新上台,他们就会再打一仗。如果需要像北方佬那样花钱收买黑人的选票,他们就会花钱收买黑人的选票。如果需要像北方佬那样让一万名死人参加选举,那么佐治亚州每一个公墓里的每一具尸体都会到投票站去。在我们的好友鲁弗斯·布洛克的仁政之下,情况会非常糟,佐治亚很快就要把他赶走了。”
“瑞德,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思嘉大声说,“听你这么说,好像我不希望民主党重新掌权似的!而你明明知道,情况不是这样!我是很喜欢他们回来的。难道你以为我愿意看着这些兵在这里走来走去,使我想起——难道你以为我愿意——唉,我也是个佐治亚人呀!我希望看到民主党人重新上台。可是他们不上台,老也不上台。即便他们上了台,对我的朋友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们的钱还是他们的,对不对?”
“那就得看他们能不能存住钱了。看他们现在这个花钱的样子,我怀疑他们的钱能留过五年。来得容易,去得快呀。他们的钱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正如我的钱也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一样。它肯定还没有把你变成一匹马,是不是,我可爱的小骡子?”
最后这句话引起了一场口角,他们吵了好几天。思嘉绷着脸,不说话,显然是要求瑞德向她赔不是。这样过了四天之后,瑞德到新奥尔良去了,把韦德也带去了,嬷嬷对这件事是反对的。他一直待到思嘉的怒气消了才回来。不过瑞德不肯屈服,依然使她感到难受。
瑞德从新奥尔良回来时,心平气和,思嘉也就尽量强压着怒火,暂时把这件事置诸脑后,留待将来再考虑。她现在不想在令人不快的事情上费心思。她希望快活,因为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在新居里首次大宴宾客。那将是一次规模极大的晚宴,要用棕榈树装点起来,还要请一支管弦乐队。四周的回廊全要用帆布遮起来,那各式小吃使她想一想都要流口水。她在亚特兰大所有认识的人她都要请,包括所有的老朋友和度完蜜月回来后认识的所有那些漂亮的新朋友。准备这次宴会,使她感到兴奋,在大部分时间里,她也就忘了瑞德那些刺耳的话。她感到快活,在她考虑怎样举办这次宴会的时候,她感到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快活。
啊,有钱可真有意思!开宴会可以不计算花销!买最贵的家具、衣服和食品,也可以不考虑怎样付款!可以把数额相当大的支票寄给查尔斯顿的波琳姨妈和尤拉莉姨妈,寄给塔拉的威尔,多么开心呀!啊,那些妒忌人的糊涂虫竟然说钱无所谓!瑞德还说钱没给她带来什么好处,真叫人不可理解!
思嘉向所有的朋友发出了请帖,老朋友,新朋友,比较熟的,不太熟的,甚至她不喜欢的,都请到了。就连梅里韦瑟太太,她上民族饭店去拜访思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粗暴无礼,还有埃尔辛太太,她的态度冷若冰霜,也都没有排除在外。她还邀请了米德太太和惠廷太太,虽然她明明知道她们都不喜欢她,也明明知道她们参加这样体面的聚会,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会感到尴尬。因为思嘉这次新居大聚会,一半是宴会,一半是舞会,当时管这样的晚间聚会叫“大聚会”,亚特兰大还从未见过这样盛大的聚会呢。
到了那天晚上,大厅里和帆布遮起来的回廊上挤满了客人。他们喝着她用香槟配制的香甜饮料,吃着她的小馅饼和奶油牡蛎,随着乐队演奏的乐曲跳舞,乐队前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排棕榈和橡皮树。但是瑞德称之为“老团兵”的人,除了媚兰和艾希礼、皮蒂姑妈、亨利叔叔、米德大夫夫妇,梅里韦瑟爷爷之外,别人都没有来。
“老乡团”有许多人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是决定要来参加这次“大聚会”的。有的人是看了媚兰的态度而接受邀请的。有的人是因为觉得瑞德救了他们的命,或救了他们亲属的命,而接受邀请的。然而就在宴会的前两天,有一条谣言在亚特兰大传开了,谣言说布洛克州长也受到了邀请。“老团兵”表示反对,寄来了一大摞明信片,说他们不能接受思嘉的善意邀请,感到遗憾。为数不多的几位老朋友虽然来了,可是州长一到,他们感到尴尬,就毫不犹豫地退席了。
思嘉看到这些情况,既惊讶,又气愤,觉得这次宴会完全失败了。多么排场的“大聚会”呀!她精心安排了这次活动,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了不起的场面,可是老朋友只来了那么几个,老对头则一个也没来。天亮的时候,客人都走完了,她恨不得大哭大闹一番,可是又怕瑞德哈哈大笑,怕看他那转个不停的黑眼睛,因为他虽然没有说,却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我早就告诉你了嘛!”所以她只好强压住怒火,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她就对着媚兰一个人大肆发作起来。
“你真让我下不来台,媚兰·威尔克斯,你还让艾希礼和那些人一块让我下不来台。你要是不拉着他们走,他们是不会那么早就走的。唉,我看见你了!我正要把布洛克州长带过来,介绍给你们,你就像兔子一样跑掉了。”
“我想他不会——我想他不可能真来参加,”媚兰不高兴地回答说,“虽然大家都说——”
“大家?这么说来,大家都在叽叽咕咕议论我,是不是?”思嘉气愤地嚷道,“你是不是说,你要是事先知道州长要来参加,你也和他们一样,根本就不来了?”
“是的,”媚兰两眼看着地板,低声说,“亲爱的,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能来的。”
“你可真行啊!原来你也会和他们一样,让我下不来台呀!”
“唔,别这么说,”媚兰非常难过地说,“我不是有意伤你的心。你就是我的姐姐,亲爱的,是我的亲兄弟查理的妻子,我——”
她怯生生地把一只手搭在思嘉胳臂上。可是思嘉一下子把它甩开了,恨不得自己也能像父亲杰拉尔德那样,生起气来大发雷霆。但是媚兰并不示弱。她两眼盯着思嘉那双愤怒的绿眼睛,瘦削的肩膀挺了挺,顿时显出一副庄重的神气,虽然和她那略带稚气的面孔和她的身材有些不相称。
“对不起,让你伤心了,亲爱的。但是布洛克,或者任何一个共和党人,或者任何投靠北方的人,我都不能见。我在你家里不见他们,在别处也不见他们。即或我不得不——我不得不”——媚兰往四下里扫了一眼,想找一个最重的词儿——“即或我不得不显得粗暴无理,我也不见他。”
“你是在指责我的朋友们吗?”
“不是,亲爱的。不过他们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
“你是指责我不该把州长请到家里来吗?”
媚兰无法回避了,但她仍旧盯着思嘉的眼睛,毫不动摇。
“亲爱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道理的,我喜欢你,信赖你,我是不会指责你的。谁要是指责你,让我听见,我就不答应。不过,思嘉呀!”突然间,激动的话语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声音不大,里面却包含着无法消除的恨。“这些人是怎样对待我们的,难道你忘了吗?亲爱的查理死了,艾希礼的身子垮了,‘十二橡树’村烧了,难道你忘了吗?唔,思嘉,你打死的那个家伙,他手里就捧着你母亲的针线盒,你总没有忘记吧!谢尔曼的队伍开到塔拉,把咱们的内衣都偷走了,他们还想把房子烧掉,还真的拿我父亲的战刀耍弄了一番,你也不会忘记吧!思嘉呀,这些人抢过我们,折磨过我们,还让我们挨过饿,你就是把这些人请来参加你的宴会了!就是这些人,他们使得那些黑鬼对我们那么神气,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财物,不让我们参加选举。我忘不了,也不想忘掉这一切。我不会让我的小博忘记这一切,我还要教我的孙子痛恨这些人,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我还要教我孙子的孙子痛恨这些人。思嘉,你怎么能忘记呢?”
媚兰说到这里,停下来喘一口气,思嘉注视着她,媚兰感情强烈,声音颤抖,使她感到吃惊,把她的怒气也驱散了。
“你以为我是傻瓜吗?”她不耐烦地问,“我当然记得!可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媚兰。我们要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现在我就是在这么干。布洛克州长,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共和党人,如果我们善于跟他们打交道,是能够给我们很大帮助的。”
“比较好的共和党人是没有的,”媚兰斩钉截铁地说,“再说,我也不愿意让他们帮助。我也不想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如果这指的是北方佬。”
“我的天哪,媚兰,干吗要赌气呀?”
“啊!”媚兰说,显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样子,“看我说了些什么!思嘉,我本来并不想使你伤心,也不想指责你。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人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想法。你听我说,亲爱的,我是爱你的,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我也不会改变对你的态度。你也还是爱我的,是不是?我没有让你恨我吧?思嘉,咱们俩要是有什么不和,我可受不了——咱们毕竟是同舟共济,一起过来的呀!说声没关系吧。”
“快别胡说了,媚兰,你真会小题大作,”思嘉不满地说,但是媚兰轻轻地用手搂住了她的腰,她没有再甩掉。
“行了,我们又和好了,”媚兰愉快地说,不过她又悄悄地补充说,“亲爱的,我希望咱们还和过去一样,互相看望。共和党人和投靠北方的人哪一天来看你,你只要告诉我一声,我待在家里就是了。”
“你来不来,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思嘉说着,戴上帽子,气呼呼地回家去了。媚兰脸上露出伤心的样子,这使得思嘉觉得她那受到损害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首次宴会之后,一连几个星期,思嘉感到要对大家的看法装作根本无所谓的样子是很困难的。除了媚兰、皮蒂姑妈、亨利叔叔和艾希礼之外,老朋友都不来看她,也不邀请她去参加他们的小型聚会,这使她大惑不解,而且非常难过。难道她没有尽量捐弃前嫌,并且向他们表示,虽然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恶意中伤,她对他们并无恶感吗?他们应该清楚,她和他们一样不喜欢布洛克州长,对他笑脸相迎,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些糊涂虫!要是人人都对共和党人笑脸相迎,佐治亚州很快就可以摆脱她现在所处的这种困境。
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她和过去的生活、昔日的朋友之间的脆弱的联系,她已经一下子切断了,永远接不起来了。即便媚兰出来运用她的影响,也无济于事了。何况媚兰又惊讶,又伤心,但依然忠贞不渝,也不想帮着恢复那种联系了。即或思嘉想再像以前那样生活,和老朋友打交道,现在也已经不可能了。全城都对她板起了面孔,和花岗石一样硬。人们对布洛克政权的恨,也落到了她的身上,这种恨里面没有多少火气,而是非常冷酷,难以消逝。思嘉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敌人拴在了一起,无论她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如何,她现在都要算是变节分子、黑人的支持者、叛徒、共和党人——还要算是一个投靠北方的人。
思嘉痛苦了一阵子之后,便收起了她那假装无所谓的样子,而露出了真面目。她这个人从来不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做过多的考虑,也不因一件事做不成而长期闷闷不乐。没有多久,梅里韦瑟、埃尔辛、惠廷、邦内尔、米德和其他人家对她有什么看法,她就置之不顾了。至少媚兰带着艾希礼来看她,而艾希礼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亚特兰大还有一些别的人是愿意来参加她的宴会的,这些人比那些思想保守的老家伙随和得多。她什么时候想大宴宾客,就可以发出邀请,这些客人和那些反对她的思想僵化的老糊涂虫相比,心情愉快得多,衣服也漂亮得多。
这些人都是不久以前才来到亚特兰大的。她们有的是瑞德的朋友,有的在那些神秘的活动中和他有联系。他向思嘉提到这些活动时就说:“做生意而已,我的宝贝儿。”客人之中有的是思嘉住在民族饭店时认识的一对一对的夫妻,有的是布洛克州长任命的官员。
现在和思嘉交往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盖勒特夫妇曾在十几个州里居住过,显然每次都是因为他们的欺骗勾当被发觉而仓促离开的。康宁顿夫妇在离这里很远的某一个州里曾和“自由人局”有联系,从无知的黑人身上赚了很多钱,而他们是应当保护这些黑人的。迪尔夫妇曾把“硬纸板”鞋卖给联盟政府,战争的最后一年不得不到欧洲去躲了起来。亨登夫妇在许多城市的警察局里挂了号,但又常常在投标中获胜,得以和州政府签合同。卡拉汉夫妇是靠开赌场起家的,现在正利用州政府的钱修建并不存在的铁路,来进行更大规模的赌博。弗莱厄蒂夫妇一八六一年以一分钱一磅买下的盐,一八六三年涨到五角钱一磅,因而大发其财。巴特夫妇战争期间曾在北方某大城市开过一家最大的妓院,现在也在北方冒险家的社交界进进出出。
现在和思嘉来往密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但是参加她的大型宴会的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有一定的修养,许多人有很好的家庭背景。除了冒险家先生们之外,颇有些资产的人也从北方来到亚特兰大,因为他们看到在这重建与发展的时期,这里的生意是源源不断的。北方有钱的人家把年轻的儿子送到南方,让他们在新的地区进行开拓。北方的军官退役之后就在他们浴血奋战攻下的这座城市里定居了。起初,他们人生地不熟,很愿意应邀参加又阔气又好客的巴特勒太太举行的豪华宴会,但是不久他们就逐渐退出她的圈子。这些善良的人们只要与那些冒险家们和冒险家政权稍一接触,就会像佐治亚州的本地人一样憎恶他们。许多人加入了民主党,比南方人还像南方人。
还有一些格格不入的人依然留在思嘉的圈子里,只是因为他们到哪里都不受欢迎。他们倒是愿意到老乡团的安静的客厅里去做客,可是老乡团不请他们去。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北方来的女教师,她们到南方来,目的是教育黑人,教育投靠北方的南方人,这些南方人本来都是不错的民主党人,南方投降以后,成了共和党人。
不现实的北方来的女教师,和投靠北方的南方人,这两种人哪一种更为亚特兰大的本地人所痛恨呢?很难说得清楚,不过人们可能更加痛恨第二种人。关于北方来的女教师,人们可以说:“哦,北方佬喜欢黑人,你对他们能有什么指望呢?他们当然觉得黑人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为了个人利益而加入共和党的佐治亚人来说,就没有借口了。
“我们能挨饿,你们也应该能挨饿。”这就是老乡团采取的态度。许多人过去在联盟的队伍里当过兵,知道家里缺衣少食的人多么害怕,因此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过去的战友,如果他们为了让家人得以 口而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面目。老乡团的女眷则不然,这些女人是社会首领的坚定不移的后盾。在她们心目中,事业虽然失败了,现在却比鼎盛时期更强大,更亲切。现在它成了崇拜的对象。和它有关的一切都成了神圣的了。比如为它而献身的死者的坟墓,打仗的战场,破碎的战旗,交叉着挂在大厅里的战刀,褪了色的前线来信,参加过战斗的老战士,等等。这些女人对先前的敌人不帮助,不接待,不留宿,现在思嘉也被划到敌人里边去了。
口而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面目。老乡团的女眷则不然,这些女人是社会首领的坚定不移的后盾。在她们心目中,事业虽然失败了,现在却比鼎盛时期更强大,更亲切。现在它成了崇拜的对象。和它有关的一切都成了神圣的了。比如为它而献身的死者的坟墓,打仗的战场,破碎的战旗,交叉着挂在大厅里的战刀,褪了色的前线来信,参加过战斗的老战士,等等。这些女人对先前的敌人不帮助,不接待,不留宿,现在思嘉也被划到敌人里边去了。
在这个由形形色色的人出自政治形势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里,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钱。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战前从来没有在手里一次拿着二十五块钱,现在却恣意花钱,其奢侈程度在亚特兰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政治上,共和党人掌权,亚特兰大进入了一个浪费和讲排场的时期,表面上的文雅微微地遮掩着下面的庸俗与罪恶。很富的人和很穷的人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显。居高位者对不那么幸运的人毫不关心。黑人当然除外。他们的一切都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住宅,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娱乐,因为他们掌握着政权,每一张黑人选票都是起作用的。至于新近陷于贫困的亚特兰大人,他们可以挨饿,或者栽倒在大街上,刚刚富起来的共和党人是无动于衷的。
在这庸俗的浪潮中,思嘉处于领先的地位,兴高采烈。她刚结了婚,打扮得花枝招展,又有瑞德的钱做坚强的后盾。当时的情况是合乎她的口味的:人人都毫不掩饰地炫耀自己,妇女的衣着都过于华丽,家里的陈设都过于讲究,珠宝太多了,马匹太多了,食品太多了,威士忌太多了。思嘉有时也静下心来想一想,她知道如果严格地用母亲爱伦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她新近结交的这些女人都不能算是正经人。但是自从很久以前,她在塔拉站在客厅里,决心做瑞德的情妇以来,屡次违反母亲爱伦的标准,所以现在也就不怎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了。
严格说来,这些新朋友也许不能算是先生和女士,但是他们和瑞德在新奥尔良交的朋友一样,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这些人比她以前在亚特兰大认识的性情压抑、常去教堂、喜欢读莎士比亚的那些朋友,有趣得多。除了度蜜月时那段短暂的时间外,她很久没有感到乐趣了。她也很长时间没有安全感。现在生活安定了,她想跳舞,她想玩,她想放荡,她想大吃大喝,她想穿绸缎,她想睡在柔软的羽毛床上,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这一切,她都做到了。瑞德让她由着性子干,觉得很有趣,她现在也摆脱了幼年时代的束缚,甚至最终摆脱了受穷的顾虑,于是她就要实行她过去常常抱有的一种奢望了,这奢望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不赞成,就叫他见鬼去。

思嘉陶醉了,她的心情与赌徒、骗子、彬彬有礼的女冒险家、一切靠耍心眼儿制胜的人一样,这种人活在世上,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思嘉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那傲慢的态度几乎马上就膨胀得无边无际了。
思嘉对待新结识的共和党人和投靠北方的人也是蛮横无理的,但是她对北方驻军的军官及其家属比对任何其他人都更为粗暴,更为傲慢。流入亚特兰大的,有各式各样的人,惟有军人,她是既不接待,也不欢迎的。她甚至故意显得对他们不礼貌。蓝军装意味着什么,不光是媚兰一个人不会忘记。对思嘉来说,那军装和那金黄色的纽扣永远意味着围城的恐怖气氛,逃难的可怕经历,意味着掠夺,焚烧,意味着极度穷困的生活和在塔拉的艰苦劳动。现在她有钱了,而且结交了州长和许多显要的共和党人,社会地位稳固了,就有资本对每一个穿蓝军装的人无礼了。她也的确对他们无礼了。
瑞德有一次漫不经心地对她说,在他们家聚会的男客,大部分人不久以前还穿着这身蓝军装呢。思嘉却反驳说,北方佬只要不穿军装,就不像是北方佬了。瑞德答道:“你真固执得可爱,”耸了耸肩膀,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思嘉讨厌驻军穿的笔挺的淡蓝军装,特别喜欢怠慢他们,因为她这种态度实在使他们感到愕然。驻军的家属自然是要感到惊愕的,因为她们大都是文质彬彬的有教养的人,她们在这怀有敌意的异乡感到孤独,盼着回到北方去,而且为不得不维护那个无赖的统治而感到有些惭愧。这些人肯定比和思嘉来往的那些人强。驻军军官的太太们看着活跃的巴特勒太太竟然把红头发的丑陋的布里奇特·弗莱厄蒂一类的女人当做挚友,而故意怠慢她们,自然是感到迷惑不解的。
然而就连思嘉视为挚友的女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不过她们是心甘情愿的。对她们来说,思嘉不仅象征着财富与风度,而且体现着旧的制度,包括旧的人物,旧的家庭,旧的传统,等等,而她们正殷切地希望和这些旧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她们所向往的那些旧家庭恨不得把思嘉赶出去,但是新兴的达官贵人的太太们对于这一点,是全然不知的。她们只知道思嘉的父亲当年是个大奴隶主,她的母亲来自萨凡纳的罗毕拉德家族,她的丈夫是查尔斯顿的瑞德·巴特勒。对她们来说,这就很够了。旧的社会集团鄙视她们,对她们不回访,在教堂里只对她们冷淡地点头致意,她们一心想打入这样一个旧的社会集团,就用得着她这块敲门砖。事实上,思嘉还不光是她们进入社会的一块敲门砖。她本来并不引人注目,刚刚发迹,对她们来说,她就是社会的体现。她们本人也不是真正上流社会的女士,因此对于思嘉这一套虚假的外表,她们看不清楚,思嘉自己也看不清楚。她们是按照思嘉对自己的看法来看待她的,因此在她面前忍气吞声。她摆架子,她施恩惠,她发脾气,她耍态度,她当面对人粗暴无礼,她毫不客气地指责人家的缺点,这一切,她们都忍受了。
她们没有根基,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因此特别希望显得文雅,不敢发火,也不敢顶嘴,生怕人家说没有女士的风度。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她们也要像个女士的样子。她们装出一副非常娇嫩谦恭与天真的模样。听听她们说的话,你会觉得她们与罪恶的下层社会既无联系,也不了解。红头发的布里奇特·弗莱厄蒂皮肤白皙,娇嫩怕晒,操着柔和的爱尔兰口音,谁也想不到她竟会盗走父亲暗中收藏的财物,来到美国,在纽约一家饭店里做女招待。看一看西尔维亚(原先叫萨迪·贝尔)·康宁顿和玛米·巴特那多愁善感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前者是在父亲在鲍厄里开的酒店楼上长大的,忙时还要帮着照看酒吧,谁也不会想到后者据说本是她丈夫开的妓院里的一个姑娘。现在她们都成了娇滴滴的风雨不愁的宝贝儿了。
男人们虽然会赚钱,却不善于学习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可能对新绅士向他们提出的要求还不够耐心。他们在思嘉的宴会上喝酒喝得很凶,实在太凶了,宴会之后往往有一位或几位客人临时留下来过夜。他们喝酒,和思嘉小时候那些人喝酒的样子可大不相同。他们满脸发胀,反应迟钝,丑态毕露,脏话连篇。此外,无论思嘉在显眼的地方摆上多少只痰盂,第二天早上还是可以在地毯上看到嘴里流出的烟汁的痕迹。
思嘉看不起这些人,可是她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因为她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她家里就老有许多这样的人。因为她看不起他们,他们一把她惹烦了,她就叫他们去见鬼。不过他们倒也能忍受。
瑞德的话,他们也能忍受,这就更不容易了,因为瑞德把他们看透了,这一点,他们也是知道的。他甚至就在自己家里,也是说揭他们的短,就揭他们的短,而且总是弄得他们无话可说。关于自己如何赚钱,他认为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因此他假装认为别人怎样发迹,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于是他几乎一有机会就要说,而大家一致认为,为了照顾面子,还是不说为好。
不定什么时候瑞德就会举着一杯香甜饮料和蔼地说:“拉尔夫,我要是不糊涂,就该像你那样,把金矿股票卖给寡妇和孤儿,而不应该去跑封锁线。你那个办法保险得多。”或者说:“哎呀,比尔,我看到了,你又买了两匹新马呀!是不是又卖了几千块钱的并不存在的铁路工程的债券?干得不错呀,伙计!”或者说:“祝贺你,阿莫斯,祝贺你和州政府签了合同。真糟糕,你不得不贿赂这么多人,才把合同拿到手。”
总而言之,太太们觉得瑞德庸俗得让人无法忍受,对他十分讨厌。先生们则在他背后管他叫猪猡,杂种。过去亚特兰大不喜欢他,他没有想办法讨好他们,现在亚特兰大依然不喜欢他,他也依然没有想办法讨好他们。他自行其是,感到自得其乐,看不起别人,对周围的人提出的看法置之不理,客气得使人觉得他这种客气实际上是一种进攻。对思嘉来说,他依然是个谜,不过她已不再为解这个谜而伤脑筋了。她确信,他对什么都不满意,将来也不会满意;他或者是急需什么东西,而恰恰没有这件东西,或者是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东西,因此对任何东西都觉得无所谓。他讥笑她做的每一件事,他鼓励她任意挥霍,待人傲慢,他讽刺她华而不实,虚装门面——他为她付所有的账单。
[1] 英语,意为:大百货店。
[2] 英语,意为:货物出门概不退换;实际意思是:顾客自行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