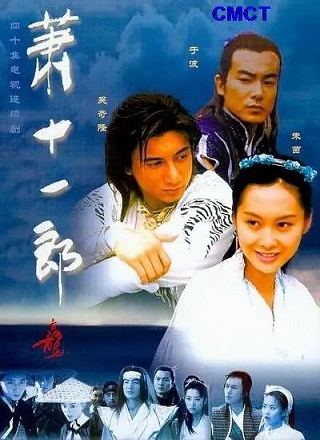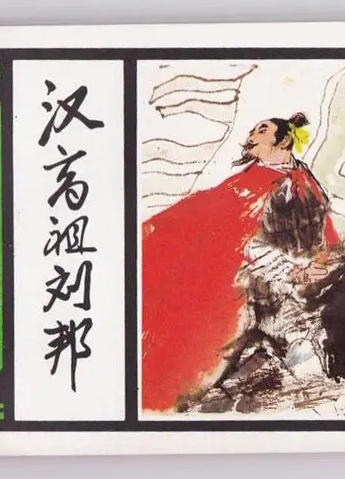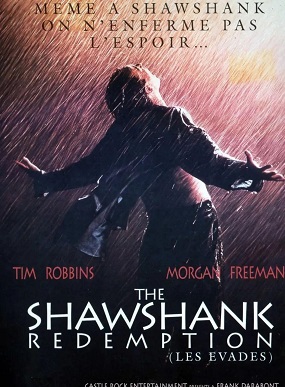11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下榻在西郊的一栋旧式别墅里。
周谷城应邀来到了毛泽东在西郊的下榻处,他一进门,正和陈丕显谈话的毛泽东就起身相迎,笑着说:
“又碰到了。”
这是毛泽东每次见到周谷城时的常用语,话虽平淡无奇,却透出了老朋友之间的亲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候之后,两人便天马行空地聊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哲学史的写作,他说: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周谷城说:
“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了下文。”
毛泽东话题一转,说:
“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他们又谈到旧体诗,谈到了晚唐的李商隐。周谷城说着说着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仰靠在沙发上,随口用湖南腔哼起了李商隐的一首七言诗: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把前几句反复吟诵了几遍,可那最后两句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朋友忘了,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吟道: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周谷城在毛泽东面前不经意地吟唱这首讽喻帝王末路的诗篇,是不太妥当的,而他竟然轻轻松松地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自然然地接了下去。毛泽东念出最后一句时,周谷城又跟在他的后面哼,而且感到心情舒畅,超乎寻常。毛泽东和周谷城一样,心情也很舒畅。可周谷城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此生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
1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为斯特朗80寿辰,派人送给她两张祝贺卡。
11月22日,有关部门特意为斯特朗包了一架专机,满载着她和她的30位中外朋友飞抵上海,住进了古朴典雅的锦江饭店。毛泽东将在这里会见她,祝贺她的80大寿。起初,毛泽东只打算会见斯特朗一个人,斯特朗不同意,她说:
“我的朋友们这么大老远和我一起来,假如毛主席见我,也应见他们。”
11月24日,是斯特朗的80周岁生日。毛泽东将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斯特朗和她的朋友们。
天将近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一个大房间的门口迎接客人,江青也站在毛泽东身旁一同迎客。毛泽东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愉快,他首先祝贺斯特朗生日愉快!然后同客人们一一握手,说:
“我已经认识你们中的好几位。但大多数人是新的。”
当毛泽东与中宣部领导包括副部长吴冷西在内的几位干部握手时,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面有不豫之色。他把客人领进了接待室。这里铺着一个大的地毯,摆放着一个大的椭圆型桌子。毛泽东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到第2幅作品前看了一下,又走向第3幅作品;尔后他让斯特朗坐了首席,自己在相邻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慢悠悠地说:
“我,一个吸烟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是对立的一派,不吸烟派。”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这个开场白感到吃惊。身为医生的马海德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便挑战似地说道:
“你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派别问题吗?”
毛泽东说:
“当然,在我和医生之间,医生说我不应该吸烟,我说我要吸。我行我素嘛!”
他用目光巡视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又说:
“你们有多少人吸烟?吸烟的人拿一支香烟举起手来。手里拿一支烟就是吸烟者的标志。”
毛泽东说话的口气很轻松。在场的外国朋友不知毛泽东何出此言,而几位中宣部领导干部却深知个中原因:毛泽东还在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生气呢。他们面面相觑、惶惑不安。
原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从11月12日开始,上海的《解放日报》、浙江的《浙江日报》、山东的《大众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的《福建日报》、安徽的《安徽日报》、江西的《江西日报》,都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北京市各家报刊及全国其它各地报刊却都拒绝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自然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使他非常愤慨,于是他就指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结果,北京连单行本也不予理睬。
且说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人,见没有几个人拿起烟举手,他笑了笑,旁敲侧击地说:
“好吧,看来在这方面我也是少数派喽。不管怎样,我还是吸烟,并且劝你们也吸。”
午宴开始后,毛泽东以传统的主人姿态,从第一道菜拼盘中,夹了一些,放在斯特朗的碟子里。午宴的气氛虽然并不十分热烈,但毛泽东对斯特朗的关怀与盛情,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斯特朗还是感到很满意、很愉快。
11月26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14日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的有功人员。接见结束后,江青对罗瑞卿说:
“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
罗瑞卿当场表示说:
“我们《解放军报》支持。”
他马上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一个态度鲜明的编者按。
11月29 日,在压下姚文元的文章19天之后,彭真得知《解放军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得不给范瑾打去电话,要《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第二天,《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加上了彭真亲授的按语。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原来在11月27日,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组织人写关于近年来海军思想斗争的材料,他特意嘱咐李作鹏要在这份材料中说明罗瑞卿的表现。
此前,罗瑞卿对林彪的“顶峰论”、大搞“突出政治”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拉拢他无效,便认为他是妨碍自己向上爬的障碍,就决定除掉他。李作鹏立即召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秘密整理了材料,说罗瑞卿“怀有巨大的阴谋”;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想当国防部部长”。
1965年12月1日,《光明日报》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这个时期,各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均仿照《北京日报》加了编者按语。这些按语,强调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力图把这一讨论局限在学术领域。此后,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向阳生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协作组“方求”等,接二连三地发表批驳姚文的文章。就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还击时,《红旗》杂志的编委关锋和戚本禹站了出来。戚本禹表示:
“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
此后,关锋、戚本禹二人来到了上海,与姚文元商谈此事。张春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就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而这场论战便成了不久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在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林彪在这个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55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12月2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12月初,毛泽东获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在军人集团10月1日政变夺取掌权后于11月24日被杀害,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写出了《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其词云: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鼓吹的所谓的“历史主义”。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12月8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了,吴冷西也列席了会议。
叶群在会议上分3次作了约10个小时的发言,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12月11日,罗瑞卿被召到上海会议上,但他没有得到申辩的机会。
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提出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说:
“他罗瑞卿只是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也只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嘛。”
林彪说:
“他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反对主席。”
毛泽东见林彪如此坚持,只好退了一步,说道:
“可以先挂起来么。10年不行,20年,挂1万年行不行?”
毛泽东不愿意打倒罗瑞卿,但他又不能不同意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离军事领导岗位。
林彪建议由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那么匆忙,还是让他代代吧。”
于是,杨成武就出任了代理总参谋长职务。
12月15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上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他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
这份《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是以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又吸收了4月25日他在政治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看了《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批复道:
“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太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后来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通知,连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中央在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同时注明:“不登党刊。”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会议决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5条意见:
“1、性质严重,手段恶劣。2、与彭、黄有别。3、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4、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领导有责。”
会议还决定:“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欲知罗瑞卿后来的状况如何,请看下一卷便知。
东方翁曰:常言道:党内有党,派中有派。此一时期中共党内、军内的状况便是如此。面对着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实力派的挑战,毛泽东不得不处理好军内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从大局出发,压抑着与罗瑞卿的深厚感情,从保护罗瑞卿的目的出发,调动他离开军队,到地方上去工作。以这种有条件的方式,支持三军统帅林彪。舍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惜罗瑞卿不理解,不愿意离开军队。以至于后来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状况,这也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