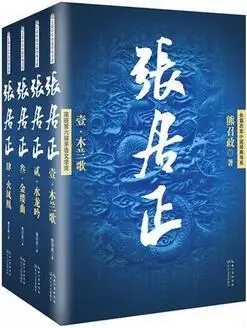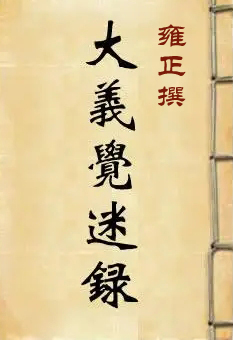如前所述,-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我对-和武藤两人所说的话,一开始就产生若干怀疑。因为在中学生时代,通过军事教练的教师、退伍老军官所谈的亲身经历,曾听到过当年暴行的事实。我又通过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战争》一书,看到了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有关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从他父亲家永宜太郎——一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委以陆军步兵少尉而前往台湾赴任——少将的遗物中发现的。
其实,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所载《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在“日俄战争以后”云云等观点,立即受到了鹈野晋太郎——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将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当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发表在该杂志同年九月号,题为《〈南京大屠杀〉读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事实上,日本军在日清战争时,攻入旅顺后不久,进行了如同在南京发生的那样的大屠杀,杀害两万人,这段历史应如何看待?……从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制军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说要进行‘征伐台湾’的大屠杀,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其残酷性始终不变,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
虽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视-和武藤的证词,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详细地介绍了鹈野的批判文章,并对他们两人的证词表示有若干疑问,即使这样,我仍固执己见,不想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一,那是因为献身中国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传教医师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来到奉天(沈阳)——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DygaldChristie;ThirtyyearsinMukden,1883-1913,London,1914.)一书中,说是在日清战争时,日本军的军纪严正,出乎意料(上册),根本没有提及在旅顺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克里斯蒂牧师在战争开始后即去牛庄(营口)避难。如果发生了鹈野所说的多达两万市民被杀之大屠杀事件,这一传闻当然会传到在牛庄避难的牧师耳边,他理应把它写入自己的那本书中,但该书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叙述。该书的日译本是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在战争期间出版。人们认为,可能由于书要被检查,因此他对某些情况略而未译,但看了原著后,才知道它还是一个全译本。那末,克里斯蒂为什么不去特别写旅顺大屠杀事件呢?实在令人费解。但在该书中也可看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若干叙述,兹介绍如下:
日本军不断进军,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占领了旅顺、开州、海州等。
几个城镇和村庄遭到破坏,许多无辜市民被杀,几百个人在严寒的冬天流离失所。
克里斯蒂所说遭到破坏后许多居民被杀的“几个城镇”,其中当然包括旅顺,但那里平时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为战火所迫而逃入该市,或有许多散兵换上便衣后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会有多达两万的中国人被屠杀。
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第九章)、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中冢明的《日清战争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顺屠杀事件,虽然我过去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也决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为历史家来说,这是天大的无知,其可耻的失策已经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旅顺大屠杀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过藤岛守内的《屠杀之地‘满洲’之行归来》其一、二(载《潮》,一九七二年九、十月号)才确认这一事实的。据说,藤岛从沈阳辽宁大学的教师们那里获知旅顺大屠杀的有关资料,那就是事件的目击者英籍船员詹姆斯-艾伦所写的《旅顺落难记》(中译本)。藤岛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到了艾伦用亲身经历写的原著(UndertheDragonFlag,1898.),并对其内容大要作了介绍。书中说,一受害者达六万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写的《“东方史”和“亚洲史”》一文(收录在《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下册,青木书店出版),了解到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的记述及其所引英籍国际法学者霍兰德著书(ThomasE.Holand;Studiesininternationallaw,1898.)研究的情况,不要说是受害人数达六万人,就是说两万人也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觉得居住在旅顺或在那里避难的中国人多半被残酷杀害,这是必须确认的事实。与此有关,还可看到两、三幅随军画家所画屠杀的场面,那是公开出版的。
在已经获知这一事实的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务,是要对日本军的残暴性弄个清楚。
※ ※ ※
诚然,日本军队残暴成性,由来已久。但事实上,这个军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发残暴。对于在日本军队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素质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年轻军官“勇猛”无比
在检查官审问武藤中将的记录中,还能发现如下问题。检查官问:“你知道在中国和菲律宾许多无辜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有的被强奸,不感到良心上的责备吗?”武藤中将答:“在南京和马尼拉发生暴行后,自己觉得身为与这两起事件有关的参谋官员,感到在日本多队的教育中缺少点什么。”检查官认为好极了,就插话:“你认为在军事教育中缺少些什么?”武藤避开话题说:“在南京和马尼拉施加暴行的军队是紧急动员来的,未受过正规的军队教育。”他还就日本军队的暴行以南京事件为契机在高级军官中有所反映的倾向发表议论说:“这证明日本人的素质和人格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善家庭和学校教育。”这是非正式的议论,它归罪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将所认为的那样,南京占领军之素质所以差,那是因为日本军的大部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也许可以这样说。对此,崛场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七五九页)中说“这些问题应当仅指责军队吗?军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毋宁说国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况是未经教育且年纪较大,而应征入伍的人素质较差且问题较多,则是经常性的。”
但据我的曾当过南京占领军通讯兵的义弟说,满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年轻军官和士官候补生。所谓“年轻军官和上官候补生”云云,在旧著《日本近代战史之谜》中有所记述,但根据以平冈正明为中心的五人采访小组的调查、采访、研究和执笔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战》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情况,说:“这可能像洞富雄所说的那样。我在这次调查范围内,也从旧军人的回忆中,听说日本军的顽强性和残暴性,主要在于下士官和年轻军官。他们亲自参与屠杀,并作示范,也叫新兵这样干,进行了杀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战》,载《日本之秋》季刊2)。当时参与南京事件的年轻军官,现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纪。在《日本记录》中所收《花冈事件》一文的笔者野添宪治也说:“现在,在我周围上了年纪的旧军人中,很多人在酒醉后傲慢地说,他们在大陆的行为是野蛮的”(《强行带走的结果》,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年轻军官是典型的日本军人,是单纯地培养其军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说,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军队教育与对敌对国家人民犯下暴行之间的联系。
关于这些年轻军官的残暴性,我们曾经听到过下列证词。鹈野晋太郎自己承认:“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个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前引《〈南京大屠杀〉读后》。鹈野也在《世界》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手记,题为《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
由此联想到,当进攻南京的追击战开始时,有一个传闻,说是片桐部队的两个少尉相互进行在“占领南京前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东京日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报道)。所谓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事实上是从无锡出发,到攻打紫金山时结束。这两个少尉,一个杀了一百零六人,一个杀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竟能分别杀死一百多名中国兵,这是正当战斗行为的结果吗?还是屠杀?铃木二郎——当时作为《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曾向报社发了关于这一杀人比赛的消息——在他前几年写的报告文学中提到:两个军官说过,“两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杀”(《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然而,据当时报道,说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在横林镇战斗中杀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战中杀死这么多进行抵抗的对手吗?可以断定,他杀的多半是俘虏来的不抵抗的士兵。当时两个军官所说的,是一种隐瞒事实的抵赖。志志目彰曾听当年进行欢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指野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谈起过攻打南京的情况,那是他来到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小学生说的。当时,他听到该少尉这样说:
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的事……
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
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原文如此——译者)”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在一边,逐个杀死。……
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
“砍杀百人比赛”,也是一种屠杀。N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
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威武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10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
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第一至一九0页)
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著《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0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征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