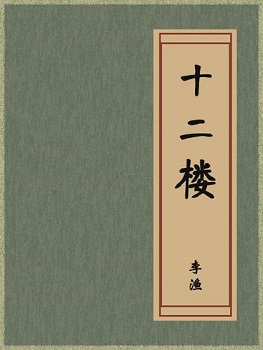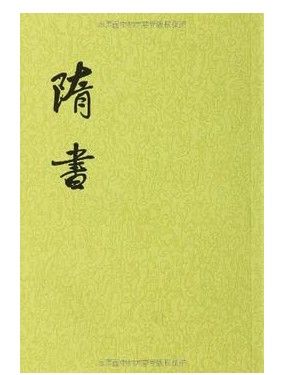04
“菲德尔(即菲德尔·卡斯特罗),此刻我忆起许多往事,忆起当年在安东妮娅家里跟你相识的情景,忆起你邀请我加入你们,忆起当时的筹备情况是何等的紧张,还记得有一天,有人问我们,万一我们死了,应该通知谁?这种可能性使我们震惊,后来我们知道了,在革命之路上,的的确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有那么多同志都倒下了,今天,这一切已经不再具有那么浓厚的戏剧性色彩,因为我们更加成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会重演的。
我相信,我已经完成了把我同古巴革命结合在一起的那一部分职责,因此,我要向你、向同志们、向你的人民同时也是我的人民告别。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的部长职务,放弃我的少校军衔和我的古巴国籍,从此,我和古巴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联系了,仅存的是另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能像职务那样辞去的。
回顾过去的生活,我曾努力地工作,度过壮丽的岁月,现在,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而这些事情是你作为古巴领导人难以去做的,我们分别的时候到了,此刻我心中悲喜交加。
在古巴,我留下了一个创业者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最爱的亲人,留下了把我视如己出的人民,如果我葬身异国,那么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古巴人民,特别是你,菲德尔,我感谢你的教导和你的榜样。
我没有给我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自豪,我不会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我知道国家会对他们做出充分的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受教育,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你和我们的人民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讲了,千言万语说不尽我心中的热忱,又何必浪费笔墨呢?
向着胜利,直到永远!誓死保卫我们的祖国,菲德尔,我用全部的革命热情拥抱你。”
在留下这封信后,格瓦拉就离开了古巴,他放下了家庭、放下了高官厚禄、放下了尘世间的一切念想。选择再一次走进深山老林、去当一个游击战士。
很多事情促使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其中最残酷的一件是他无法忍受作为一个幕后的指挥者,把他的一个个手下、同志、学生都送上战场,而他自己却安然无事。
在对阿根廷的游击渗透中,格瓦拉的多年好友马塞蒂、从古巴革命时就跟随他的贴身保镖埃尔梅斯都死了。
格瓦拉心灰意冷地对阿尔贝托(当年摩旅的同伴)说:
“你看我,就坐在书桌后面,见鬼,我的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死了!是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的。”
整个20世纪60年代,古巴对外输出的革命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格瓦拉不愿接受这个结果,他决定亲自走上战场,他要把自己的命都赌上。
在离开家前,格瓦拉和自己的妻子阿莱伊达、保姆索菲亚坐在一起吃饭,格瓦拉突然间问索菲亚:
“那些在革命中牺牲的古巴人的遗孀怎样生活?她们再婚了吗?”
索菲亚回答说:
“是的,大部分都再婚了。”
格瓦拉转向阿莱伊达,指着面前的咖啡杯说: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给我上的这杯咖啡,希望将来也能上给另外一个人。”
后来索菲亚一想到当时的情形就会颤抖,她明白格瓦拉是在对阿莱伊达说,如果他死了,他希望阿莱伊达能再婚。
在最终离开古巴前,格瓦拉和卡斯特罗见了一面,此时卡斯特罗对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有所疑虑、也不希望格瓦拉以身犯险,但既然格瓦拉下定了决心,卡斯特罗还是给了他全力支持,格瓦拉需要的一切人员和装备,卡斯特罗都给了他,并在舆论和外交上对他予以支持,在告别宴会的最后,两个老朋友之间来了一个男人式的拥抱,然后他们都向后站了站,把各自的手臂搭在了对方的肩上,这个姿势维持了很长时间,过去十多年的光阴仿佛就从他们相互交叠的臂膀间穿过,在场的泊涅诺感叹道:
“这是告别宴会中最令人感伤的一幕。”
时间到了,格瓦拉终究还是走了,他的汽车一路向机场驶去,之后整个营地都陷入了一片忧郁的沉默中,卡斯特罗离开人群,独自坐在一边,他垂着头,就那样坐了很久。
人们想知道他是否在哭,可是没人敢靠近他,黎明时分,人们听到卡斯特罗突然喊了一声,他的手指向天空,人们抬眼望去,天空中飞过的正是格瓦拉的飞机。

05
玻利维亚,格瓦拉一生的终点。
这里四通八达,和阿根廷、巴西、巴拉圭、智利、秘鲁都接壤。
格瓦拉想要以玻利维亚作为突破点,将革命之火传遍整个南美。

和他一同前往玻利维亚的,还有17个古巴人。
他们大多是从古巴革命战争时期就追随格瓦拉的老兵,其中不乏身居高位者,比如陆军师长华金、工业部副部长阿莱汗德罗、糖业部副部长加伊尔,他们本可以安度余生,但在格瓦拉的召唤下,他们再一次拿起了枪、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人类革命史上的典范。
卡斯特罗任由格瓦拉调遣这些高官,也表明了他对这次行动毫无保留地支持。
除古巴人外,游击队中还有36个玻利维亚人,他们代表了玻利维亚的本土革命力量,但在征召玻利维亚人时,格瓦拉首先就遇到了问题。
这个问题在于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蒙赫,蒙赫是一个首鼠两端的人,他对于是否发动武装革命感到犹豫不决,他自己是倾向于搞议会斗争、走选举路线上台的,但既然古巴派人来了,他又觉得不妨让古巴人试一试,但这一试,他又害怕格瓦拉打出名声来,影响到了自己的地位,在这种种纠结之下,蒙赫常常出尔反尔,他一会儿因为在选举中得到了一点选票,就决定要撤回对格瓦拉的支持;一会儿又说他是支持武装革命的,他领导下的玻共,本应是连接外来的古巴势力和本土的玻利维亚人民之间最重要的纽带,但这个纽带从一开始就是不牢固的,格瓦拉也没有及时认清这一点、及时止损,他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心态,相信自己可以说服蒙赫、或者摆脱蒙赫单干。
结果等他到了玻利维亚后,情况迅速恶化,蒙赫向格瓦拉摊牌,要求获得游击队的领导权,在蒙赫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的国家、而他又是玻共的总书记,但蒙赫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格瓦拉不可能将游击队员的性命交给这样一个人,于是格瓦拉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可以由蒙赫担任游击队名义上的领导,但实际的指挥权仍由自己掌控。
蒙赫连这个方案也接受不了。
两人不欢而散。
在临别前,蒙赫警告那些想要跟着格瓦拉搞武装革命的玻共党员,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这里,就会被开除出党,给他们家人的津贴也会停发。
但没有一个人跟着蒙赫离开,这些玻共党员都选择继续跟随格瓦拉,格瓦拉看似取得了胜利,但他也和蒙赫、以及蒙赫领导的玻共彻底闹翻了,一旦没有了本土政党的支持,格瓦拉这支外来的游击队与玻利维亚人民之间的联系就被大大削弱了。
此后还有玻共党员想要来投奔格瓦拉,也都被蒙赫半路拦了下来,格瓦拉一行人只有靠自己了。
而他们要对付的,恰恰是最强大的敌人,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

巴里恩托斯 图源:网络
巴里恩托斯是通过军事政变上的台,但在除掉了几个主要的对手后,他又举行了一次总统选举并成功当选。
这次选举大大增强了他的政权合法性,巴里恩托斯本人也很擅长迎合民众,他精于演讲,能够用民粹主义的话语煽动听众,他是个坚定的基督徒,而基督教在玻利维亚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他还会说克丘亚语,克丘亚语是南美洲本地原住民的语言,也是玻利维亚农民最主要的语言,当玻利维亚的上层阶级大多只会说西班牙语时,巴里恩托斯却能用克丘亚语直接和农民们对话,为他在农民中增添了相当的魅力。
在外交上,巴里恩托斯紧跟美国执行反共政策,他大量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允许美国的军事教官来训练他的士兵,这使得他在华盛顿也很受欢迎。
除开这些优势,巴里恩托斯本人还有一项天赋,他是反革命的天才,在玻利维亚之前的历史中,每当左翼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这三方结成联盟的时候,革命就将爆发出摧枯拉朽的力量,而要想不被革命推翻,就必须得打破这三方势力的联盟。
巴里恩托斯发现,农民是这个联盟中最薄弱的一环,他们所处的环境最闭塞、受教育程度最低,他们的生活条件最差、诉求也最低,巴里恩托斯找到了破局的关键——农民。
1964年,巴里恩托斯提出了开创性的“军人—农民联盟”,由他领导的军政府来进行土地改革,保证农民能获得赖以为生的土地,军政府还为农村修路、修学校,而农民则反过来帮助军政府镇压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
巴里恩托斯此举收效显著。
在他任内,玻利维亚农民都团结在了他麾下,并对任何共产主义势力保持警惕。
当巴里恩托斯解散全国矿业工会、对罢工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时,农民直接加入到了政府军一边,势单力薄的工人阶级根本无力反抗,革命力量被迅速摧毁了。
《玻利维亚史》作者克莱恩评价道:
“巴里恩托斯将城市反劳工势力、保守军政权和印第安农民联合在了一起,这样一个强大的联盟是无敌的。”
在这种情况下,格瓦拉要想发动玻利维亚农民去反对巴里恩托斯,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革命条件根本就不成熟。
格瓦拉最好的选择是,等待军农联盟由于军政府自身的腐败和不稳定破裂后再去发动革命,就算一定要现在去,那去城市里发动已经和军政府闹翻的工人阶级,成功率也要更大一些,但格瓦拉受过去经验的影响,坚持从农村起步,他对玻利维亚局势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他又一次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最终他是一头扎进了玻利维亚的农村,而农村恰恰是巴里恩托斯的铁票仓、基本盘。
巴里恩托斯有一个绰号——“玻利维亚农民的最高领袖”,当他宣布格瓦拉是“卡斯特罗派来的特工”,并号召“全国公民以爱国热情抗击这些外来入侵者”时,格瓦拉率领的游击队瞬间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
玻利维亚农民不理解他们、害怕他们,往往游击队还没走到一个村子,村里的农民就全部跑光了,格瓦拉在日记中坦言:
“能确保农民中的大多数保持中立就已经很不错了,想获得他们的支持是以后的事。”
在11个月里,格瓦拉没能吸收到任何一个农民加入游击队,而且这种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巴里恩托斯为了对抗游击队,开展了大面积的“市民行动”计划,包括修路、进行反游击战宣传、给农民送土地、在乡村地区分发学校用品等,士兵和警察在农民之中积极地打探消息,那些供出游击队行踪的农民,会得到赏钱。而支持游击队的,即使你只是帮游击队跑腿买了点东西,也会被逮捕。
巴里恩托斯以此确立了对农民的掌控。
到1967年9月,格瓦拉就发现:
“农民群众非但不援助我们,反而向政府当局通风报信。”
格瓦拉的手下华金所率领的一支支队,就被当地农民引进了政府军的埋伏圈,结果全军覆没。
在一次又一次被农民泄漏行踪后,格瓦拉不得不采取一种饮鸩止渴的生存方式,他们每见到一个农民,往往都必须得先把他控制住,不然这个农民很可能会跑到政府军那里去告密,虽然格瓦拉他们是迫不得已,虽然一旦要进行转移时,他们就会放掉这些农民,但走到这一步,也说明了格瓦拉的群众基础太薄弱,在政府军日复一日的围剿中,他的失败只剩下时间问题。
到1967年10月8日,整个游击队只剩下17个人,而他们的行踪再一次被当地农民透露给了政府军,政府军派出了十倍兵力,其中包括最精锐的、受美国训练的游骑兵部队,他们将游击队包围在了一个小小的峡谷中,切·格瓦拉的命运就此注定了。
06
“别开枪,我是切·格瓦拉。对你来说,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
后世有许多人,试图用这句话来证明格瓦拉是懦夫、胆小鬼,来否定格瓦拉的一生,这里我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这句话的真实性是存疑的,因为格瓦拉本人和他的绝大部分战友,最终都被政府军杀害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格瓦拉被俘前后的许多史料,包括这句话,都是来自于玻利维亚政府军单方面的叙述,而他们出于宣传需要,是有可能编造、虚构、扭曲格瓦拉的话的,毕竟在制造假新闻这件事上,玻利维亚政府军早有前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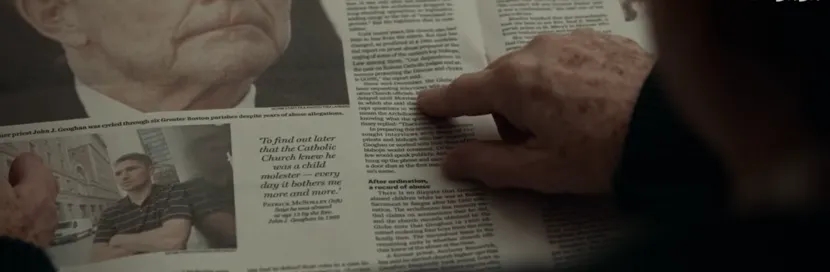
他们总是夸大自己的战果,在几乎每一场战斗中都宣传自己的伤亡更少,甚至在1967年9月11日的广播中,巴里恩托斯就宣布已经击毙了格瓦拉,而格瓦拉当时还活得好好的。
游击队的另一个领导人因蒂,也在1967年6月12日被政府军造谣,说他已经被击毙,但因蒂其实活得比格瓦拉还长,他从政府军的包围圈中逃了出来,一直活到了1969年9月9日,才在拉巴斯被政府军杀害。
考虑到玻利维亚政府军的这些前科,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在这句话上也撒谎了。
而且关于格瓦拉被俘时到底说了什么,玻利维亚政府军自己就有三个版本。
最官方的版本来自于奥万多将军,他是巴里恩托斯的盟友、玻利维亚政府军的总司令,他告诉记者:
“格瓦拉说的是,我是切·格瓦拉,我失败了。”
而俘虏格瓦拉的政府军士兵乌昂卡则说:
“格瓦拉说的是,别开枪,我是切·格瓦拉,对你来说,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
前线指挥官森特诺则说:
“格瓦拉根本没有时间说任何话。”
这三种说法彼此矛盾,让政府军的可信度进一步下降了。
抛开这种种疑点,就算格瓦拉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也不认为这句话就可以证明格瓦拉是一个胆小懦弱的人。
格瓦拉当时腿已经受伤了,他的步枪被击毁,手枪子弹也打空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既无法战斗,也无法自杀,被俘就成了唯一的选项,而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被俘虏、被抓捕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败,卡斯特罗、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都曾经被他们想要推翻的政府抓住过,但他们后来都幸免于难、最终取得了胜利,如果他们当初一被抓就寻死,那反倒见不到后来的胜利了。
就是那些最终牺牲了的革命者,也往往在公开审判、走上刑场时,通过发表一番慷慨激昂地演讲,博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为革命事业做出最后一番贡献。

考虑到被俘后还存在的这种种可能性,格瓦拉要求士兵别一激动就把他打死,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格瓦拉在被捕后的一系列表现,也证明了他绝非胆小懦弱之辈,负责审讯的政府军中校塞里克就认为格瓦拉的态度“傲慢挑衅”,当塞里克指责格瓦拉是在搞“入侵”,说他的游击队员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时,格瓦拉看了看身旁战友的尸体,回答道:
“中校,看看他们,在古巴,这些小伙子拥有他们想要的一切,可是他们仍然来到这里像狗一样死了。”
塞里克继续沿着这个话题,想要得到那些仍然在逃的游击队员的信息,却被格瓦拉拒绝了,格瓦拉说:
“中校,我的记性很差,我不记得了。”
塞里克换了个问题:
“你是古巴人还是阿根廷人?”
格瓦拉回答道:
“我是古巴人、阿根廷人、玻利维亚人、秘鲁人、厄瓜多尔人,你知道的。”
塞里克接着问:
“是什么让你决定到我们国家来作战的?”
“你难道看不到这些农民的生活状态吗?”
格瓦拉反问道:
“他们几乎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在令人痛心的贫困中,只有一间房睡觉、吃饭,无衣可穿,他们像动物一样被人丢弃不顾。”
塞里克没法否认这些事实,他只能说:
“但古巴也有同样的事发生。”
“不,那不是真的。”
格瓦拉回击道:
“我并不否认在古巴也存在贫困,但至少那里的农民还有进步的希望,而玻利维亚人的生活却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完全看不见生存条件的改善。”
在塞里克之后,负责审讯的是美国中情局特工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用尽了花言巧语,想要从格瓦拉那里刺探到具体的作战信息,或者至少引诱他说一些关于卡斯特罗的坏话,却始终没能成功。
交谈到最后,反倒是罗德里格斯被格瓦拉感动到了,当罗德里格斯问格瓦拉有什么遗言时,格瓦拉说:
“告诉卡斯特罗,他很快就会看到美洲革命的胜利,告诉我的妻子,要改嫁,要过得幸福。”
据罗德里格斯回忆: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感伤的时刻,我不再憎恨他了,他的最后时刻到了,他表现得像个男人,面对死亡时他勇敢而又坦然。”

考虑到审判格瓦拉可能引发国际舆论对他的同情,而关押格瓦拉又可能导致他被其他人救走,巴里恩托斯与美国大使商议后决定,直接秘密处死格瓦拉,并对外谎称格瓦拉是因战伤过重、不治身亡。
这种不经审判就秘密处决战俘的行为,既不人道、也违背了国际公约,就是在玻利维亚政府军内部也引起了争议。
据政府军军官阿约罗亚回忆:
“对于在场的所有军官来说,枪杀切·格瓦拉都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命令,森特诺就非常担心,表示反对,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但命令来自玻利维亚最高层,军令如山、不容置疑,最终处决还是执行了。
负责执行的是政府军中士马里奥·特兰,他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格瓦拉的眼睛很大,闪闪发光,当他盯着我看时,我感到头晕目眩,我甚至感觉他只要快速移动一下,就能把我的枪夺走,他对我喊道,冷静点,瞄准好,你不过是要杀一个人。于是我向后退了一步,闭上眼睛,开了枪。”

玻利维亚军官与记者察看切·格瓦拉尸体 图源:网络
07
格瓦拉死了。
他死的时候只有39岁。
围绕着他的死,巴里恩托斯政府编织了一个又一谎言,他们先是声称:
“格瓦拉是在战斗中受伤、不治身亡的。”
这个谎言很快就被戳穿了。
当地的村民、检查格瓦拉尸体的外科医生、甚至政府军内部都流露出质疑的声音。
眼见阴谋败露,刽子手们便纷纷甩锅,马里奥·特兰说:
“我只是遵守了巴里恩托斯总统的处决命令。”
中情局特工则说:
“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希望这位游击队领袖活着,命令是玻利维亚最高指挥部下达的。”
连奥万多将军也声称当初在高层会议上,他是“反对杀死格瓦拉的”。
他们互相推诿,上演了好一番闹剧。
为了掩盖罪行,玻利维亚军政府将格瓦拉的遗体秘密埋藏了起来,只留下一双手证明他们的确消灭了切·格瓦拉。
当格瓦拉的家属来索要遗体时,军政府代表们脸不红心不跳地宣称:
“尸体已经被烧了。”
这个谎言将在三十年后格瓦拉的遗体重现人间时被戳穿。
巴里恩托斯还收缴了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日记中记载了许多对他不利的内容,比如,游击队打过好几场胜仗,往往没付出什么伤亡,就击毙、俘虏了许多政府军,这与政府军长期胜利的宣传是不符的,而且,格瓦拉一共俘虏了85个政府军,他没有杀掉其中任何一个,就是那些假扮成平民偷偷接近的,他也没有杀,他严格地遵守国际公约,把俘虏教育了一番后,就全部释放。有一个被俘的年轻士兵,受到了感召,在被释放前还说自己将会脱离政府军。
格瓦拉的这些行为,完全不符合军政府对他妖魔化的宣传,与军政府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是形成了鲜明对比。
军政府不仅杀害了包括格瓦拉在内的一大批游击队战俘,就是那些帮助游击队的玻利维亚农民,也会受到酷刑。
考虑到日记中存在的不利内容,巴里恩托斯本打算只公开部分日记,还要将日记卖个高价,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朋友、内政部长阿格达斯竟然在此时跳反了。
阿格达斯宣布自己是“秘密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情格瓦拉的遭遇、将格瓦拉视作“英雄、全美洲的榜样”,他逃出玻利维亚,将格瓦拉被砍下的双手、格瓦拉的全部日记交给了古巴政府,并揭露了巴里恩托斯政府与美国政府合谋,残忍杀害格瓦拉的内幕。
阿格达斯后来自愿回国接受审判,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道:
“我之所以离开本国,是因为我自从担任内政部长以来,在履行职责时,亲身体会到我的祖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国家主权,美国设在玻利维亚的机关拥有无上的权力,我成了美国政府的牺牲品。”
阿格达斯承认,是他把日记交给古巴政府的,但他没有索取任何经济报酬,他做这件事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他告诉法官:
“我曾同不少美国官员交谈,得知美国政府打算先激起人们对格瓦拉日记的强烈兴趣,然后把他们自己的说法塞进日记中去,对日记原文进行大幅篡改,其目的是想借这部日记来证明他们对古巴进行多方面的武装侵略,以及在国内实行大规模镇压都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他们阴谋出版一部伪造的或者与原文有很大出入的日记。”
阿格达斯的揭秘令巴里恩托斯政府和美国政府丢尽了颜面,阿格达斯本人也因此遭到暗杀、险些丧命。
他后来举家搬到了古巴,才躲过一劫。
随着真相一步步浮出水面,格瓦拉的死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广泛的同情,巴里恩托斯为了防止人们纪念格瓦拉,甚至把格瓦拉的遇难地——一所小学都给拆掉了。
但这种荒唐的做法阻挡不了愤怒的人们。
在乌拉圭,示威者将玻利维亚大使馆包围了起来;
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政府的几个办公点被焚烧;
在维也纳,示威者抢走了玻利维亚大使馆的国旗。
就是在玻利维亚,大学生们也举行了广泛的悼念活动,他们称赞格瓦拉是全世界青年的象征,要求授予格瓦拉“玻利维亚解放斗士”的称号。
在摆放过格瓦拉遗体的医院房间里,前来悼念的人们在墙上写满了纪念的话语,其中一句是:
“他们没能合上你的眼睛,所以,你是永生的。”
08
1997年10月17日,卡斯特罗来到圣克拉拉市,来见一个老朋友,三十年前他们分开时,彼此都还正值壮年,而三十年后,卡斯特罗已经是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了。
风吹起他花白的胡子,也吹拂过切·格瓦拉木质的棺材,三十年来,卡斯特罗曾经如梦呓般向警卫感叹道:
“自从切走之后,他的音容笑貌每周都会出现在我的睡梦中。”
三十年来,卡斯特罗终于从玻利维亚找回了英雄的骨骸,在将切下葬的这个日子,卡斯特罗感叹道:
“这一块碑石下的土地怎能容得下切?这一方小小的陵墓怎能容得下切?我们所深爱的、却并不算广袤的岛国又如何能容得下切!对于切,唯有他所梦想的世界,他曾经生活并为之奋斗过的那个世界,才有足够的空间。”
几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影子从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当军农联盟破裂、玻利维亚的农民惨死在政府军的枪口下时;当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先后爆发了上万人的抗议游行时;当反帝、反殖民运动在亚非拉三洲一次次风起云涌时,切·格瓦拉的肖像总是会被高高举起,因为他永远年轻,永远反抗,永远带着一双充满决心和愤怒的双眼出现在世人面前。
他早已知晓自己的命运,他说:
“当死亡降临时,只要还有一只耳朵能够听到我们战斗的呐喊,只要还有一双手能接过我们的步枪,我们就了无遗憾。”
他告诉玻利维亚的农民:
“你们会看到,我们来过以后,当局将破天荒地第一次想到你们,他们会答应给你们建造医院或者别的什么,他们之所以会许下这个诺言,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区活动。”
在格瓦拉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一边过着朝不保夕、残酷壮烈的游击生活,一边又对未来的世界抱有无限的柔情和想象,这是他作为一个冷战时代的革命者独有的浪漫,他在信中这样告诉自己的孩子:
“将来,如果帝国主义还在,我们就要一起去消灭它。如果它被消灭了,你,卡米罗还有我,我们就一起去月球度假去。”
格瓦拉死后,游击队中有五名战士从政府军的包围圈中幸存了下来,他们逃到了智利境内,得到了智利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保护,最终平安抵达古巴,智利社会党议员萨尔瓦多·阿连德护送了他们一程。
幸存的五名战士中,有两个玻利维亚人:因蒂和达里奥,他们虽然一度脱险,但后来又返回了玻利维亚,重新组织游击队,他们继承了格瓦拉的遗志,相继牺牲于与政府军的斗争中。
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将他最后一场战斗的日期:10月8号设为了古巴的“游击英雄日”,并将格瓦拉的墓地和纪念馆设置在了圣克拉拉市——他带领游击队取得古巴革命决定性胜利的地方。
“你在想自己的不朽吗?”
“不,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格瓦拉被处决前,与士兵的一段对话
全文完
参考资料:
《切·格瓦拉传》乔恩·李·安德森
《Fidel Castro: My Life: A Spoken Autobiography》 Fidel Castro、 Ignacio Ramonet
《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切·格瓦拉
《拉美传奇英雄格瓦拉》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
《古巴的土地改革及其历史意义》冯秀文
《土地改革——古巴革命的矛头和旗帜——戚·格瓦拉访问记》庞炳、迈庵
《论游击战》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语录》三联书店出版社
《切·格瓦拉:卡斯特罗的回忆》菲德尔·卡斯特罗
《The Military-Peasant Pact》原载于《The Bolivia Reader》
《Historia del pacto militar campesino》Cesar Soto
《玻利维亚史》赫伯特·S.克莱恩
《玻利维亚日记》切·格瓦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古巴对非洲的外交政策》陈云龙
《切·格瓦拉之死》弗罗伊兰·冈萨雷斯、阿蒂斯·库普尔
《切·格瓦拉:未公开的档案》尤里·加夫里科夫
《格瓦拉及其领导的拉美游击运动失败的国际因素》杜娟
《卡斯特罗政府时期古美关系研究(1959-2008)》周璐瑶
《古巴-美国关系50年四题》张凡
《Traveling with Che Guevara》Alberto Granado
来源:亚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