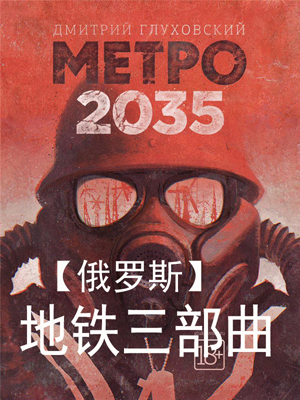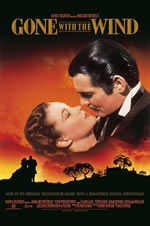桓宣说服樊雅投降,使得祖逖非常高兴,他亲手解开樊雅身上的绳索,热情地接待了他。然后和桓宣、李头等人一起率兵进入谯城。
樊雅要把自己的“官邸”让给祖逖,祖逖没有答应,还让他住在那里,自己找了一个宽绰一点的院子安顿下来。
刚刚安顿好,韩潜走过来:“将军,这一箭之仇不报了?”
祖逖笑了:“你还记着那一箭之仇哪?坐下,听我给你说说一箭之仇的故事。战国时代,有一个齐桓公曾经称霸一时,齐桓公叫公子小白,他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他们两个在齐襄公执政时都在国外避难,公子纠跟着他的师傅管仲在鲁国,公子小白跟着他的师傅鲍叔牙在莒国。后来,齐襄公被杀,大臣们派人到鲁国迎接公子纠回国继任国君。管仲想到在莒国的小白离齐国近,怕他抢先回国继位,就带领一支军队去拦劫小白,小白不顾管仲的阻拦,坚持回国继任国君,于是,管仲向小白放了一支暗箭,他以为小白死了,就从容地护送公子纠回国。没想到小白没被射死,在他师傅鲍叔牙的救治之下,先于公子纠回国继位,管仲只好带着公子纠回到鲁国,在鲁国军队的保护下,想以武力争夺王位,但是,鲁军战败,只得接受齐国的条件:逼死公子纠,抓起管仲。齐国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国君要报一箭之仇,必须亲手杀死管仲,于是,管仲被押往齐国。然而,齐桓公不仅没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管仲为相国,鲍叔牙知道自己才能不如管仲,甘愿作他的副手。在管仲的辅佐之下,齐桓公很快在诸侯中确立了自己霸主地位。我不是齐桓公,樊雅也不是管仲,我的意思是为了收复中原,能多团结一个人是一个人,别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
当天晚上,樊雅请来祖逖、桓宣、冯铁、韩潜、卫策、董昭和李头等人,在他的花厅宴请他们。下人给每位客人斟满了酒,然后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说:“几个月来,樊雅不自量力,拥兵自重,与各位兵戎相见,在下给各位赔罪了。”
祖逖说:“樊将军,我们既然握手言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他和樊雅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卫策说:“对,相逢一笑泯前嫌。”
樊雅举起第二杯酒:“还要感谢桓参军为我指出一条明路。”说着,端起酒杯,又一饮而尽,“往后,樊某人定当在刺史大人的统率下,投身北伐大业,但凭祖豫州驱使,樊某万死不辞。”
酒席间,大家谈笑甚欢,前嫌尽释。酒酣耳热之际,桓宣对祖逖说:“士稚,你可知樊将军为什么能支撑几个月还那么气定神闲吗?”
祖逖问:“为什么?”
桓宣说:“他有曹丞相暗中相助。”
祖逖疑惑了:“是吗?”
桓宣对樊雅说:“还不把你的底牌亮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吗?”
樊雅说:“好吧。”说完,拍了拍手。宴席前面的芍药花盆纷纷退向两旁,刹那间,那个幽深的洞口呈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啊”的一声,惊得面面相觑。樊雅拽了一下旁边的绳子,一架梯子升上来,他率先沿着梯子走下去,大家出于好奇,也顺着梯子先后下去了。
原来,下面别有洞天,一条长长的地道赫然出现在眼前。地道向四面八方延伸,每隔几步,就有一个灯盏,照得地道里明明暗暗,恍恍忽忽。地道很宽,也很高,两个人可以并肩前行。一行人摸索着走了许久,樊雅拿起一根棍子向洞顶敲了三下,洞顶透进一道光亮,上面垂下一架梯子,大家顺着梯子上去,原来这是城外一户人家的屋里。主人盖上地板,地上又不留一丝痕迹了。
主人请大家坐下喝茶,樊雅说:“这就是当年曹操留下的运兵通道。”
祖逖问:“你的粮食就是从这里运送进去的?”
樊雅说:“这样的出口还有不少。”
桓宣对主人说:“老人家,这几天你受委屈了。”
主人说:“委屈倒没什么,你的那些兵可把我吓坏了。听口音,长官是谯国人吧?”
桓宣一笑:“是。咱们是老乡。”
“我说呢。”众人哈哈大笑。
大家依旧从洞口回去,又在地道里各处走了走,地道纵横交错,布局巧妙,结构复杂。大家一边看,一边慨叹工程之浩大,运思之精妙,对曹操的雄才大略赞叹不已。回到樊雅的官邸,已经是半夜时分了。半路上,韩潜悄悄对祖逖说:“还是你高明。”
第二天下午,探马报道:“石勒的大将石虎率两千兵马来攻谯城。”
祖逖带领各营头领登上城墙察看,同时派人去请桓宣,桓宣传话过来,说是他暂时不露面为好。祖逖看到北城门外一片黑压压的骑兵,整齐地排列在一杆绣着硕大“石”字的牙旗下,一个高鼻凹眼的人正在指手画脚地部署军队,想来这个人就是石虎了。只见三股大约二百人的队伍分头从东西两面向南奔去,而主力部队则开始搭建帐篷。看来是不准备立刻发动进攻,而是要先作围城的打算。祖逖吩咐城头上的士兵加紧防守,就和头领们回来了。回到驻地,桓宣已经在等候他们了。
回来的路上,祖逖对石虎的兵力和部署已经了然,如何应付石虎,也已胸有成竹,大家坐下,他先问桓宣:“石将军前来作客,你看该如何接待?”
桓宣笑笑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要攻城,咱们就弓箭伺侯;他要围城,咱们就和他捉迷藏。”
祖逖笑笑说:“好。看起来他今天是要先围城了,我们就和他捉迷藏。”他捋着五绺长髯道,“今夜我们只须如此如此……”
夜黑风高,一队石虎的巡逻兵骑马走在城墙外,人不语,马不叫,悄无声息。突然从地上钻出十几个人,如离弦之箭,窜至骑兵身后,双手捂住骑兵的脑袋,用力一拧,拧断颈椎,把骑兵伏在马上,迅捷地跳下马来,钻进附近一个运兵通道的出口,消失了。城外又复归宁静。
把守西门的石虎骑兵正在帐篷里酣睡,两个哨兵在帐篷外站岗,突然,两个人窜上来,拧断了哨兵的脖子,接着,一大批黑影迅速涌进几顶帐篷,一人一刀,把酣睡的士兵结果了。然后,悄悄牵了在旁边吃夜草的战马,向城门走去。接近城门,点上火折子一闪,城门呀呀地开了,二百多人牵着二百匹马,一声不响地进了城门,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与此同时,东门,南门也演出了同样的一幕。
只是在城外东北角,离石虎的大帐不远处,剧情略有不同,时间:半夜时分。地点:石虎堆放草料的地方。先是十几个人从通道出口钻出来,悄悄接近粮草,两个人摸到哨兵背后,解决了哨兵。然后,十来个人潜进帐篷,打发掉其余的守兵,迅速退回洞口,留下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打着火石,不多时,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两个人才悄悄融进黑夜里。
第二天一早,祖逖对桓宣说:“我们可以接待客人了。”
桓宣说:“今天由我唱主角。”
祖逖问:“我干什么?”
“你?你坐在城楼观风景。”
“行吗?”
“你依我就是。”
卯时,北城门呀呀地开了,一杆绣着“桓”字的牙旗下,桓宣骑马走在最前面,祖逖的军队,李头的军队,桓宣自己的军队,整齐地排列在他的身后,对面,是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石虎和他的骑兵。
桓宣在马上对石虎拱手道:“石将军,别来无恙。”
石虎看见桓宣,先是一惊,也忘了还礼:“怎么是你?”
桓宣坦然一笑:“怎么不能是我?”
“祖逖在哪儿?”
“我们朝廷有个不成文的制度,接待客人要级别对等,接待将军,不必刺史大人出面,我来接待就可以了。将军,你昨晚送来的六百匹马,我们收到了。刺史大人请你进城当面感谢你的见面礼。请!”
石虎那里气炸了肺,刚要扬鞭催马,冲杀过来,但他的士兵已经压不住阵脚,像潮水一样,向后退去,他也只得调转马头,倖倖退去,边走边说:“后会有期!”
桓宣拱手笑道:“恕不远送!”
桓宣退回城里,祖逖问他:“石虎怎么不战自退了?”
桓宣说:“我和他交过几次手,他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的士兵不敢跟我打仗。”
“呃,原来如此!”祖逖觉得越来越离不开桓宣了,他一面把桓宣留住,一面奏请朝廷,请桓宣做谯城内史。
降服了樊雅,赶走了石虎,祖逖总算是在中原站稳了脚跟,他在谯城度过了一个和平的春节。
这天一大早,祖逖刚刚起床,舒展一下胳膊腿,就见李头手提水桶,拿着刷马用的挠子、刷子从马厩走出来,见到祖逖,恭敬地说:“刺史大人起来了?”
祖逖笑着点点头:“你早啊!”
不一会儿,见李头拿着剑向马厩方向走去。他知道李头是去马厩旁边的小院里练剑,就说:“别到那边去了,就在这儿练吧,我也许能给你指点一二。”
李头高兴地说:“中。”说着站好架式,“献丑了。”然后就一招一式地舞起来。
祖逖在一边认真地看着。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司州时和刘琨舞剑的场景,那时候,两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前途有多少凶险,意气风发,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前途充满憧憬,为了报效国家,天不亮就起身练剑,日久天长,在互相切磋中竟然自创了一套剑法,以后两个人天各一方,都有了自己的官职,如今他以豫州刺史的身份到中原收复失地,而刘琨在并州任太守,都在为保卫国家恪尽职守。
他见李头已经收式,站在那里调匀呼吸,就走过去,拿过李头的剑来,边演示边指点:“这一招荒鸡唱晓,要刚劲。刚劲,是这套剑法的特点,到柳絮飘飞一招,要刚中带柔,不是只要柔,而是柔中有刚。到最后大江东去这招,刚中要充满雄健,滚滚滔滔,势不可挡……”
祖逖一招一式地指点,李头频频点头,用心聆听。最后,祖逖说:“以后就这样练,记住,以刚为主,刚中带柔。你的师傅是女人,大概平时练剑时忽视了其中的刚,而偏重于柔,你以后要改过来。”
李头点头称是。
祖逖忽然问道:“你媳妇是跟谁学的呢?”
“这她没说,只是说跟一位名师学的。”
“这套剑法只有我和现今的并州太守刘琨会用,莫非她跟刘琨学的?”
李头摇摇头,憨厚地笑着说:“这我就不知道了。”
侍卫送饭来了,一碗素菜,两个窝头。祖逖走进屋里吃饭,李头也跟进来,他说:“刺史大人就吃这个呀?”
“这还不好吗?你去看看,咱们谯国的老百姓都吃什么?就这还是我们淮阴的百姓一个汗珠摔八瓣种出来的呢。”
祖逖把窝头放在一边,从身旁的干粮包里拿出两张玉米面饼,掰了一块,“嚘吧嚘吧”嚼起来。一边吃一边说:“这是我们老家的饭食,我们老家管玉米叫棒子,管这叫棒子面饼。薄薄的,一嚼,嚘吧脆,香着呢!晾干了,可以存放很长时间,这是行军打仗最好的干粮。你嚐嚐。”
李头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半天,也没嚼烂,好容易咽下去了,忙说:“不中,我吃不惯。”
正吃着,冯铁等一班头领走进来。看见李头的吃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李头忙给大家让座,站在一旁看祖逖吃饭。
祖逖撩起眼皮看了看他说:“怎么,馋了?来,这儿还有两个窝头,坐下一块儿吃吧。”
李头连忙摆手:“不,不中,我怎敢跟刺史大人一个碗里吃饭?”
祖逖假装生气地说:“刺史大人,刺史大人,你怎么老是一口一个刺史大人!”
李头慌恐地说:“那,那叫什么?”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笑够了,祖逖说:“你这人憨厚,老实,又有一身武功,今后咱们一块儿抗击石勒,就是兄弟了,咱们结为兄弟如何?”
李头忙说:“不中,不中,我李头怎敢高攀!”
祖逖说:“你看,你是个男人,我也是个男人,怎么不行?”
大家又是哈哈一笑。韩潜说:“行了,李将军,别推辞了,换了我,我乐意不得呢。”
李头摸着脑袋说:“不是,……好吧,高攀就高攀吧,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一声哥哥了!”
祖逖说:“这就对了。”
李头说:“这……出家在外的,怎么摆香案哪?”
“你我都是军人,何必拘泥小节?”祖逖一指众人,“有他们作证就行了。”
李头说:“也好,那我就叫了。”嘴张了好一会儿,才叫出来,“哥哥!”
大家又是一阵轰笑。
董昭说:“送行的宴席准备好了。”
李头说:“哥哥,我先走一步。”
祖逖说:“慢着。”
李头一愣:“怎么?”
“你先把这两个窝头给我吃了。”
李头的队伍沿着惠济河向西北方向走去,祖逖还从缴获的六百匹马中拨出一百匹送给陈川,也让他们顺便带回去。冬天里地里的麦苗儿不怕踩踏,队伍抄近道开往浚仪。祖逖和李头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离谯城已经不近了,李头说:“哥哥,你回去吧。”
“不,我再送你一程。”
祖逖心里萦绕着一个问题,他迟疑着不知怎么开口。眼看离谯城越来越远了,他终于下了决心,问李头:“你和你媳妇是怎么认识的?”话说出来,马上又后悔了,做哥哥的怎好打听弟妹的事?
李头倒没介意,坦诚地告诉他:“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有一天我和爹早起去黄河边打鱼,一进船舱,有一个女子躺在船舱里睡觉,这女子蓬首垢面,衣衫破旧,身上带着一把剑,我们问她怎么睡在这里,她说她是从洛阳逃出来的,路上遇到了溃退下来的石勒部队的两个士兵,往黄河边上走,他们欺她是一个弱女子,要欺负她,她杀了一个,伤了一个,都扔到黄河里去了,她实在太累了,就躺在船舱里睡着了。我们问她要到哪儿去,她说无处可去,我爹就让我把她领到家里去了。”
祖逖忙问:“以后呢?”
“从那以后,她就住在我家里。后来石勒的军队经常过河来搔扰,我娘怕我们出事,就让我带她到别处躲避一时,我当时正要到嵩山学艺,我娘就让我带她一起去了。几年以后,我们学成回来,正好陈川招兵买马,我们就投奔了陈川。”
祖逖的心嘣嘣地跳了:“你们什么时候成的亲?”
“在嵩山,师傅撮合我们成了亲。”祖逖觉得心里一阵绞痛。
“她的父母……?”
“她后来跟我说,她父亲是长沙王司马乂手下的一位将官,战死以后,她和母亲就寄住在司马乂家里,司马乂被杀以后,她和母亲逃出洛阳,半路上失散了。”
祖逖的心跳得一阵紧似一阵:“她叫什么名字?”
“银屏。”
果然是她!一别十几年,终于有她的下落了,可她,她已经和别人成家了,嫁的又是自己刚刚结拜的兄弟!唉……
他不忍再问,就说:“兄弟,不远送了,这匹马送给你。”
“不中,不中,这是哥哥的坐骑,我怎么能要?”
“这原是张平的马,谢浮送给我的。”
“那也不中,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你实在不要,就送给银屏吧。”
“哥哥,你们认识?”
“认识,我在司马乂手下当骠骑主簿的时候,她就在司马乂家里,那时候她是司马乂的养女。她的剑法还是我教的。后来我到东海王司马越府上供职,司马乂被杀以后,我去找过她,没有找到。司马越攻邺失败,我退回洛阳,又去找她,还是没有找到。”祖逖把缰绳递给李头,“就说是她哥哥送给她的。说来我也十几年没见她了,那时候她也管我叫哥哥。”
李头高兴地说:“原来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他接过缰绳,“我替银屏谢谢哥哥了。”
李头走远了,把祖逖的一颗心也带走了。一阵北风吹来,泪不轻弹的豫州刺史流下了两行眼泪。
回到驻地,头领们还在等他,他第一眼看见冯铁,心里冒出一丝幽怨,但很快就释然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不是也是有妇之夫了吗?头领们告诉他,朝廷的诏书到了,任命桓宣为谯城内史,他也被封为镇西将军。另外,还有并州太守刘琨派人送来的贺信。之后,大家为祖逖和桓宣举杯庆贺,祖逖面带笑容,但心里的一片乌云总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