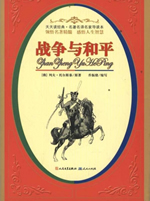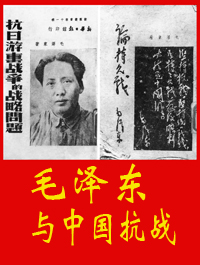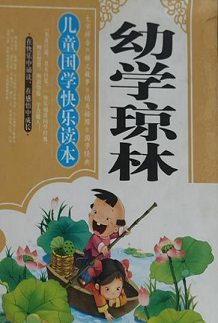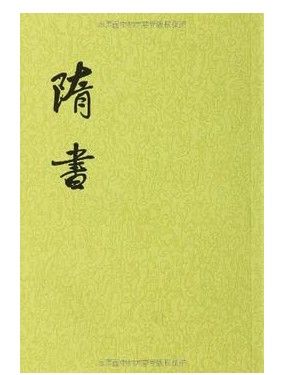不管多少人贬低,都无法扭曲这一事实:近30年来走红的“江湖大师”里,南怀瑾是最货真价实的那一个。比如另一“大师”沪上余先生,前些年吹捧一位爱舞文弄墨日后落马的污吏,(本站注:比如唐双宁之流)。居然言之凿凿“一个官员喜欢文学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腐败分子”,就冲这么一句过于感人的话,敝人就断不肯诚心悦服的,哪管他“苦旅”了多少散文。
我几乎读过南怀瑾的所有作品,始终认为他是高手。其文章、学问与见识,都是有极高修为的,不容小觑。以学问论,南应该算“通人”,大体就是什么书都看,五花八门的杂学都通晓;以作派论,南则当属“术士”,俗话说来就是“走江湖”的。而南怀瑾的麻烦和尴尬就在这里。他无法得到很好的理解:从大学刻板训练出来且颇有学问的读书人,很难欣赏他那一套旧学;而随声是非的大众,又多是盲目追星,压根不能深入他的精神内蕴。骂他的,捧他的,都不是很理解他。这里的原因,也不难推究:因为通人也好,术士也罢,在民国以前都算中国本土主流,但在此之后就算是大抵绝种了。到了今日,文化断层数十年下来,我们早就不大熟悉这样的怪人,更难理解这样的异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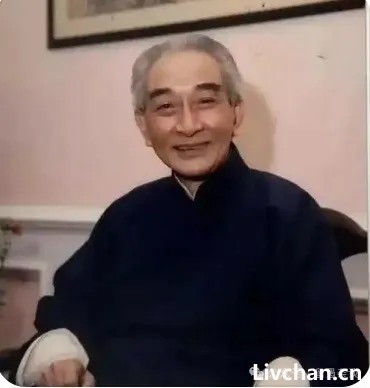
在当下的社会,旧派通人与江湖学者,都是无法归类的。比如说,南怀瑾好歹也是个“著名学者”,其所著《论语别裁》等畅销书腰封都这么介绍的,但你若要延请他到知识分子最该去的大学教书,大家都会很头疼:我们不知道应该分他到哪个学院哪个系去,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科目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去教。打坐,风水,禅修,玄学,相术,都是南怀瑾最精通的,本身也确实都是“传统文化”,可我们的大学断然不会开设这些“奇奇怪怪”到“怪力乱神”的课程。一句话就是,在现有的社会与学术评价体系里,我们已经找不到合适南怀瑾们的位置了,简直无以名之。因此,尽管晚年南怀瑾都成“大师”了,但据我所知,没有一所大学敢授予他“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之类的现代学术认证头衔。
主流的学术体制,始终都在有意无意地排斥他。而且,很多人秉持“现代科学”理念,会不假思索地认定南怀瑾为“旁门左道”,激烈者甚至认为他的东西就该付之一炬。我相熟的一位中文系博士好友就是这么坚持的。我就从不这么认为。理由是很简单的,就是起码以我的认知,南怀瑾的学问本身是很好的,他的多数著作都是颇精深的,绝非浪得虚名,当得起相关领域“必读书”之列。以段位论,什么曾仕强麦玲玲之流,压根与之不在一个层次,南怀瑾妥妥碾压。南的学问,我以为最大特色就8个字——“博采异谋,通透澄明”,这也是他最有价值的地方。这是无数的“资深教授”“长江学者”都看不到的境地。南实际上是将文史哲佛艺道6大宗打成了一片,给融会贯通了,给左右逢源了,给圆融无碍了。中国传统有个术语,叫“化境”。
这样的人,当下的中国,已经完全没有。如果非要找一位类似的,我以为前一段刚去世的谈锡永(王亭之)老先生,差不多算是一路人。他们都是什么书都读,绝不会让故纸堆自缚手脚的人,但纸上学问的掌握程度又不会比任何学院教授差,毕生也都在追求一种“活学问”。比如,一般知识分子论起行业偶像,无非顾炎武黄宗羲柏拉图休谟这类“规范人物”,而南怀瑾谈锡永们的认可的读书人典范,就会比较倾向于张良诸葛亮这种“杂学”或“事功”派。谁敢说张良孔明们就不是中国主流文化人,他们的所思所虑就不是曾经的华夏正统学说呢?他们变得可疑,只能说学术规范转移了,学术传统变异了,评价体系也面目全非了。实际上,他们这类人,毕生也都在搞学术研究,只不过他们研究方向,重在“生命谛观”与“世事照察”这两方面,此即过去所谓的“践履功夫”。
这样说起来,南怀瑾的学问,其实非常正宗,一点都不旁门。比如他那本《禅海蠡测》,十足正经的学术专著,可谓禅宗史研究正脉,文字之典雅,见识之高明,框架之谨严,放在“民国学术经典”系列完全没扞格。以传统学问厚薄论,南怀瑾也是可以与钱锺书陈寅恪这些学院派公认大家并排坐下的,只不过魏紫姚黄各有擅场,钱在文学,陈在史学,南在佛学,或学术地位上也容有高下之别,仅此而已。南可并不“民科”,他只是不耻于学者之林,对只会寻章摘句徒有知解的“大学教授”者流看不上。当代人觉得南怀瑾“怪”,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学术理路彻底西化了,自家老祖宗的路数反倒陌生了,看不懂了,而且要排斥了。
我倒不是要捧南怀瑾,更无意批评现代学术的西化路径。我只是遵照历史线索,说出一种事实。更何况,不必为之讳言,南的问题也确实不少。总体上,他的学术花样很多,作品中糟粕也不少,信口开河的暴论比比皆是,其为人更是沾染太多江湖习气。这些都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的。当然,更为糟糕的,是当下很多“南粉”,言必将他们的“南师”彻底完美化,这种趋向才是最要命,也是最招黑的。 当年,郑板桥受了很多迂生的气,痛觉一些儒粉不可理喻,很严厉地嘲讽那些言必称至圣先师的“秀才”们才是“孔子之罪人”,大概就是类似意思吧?
来源:留愚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