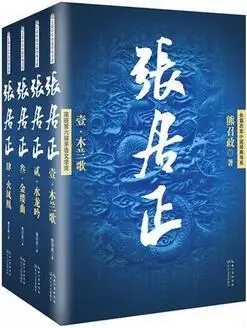谭泊
现在,老屋门前的那条河,只能叫做池塘了。
世上万物,似乎都有一个生命周期。河也一样。那条小河也曾有过它的青春时光。那时它是流动的,清澈的,在一场夏雨过后,甚至可以看到活泼的鱼儿蹿出水面欢蹦乱跳。
那是它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时间节点。
时间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在某个时间点,你可以呈现那样一种状态,心安理得,而在另一个时间点,你就必须换一种方式存在。在我懵懵懂懂接触这个世界的时侯,有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就一个人坐在老屋台门口的门槛上,静静地看着门前的风景,看一只小狗慢悠悠地走过,看门前那条小河。大人们忙着他们的事,没有谁来呼唤我。
那真是一个奇妙的年龄。再年幼一点,我可能正在不停地哭泣,再年长一点,我可能需要应付一些事情了,比如作业,比如打架,比如帮着父母剥蚕豆或是喂猪食。生命中,也许就只有那么一个时间段,我可以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既不打扰大人,也不被大人打扰,我可以有大把的时间,象个乖孩子又象个傻孩子,安静地坐在门槛上。
门槛与河流是平行的。被岁月打磨得油光发亮的枕木门槛看上去是那样的小,而河流,大得就象是整个世界。
河也一样。那时,没有谁特别地去疼它,关注它,但它就好好地存在着。
那时,河流是会结冰的。
那年冬天似乎比往年的任何一个冬天都要寒冷,裹得厚厚实实又破破烂烂的大人们站在岸上,大声地笑着,喊着,偶而往冰面上扔一个硬币或者一颗石子。冬日的阳光照着他们,照着那个小心翼翼地走在在冰面上俯身摸硬币的男孩。
一个慌慌张张的女人赶过来了,跺着脚喊:快上来,快上来,咱不要那些臭钱!
那个脸涨得通红的小男孩,憋足了气:不。
女人急得快要流泪了:快上来,娘给你钱,你要多少娘给你多少。
那个蹲在冰面上冷得发颤的男孩,依然眼眶红红的,委屈而坚决地说:不。
女人于是流泪了。她把脸转向那些站在岸上的大人们,不骂他们,只把一个女人的眼泪流给他们。
那时,会有一只小鸟,一不小心就从河边那棵高大的泡桐树上掉落下来。
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沿着河岸缓慢地行走在黄昏中。后来天色渐渐暗下来,后来晚风更紧了,再后来这个孤独的小男孩便看到有一个小东西从那棵光秃秃的大泡桐树下掉下来。
小男孩看得清清楚楚,他说:那是一只鸟。
他于是趴下来,伸出双手抓住岸边的一块石头,极为大胆地把头探向河面。这时侯一个女人的声音便远远地传来了:阿云——,阿云——
那个叫阿云的男孩没有理会妈妈的叫喊。那一刻他显示出极大的耐心,目不转睛地盯着已经模糊不清的河面。他一定在想,等那只鸟一钻出岸边的那个洞,他就把它捉住,那只鸟一定是受伤了,他得把它带回家,然后给它吃好的住好的,然后等天气暖和的时侯,就放它在空中飞————让它自由地飞翔还是牵着一根长线,那就只有小男孩自己知道了。
女人的声音渐渐地近了。她已经看到了儿子趴在河边。这个淘气的孩子让妈妈不禁有些生气,她的声音开始变得焦急而恼怒:“回家去,快跟妈妈回家去!”
“妈,一只鸟掉下来了,它钻进那个洞里去了……”
“回去!”
“妈,我亲眼看到的,一只鸟……”
但是女人没有看见。女人硬是把儿子背在身上,任这个固执而淘气的孩子一遍遍喊叫。
在时间的长河中,那些片断是如此清晰。那条门前的小河,在我童年目光的注视下,大部分时侯都是缓缓地流动着,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叙述着,不急不慢。那时,小河连通着两个村的主要河道,而它们,又都与一条叫“官河”的大河相连通。所以,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河水突然就裹挟着各种各样的漂浮物暴涨起来————那是“官河”的上游开闸放水了。
门前的小河是那样小,但在某一刻,它又是那样大。它不由分说地升腾起浑浊的水面,又象潮水一样很快地消退,恢复它的清爽和宁静。它象迷一样在我稚嫩的童年留下一个个问号。坐在老屋台门口门槛上的时光,也许就是我人生最惬意的巅峰时刻,我不用关心谁,好象谁也不用特别地关心我,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存在,我唯一关心的是,那些水,为什么会突然到来,而才过了那么一会儿,它们就突然退去了呢?
那时,我无法理解水的力量。它纽系着一个村庄与外面的世界,它使时空不再那么轻易地割裂。而我坐在门槛上,目光能及的最远处,就是一片长着枇杷、无花果和各种各样蔬菜的园地,笔直的河流从中间穿过,一棵枝枯叶疏的老乌桕则歪歪斜斜地横卧在水面。大人们说,几十年了,它就一直是这样。
从我开始懂事起,直到它最终消失,每次看到这棵艰难地横卧在水面上的老树,内心就会涌上一种由衷的敬意。那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对顽强生命的礼赞。
而坐在门槛上望着门前小河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紧急着,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在漫不经心中悄悄地过去。每一个时间节点,我都是不同的我。我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门槛上无所事事地看一条河了。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撇开哲学意义上的理解,在现实的河流中,我就有一种深刻的体悟:似乎才刚刚离开老家,离开老屋门前那条小河,当我再次回来时,映入眼帘的,竟然,早已不是那条熟悉的河了。
先是那片园地消失了。伴随着园地消失的,是穿越其间的那段河流消失了,那棵顽强生存了许多年的老乌桕消失了。当然,还有时间,那个园地上草木繁盛的时间节点,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知不觉中,连通另一个村的那段河道也消失了…………河道的消失,在某些时间节点上,就象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万物慢慢生长,河流,慢慢萎缩。大地上那些人们熟视无睹或是惊艳无比的变化,在一条村河上毫无新意地演绎。
有一年夏季,暴雨倾泻而下,半个村庄浸泡在一片洪水中。当洪水退去,村里下定决心要把那段尚存的河道疏浚得更象一条河道。于是,村里出了一笔钱,把疏浚河道的工程包给了一个叫“大头”的中年人。于是,强壮如牛的大头就抡起铁耙、铁锹,像远古的愚公,带着一家人干了起来。在下一个雨季到来之前,大头争分夺秒、不知疲倦地干着,想着那笔即将到手的钱,他阔大敦厚的脸庞始终洋溢着笑容。
大头的活儿很快就干完了。
但是那时,曾经的小河已经只是一个池塘了。失去了与邻近两个村的水域连通,失去了与“官河“的终极联系,一场简易的整容已经无法重新让这条河流焕发昔日的风采了。强壮的大头无法阻挡那些断断续续倾倒的垃圾和泥土,四季豆和南瓜棚架上疯长的藤蔓在不断地延伸。一条河流在岁月流逝中的嬗变,大头根本无法阻挡。
还有更多的变化,大头无法阻挡。
那时,我已经外出求学。在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后,我回到老家,在跟母亲的闲谈中,意外地得知,一向体强力壮的大头,竟然得了恶疾,三个月不到就去世了,“前一阵子还好好的,一下子,说没就没了。“
母亲的娘家跟大头一家有着不算太远的亲戚关系。说到大头的死,母亲的眼中忍不住充满了伤感。
那时侯我就想,死亡,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它就像一棵老乌桕的消失,或者,就像一段河流的消失吧。
现在,老屋门前的那条河,只能叫池塘了。
池塘里漂浮着一种说不上名的水草,被白色的PV管围隔成几个方格,一丝不乱,翠绿欲滴。在治水最火热的那些时光,这样的水草遍布大江小河,成为一道水上风景。水草被限定在框框内,有秩序地发挥着净水的功能。至少,它使水面看上去是那样的清洁。
但是现在,我好象不太关心那些水草,关心它们是否真的能发挥治水的功能。在我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隐隐地发问:现在,这个仅存的池塘,它还能存在多久呢?未来的一天,老屋大概率是要拆迁的,而老屋前面的这个池塘,大概率也将被填平吧,从此,永远消失。
想想也有点好笑,老屋也要消失了,为什么还要去关注老屋门前一个池塘的未来呢?
未来,我们只会怀念那些曾经的时间,和一段曾经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