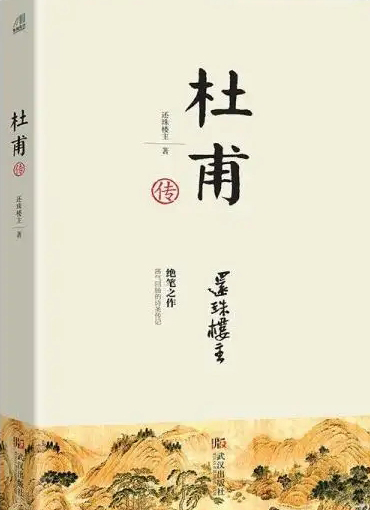文|刘荒田
普普通通的夏日黄昏,暮色转暗。我坐在餐桌的东端,埋头嚼鲜嫩而价昂的番薯叶,隐隐感到光线异常,抬眼,远方的海平线,半轮日头正在沉没。如何比喻它?比作杀伐征略大功告成的帝王,面对丹墀上俯伏着的臣子,即将接受“吾皇万岁”的山呼,向龙椅徐徐落座?否,不如比作一片秋日的红叶辞枝、一颗火红的苹果坠地、人散后篝火堆里最后一段木炭熄灭。
总之,它不把一切当回事的超脱、沉稳、悠然,让我搁下筷子,不敢把眼球转一转。
有一种说法:日落耗时三分钟。家里的挂钟不必看,我可据目测断定不需要这么久,也许只有一分钟,理由是:它整个消失,只在我十来次眨眼之内。
有日落必有日出。我享受初阳温暖的光线,多半在朝东的卧室里。退休以后,赖床躺着看电子书,阳光像猫尾巴般扫过脸颊。
阳台也朝东。老妻常常赶在日头移到头顶之前把半干的衣服晾在阳台,她坚定地认为,日头的气味最好闻,衣服须被带光芒的芳香染一遍。
看落日,在同一个位置,一坐就是二十多年。中年到老年,日复一日地被太阳的临别秋波关照着,同一张脸的皱纹一次次地被灌满余晖。我能不赞美金黄色的千篇一律吗?
日出日落可是简单的重复?于它自己,当然是时间的脉搏、宇宙一个角落的节律。于人,就是生命本身,一天的早晨、中午、黄昏,就是“微缩”周期。
许多年前,我参加一位外国朋友的婚礼,新娘子请出年迈的父亲,在舞池中欣然起舞。父亲年过七旬,腿脚不大灵便,女儿迁就着,舞步虽然缓慢,但配合默契。这时,台上乐队的女歌手在轻柔的序曲引领下,《日出日落》曼声而出。这是风靡全球的名曲,出自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影片中,一对犹太老夫妇和新婚的女儿、女婿在火车站道别,喜悦与伤感交错的场景,所配的就是这支歌。
“这是我带大的小女孩吗?这是在玩耍的小男孩吗?我不记得他们长大了啊,他们是何时长大的呢?她是何时变成个美人的?他是何时长这么高的?昨天他们不是都还很小吗?”全场肃静,只有歌声盘旋,我的心剧烈跳动。
“日落、日出、日落,时光飞逝,幼苗在一夜之间成长为向日葵,在我们注视下绽放。日出、日落,日出、日落,岁月飞逝,季节不断更替,满载着欢欣与泪水……”台上的主人席,一排十多人,先是老一辈低下头,用餐巾或手帕揩眼睛。然后是小一辈,看着家长,情绪起了变化。
旋律激越起来,台下二十多桌客人,一双双眼睛闪着晶莹的光。新娘终于忍受不住,在“日出日落”复调中,紧紧搂抱着父亲,哭泣起来。父亲一脸是泪,然而笑容灿烂。最后,全体站立,高唱“日出日落”,大家离开座位,与亲友拥抱。歌手一次次地唱,谢幕时脸上湿漉漉的。
每一次这样面对日出日落,《日出日落》这首歌必在耳畔响起。
我也有儿女啊!42年前端午节刚过,我与妻儿在广州长堤和故土的朝阳告别,坐上开往异乡的车。车厢里,六岁的哥哥和一岁多的妹妹哪里知道愁滋味?一个劲儿地玩闹。一个陌生人在邻座吃荔枝,分了几颗给他们。他们吃了,使劲把核扔出窗外,那依然是家乡的土地。前方,是崭新的第二故乡。从此,异乡的日出日落如走马灯,转到如今。
一样的日出日落,一样的季节嬗递,一样的升沉生灭。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所拥有的,却是不一样的年岁、不一样的人间与心境,唯太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