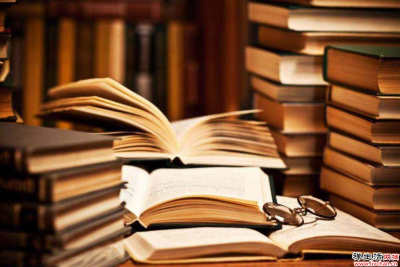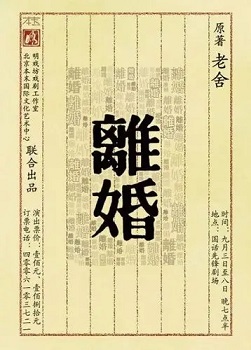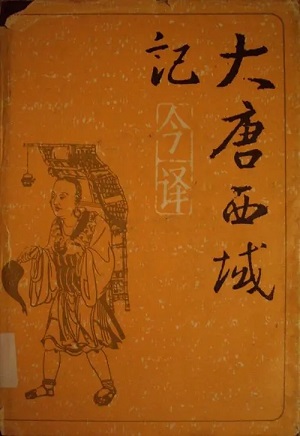在另外一种诗格中,杨克找到了新符号的意义
文/一川
在国家叙事中把握个人经验时,常会看到某种过于用力的表达导致诗性格调的弱化。而在杨克的文本中,一种透彻的秉性依旧在那守望着,这种守望不是减弱而是加强。陌生化的语言,生活化的叙事,静物的部分动作化,感情的部分细节化,主体视角中形成集体视觉的统一,互相呼应,交织于一起,“此时北方的长街宽阔而安静/四合院从容入梦 如此幸福的午夜/我听见头顶上有一张树叶在干燥中脆响/人很小 风很强劲/秋天的星空高起来了/路灯足以照彻一个人内心的角落”。在卑微和坚强中,他抓住了存在中最重要的部分,以具象的“一根枝桠”走向整体的“世界”,正是以最小的事物抵达至高存在者的意义。

那种繁复咀嚼痛楚后的真切悲悯呈现在文本中,那是什么?是工业文明中对农耕文明仅存的一点点希望,“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低微的事业中选择了历史唯一的正确性,“厂房”“矮脚稻”的意象以“抱住”的方式,勾画了现代人的“器”与“道”割裂感。
杨克以更柔韧的感知系统触发当下性,并保持最真的心绪表达,交织混合的拟喻手法,见到天地之时也见到了人间,他以历史尘埃发出的悲悯意识或将以新的悲悯展开。作为诗人而言,正是那种无限接近“存在”与“非存在”“有意义”与“无意义”的价值判断让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成色,不能说这会产生三六九等之分,而应该为无限接近诗的内部而骄傲。
这是通达现实以上和现实以下的路途,也只有这一条路走向个人的内心,或集体的意志中,“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此处的诗行通过修辞指向真诚,“亿万儿女手牵着手/在枝头上酸酸甜甜微笑/多汁的秋天啊是临盆的孕妇/我想记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户”,感受力正通过植物与人迁移到内在统一的模型中,支点却是朴实无华的,“窗户”“微笑”“孕妇”等意象纵横交错以生活化的现代主义形象撑开“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忍受着龟裂土地的艰辛/每一根青筋都代表他们的苦/我发现他们的手掌非常耐看/我发现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回到杨克写作意义本身,必是探寻寻常事物中人类社会的本质,且这本质在现象学中有着符号般的意义。

附:杨克诗歌作品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外二首)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
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
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
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
亿万儿女手牵着手
在枝头上酸酸甜甜微笑
多汁的秋天啊是临盆的孕妇
我想记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户
我抚摸石榴内部微黄色的果膜
就是在抚摸我新鲜的祖国
我看见相邻的一个个省份
向阳的东部靠着背阴的西部
我看见头戴花冠的高原女儿
每一个的脸蛋儿都红扑扑
穿石榴裙的姐妹啊亭亭玉立
石榴花的嘴唇凝红欲滴
我还看见石榴的一道裂口
那些风餐露宿的兄弟
我至亲至爱的好兄弟啊
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
忍受着龟裂土地的艰辛
每一根青筋都代表他们的苦
我发现他们的手掌非常耐看
我发现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
痛楚喊醒了大片的叶子
它们沿着春风的诱惑疯长
主干以及许多枝干接受了感召
枝干又分蘖纵横交错的枝条
枝条上神采飞扬的花团锦簇
那雨水泼不灭它们的火焰
一朵一朵呀既重又轻
花蕾的风铃摇醒了黎明
太阳这头金毛雄狮还没有老
它已跳上树枝开始了舞蹈
我伫立在辉煌的梦想里
凝视每一棵朝向天空的石榴树
如同一个公民谦卑地弯腰
掏出一颗拳拳的心
丰韵的身子挂着满树的微笑
◎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
厂房的脚趾缝
矮脚稻
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它的根锚
疲惫地张着
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
从一片亮汪汪的阳光里
我看见禾叶
耸起的背脊
一株株稻穗在拔节
谷粒灌浆 在夏风中微微笑着
跟我交谈
顿时我从喧嚣浮躁的汪洋大海里
拧干自己
像一件白衬衣
昨天我怎么也没想到
在东莞
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
青黄的稻穗
一直晃在
欣喜和悲痛的瞬间
◎高秋
此时北方的长街宽阔而安静
四合院从容入梦 如此幸福的午夜
我听见头顶上有一张树叶在干燥中脆响
人很小 风很强劲
秋天的星空高起来了
路灯足以照彻一个人内心的角落
我独自沿着林荫道往前走
突然想抱抱路边的一棵大树
这些挺立天地间的高大灵魂
没有一根枝桠 我想栖息
我只想更靠近这个世界
(原载2022年8月12日《澳门晚报》A8版)

杨克,编审,一级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出版《杨克的诗》《有关与无关》《我说出了风的形状》《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等12部中文诗集、4部散文随笔集和1部文集以及8种外语诗集。翻译为16种语言发表。
一川,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欧洲诗人》特约诗评员。作品散见于《星星》《扬子江》《诗潮》《鸭绿江》《绿洲》《解放军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