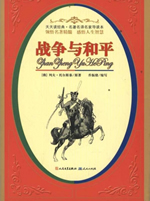文:裴氏春秋 图:大俗摄影
二叔好赌。
他的这一嗜好大概是基因传承。他的父亲排行老三,我管他喊三爷爷。我与他不是很亲,嫡系上都是一个家族,也远不到哪儿去。
记得三爷爷在世时,一场大病之后就伛偻着腰,走路要靠板凳作为辅助。即使这样,仍然没有阻滞他去往博场的脚步。板凳低矮,他低着头艰难地前行,几乎是匍匐着,倘若碰到人与他打招呼,便抬起头,眼睛里蓄满赌性的贪婪。
三爷爷离世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副通吃的好牌,是王炸。那一副牌的赌资很多,他禁不住激动,去了。三爷爷几乎没有给二叔留下什么家业。
那时候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庄户人家基本上都住进了青砖红瓦的房子,二叔家里还是三间土坯墙的主房和两间低矮的配房。
他的院墙也是土筑的,经年累月的风化已经显得苍苍斑痕。好在二叔撑起这个家以后从赌注里省出来些钱,将屋顶的茅草换成了红瓦。从远处看,院子里也有了一点生机。
在农村,赌性的顽劣往往就注定耽误了成家的大事,因为媒婆也是有责任的,他们心里都有杆称,掂量个差不多才能牵这根红线。如果谁家女孩嫁到了火坑里,媒人的好日子也到了尽头。因此没有哪个媒婆没病拎一个药壶放在家里。
二叔三十多岁,本地女孩都对他避而远之,成家无望。然而山不转路转,八十年代的时候国家法治还不健全,对买卖婚姻的立法还没有完整体系,飞来风的女孩比比皆是,于是他花钱买了一个。
那女孩个头高挑,长得也很好看,绝对配得上二叔。自从她进了二叔的家门,我就称她为二婶。如果二叔那时候能正儿八经地过日子,生活照样和和美美。可惜博场上的引力,如强大的虹吸效应,抽空了他所有的理智,一门心思赴在博场里阔掷豪赌。
解决了温饱的村里人开始思忖着致富,每家每户都养猪、养羊、养鸡。二婶也是过日子的一把好手,不仅猪羊满圈,而且也真地做到了“鸡飞狗跳”,把往年残垣断壁、死气沉沉的农家小院搞得生动活泼起来。
二婶养这些畜禽会挣钱,二叔会花钱。他花的钱像打水漂一样,过了个手瘾就不见了踪影,并没有置办多少家当。堂屋还是那座半吊子堂屋,配房还是那所脱脊漏雨的配房,二婶挣那么多的钱,当她们的女儿出生时,竟买不起奶粉。
我母亲还有些关系与他比较亲近的人劝他回心转意,他辩解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人总得有一个爱好吧?如果再不赌博,那一辈子不就白活了。
二婶见跟着二叔生活无望,在九二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她们的女儿两岁多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谁都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剩下的就是他们父女俩个相依为命地过日子。
他的女儿从小跟着他在赌博场里长大。饿了,他就给她在商店里买面包、辣条;渴了,就买汽水,总之,只要能不用回家做饭,腾出更多时间泡在赌博场里,什么办法二叔都能想得出来。但他的女儿出淤泥而不染,对于他的行径是抗拒的,感到十分厌恶,常常以绝食抗议,然而换来的效果甚微。
我们这儿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此地四通八达,也是农业经济发展空间较为广泛的区域,是大蒜、洋葱的主产区。
这些作物虽然集劳动力强,但收益比起小麦、玉米来,大得不是一星半点,是没有外收入人家的首选。二叔也栽种这些品种,每年都有,面积还不小。
夏天成熟期到了,别人忙着收获,他也劳碌着。别人开着车去出售,他也去出售。别人美滋滋地数钱,他也美滋滋地数钱。
没见他的生活有什么起色,倒是经常看见他沮丧着脸,穿着破旧的衣服挨家挨户地去借钱。
由于地基下陷,他屋子的门窗开关吱吱呀呀,许多年过去了,还是那几扇旧木门和褪了色的旧窗户。
他的女儿慢慢长大,外出打工时,觅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她的婆家是搞装修的,有自己的独立门市部。他们看着她们家过得实在太寒酸,才给他换了新的门、新的窗子。
几年后,政府扶贫,给他推倒了土坯主房,取而代之的是一所新房。
去年过春节回家,我看见二叔在还赌债,数额三千五,是一年前借本村人的。此人在建筑工程公司上班,是小头目,年薪可观,这些小钱不在乎,也不要了,只是希望他以后好好过日子,不要再傻愣愣地把辛辛苦苦一年赚来的钱往赌桌上扔。
今年过年回家,我又在赌博里见到了二叔。他坐在对着庄家的天门。那时候他一定是输得很惨,枯树皮一样的手颤抖着,伸向褪色棉袄的衣兜里摸摸挲挲,好长时间才掏出来一沓皱得不成样子十块或二十块钱的钞票。
唉!这个执迷不悟的二叔,怕是这一辈子也难以改正过来了。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历史书上没详细告诉我们的商代的“人牲”和“殉葬”还有“禅让”——俺们学的历史可能是错的…
01 先来普及两个汉字:不准。不准爆粗,不准放火,不准盗墓。暂停一下,如果你念的是bù zhǔn ,就出了点小问题。在这儿,不准,音fǒu biāo,是个人名,姓不名准,西晋... - 鲁迅(右)和周作人(左)1985年,也就是34年前,我在《鲁迅研究动态》第5期发表过一篇《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后收入拙著《鲁迅史实求真录》,湖南...
- 来源:知乎APP作者寺内正道施从滨死的其实也一点不值得同情,第三次直奉战争中,施从滨手上也是有战争罪行的。冷知识:1925年第三次直奉战争时,因为战前和奉系的一系列血海深...
- 来源:根据河北旅游文化广播系列节目《燕赵传奇》音频整理主持人:韩伟/主讲嘉宾:褚亚玲韩伟:上一回咱们听过了慷慨激昂的河北丝弦,结识了侠肝义胆的梨园豪杰,一曲丝弦犹绕...
-
 12019年,莫言应邀为赵尚志将军殉国处所立石碑撰写碑铭,并为赵将军雕像撰诗一首:白山黑水建奇功,剑影刀光气若虹。首葬丘陵藏猛虎,躯投江海变蛟龙。身经百难心不改,体被双...
12019年,莫言应邀为赵尚志将军殉国处所立石碑撰写碑铭,并为赵将军雕像撰诗一首:白山黑水建奇功,剑影刀光气若虹。首葬丘陵藏猛虎,躯投江海变蛟龙。身经百难心不改,体被双... -
 2009年3月22日,早晨6:30,美国弗吉尼亚州,晨光明媚,微风和煦,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祥和安宁的环境中。一对夫妇正在公园小道上像往常一样晨练。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死神正...
2009年3月22日,早晨6:30,美国弗吉尼亚州,晨光明媚,微风和煦,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祥和安宁的环境中。一对夫妇正在公园小道上像往常一样晨练。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死神正... -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历史书不会告诉你一、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已经进行7年,但对于欧洲来说,才刚刚走到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上。那年3月,纳粹德国的军队进入奥地...
- 第一、价值观的改革几千年来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自私自利、当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价值观被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这样的无产阶级价值观所代替,延续了几千年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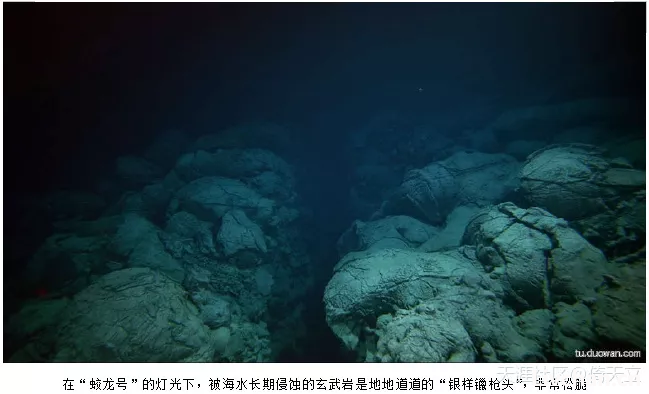
倚天立:地中海的海市蜃楼 ——对胡夫金字塔、亚历山大港和罗塞塔石碑的质疑
【何新先生的推荐按语】倚天立先生的这一组论文,理性、科学、透彻,从实证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所谓辉煌的地中海史前文明的不可信与荒诞无稽,非常值得一读,特予以鼎力推荐。此文原发于天涯论坛,鄙人读后深以为赞,可圈可点。特予略作整理,以连载形式陆续介绍,请朋友们给予关注。 -
 011898年6月9日,北京各国事务衙门,大清(李鸿章)和大英(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条约,1898年7月1日起,大清将要把广东省新安县(今广...
011898年6月9日,北京各国事务衙门,大清(李鸿章)和大英(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条约,1898年7月1日起,大清将要把广东省新安县(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