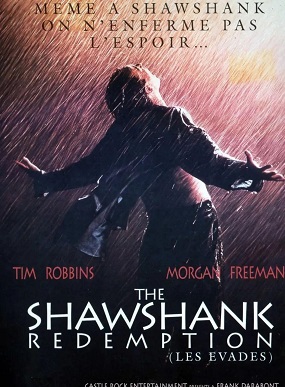郭嵩焘生平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县人,18岁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与同学曾国藩、刘蓉结为“金兰①”。道光十八年(1838年)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二年(1852年),加入曾幕,参赞其事,助创“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军。郭为“湘军”及其水师筹措粮饷,在奔走上海期间开始结识西洋人,接触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因对清廷固步自封深感遗憾,于咸丰六年(1856年),辞职回湘阴县城主讲仰高书院。咸丰七年(1857年),奉诏赴京,以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咸丰九年(1859年)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办理天津防务,因功赏戴花翎。不久,奉旨赴山东沿海稽查税务,以裕饷源。郭在京供职3年,咸丰帝先后5次召见,详询军政治乱之道。郭嵩焘深感国事衰败,帝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遂于咸丰十年(1860年)再次辞职回湘阴,开始撰写《绥边征实》一书,坦陈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内忧外患。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任苏松粮道,旋即调任两淮盐运使;次年,任广东巡抚,因捕盗、筹饷、清理积案有功,被赐二品顶戴。后因督抚交恶、粤绅诋毁,再加上郭(嵩焘)左(宗棠)构怨,于同治五年(1866年)3月被开缺(免职)回到故里,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主编了《湘阴县图志》。

郭嵩焘一生数度辞职归乡,又数度被朝廷召回并委以重任,最突出的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刻影响。
郭嵩焘是中国最早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早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就曾在浙江亲自参与抗英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又在天津亲自参与海防事宜。通过这些事件,他认识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即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历史趋势。他不仅利用一切机会,虚心了解和体察西方情势,而且通过对现实和历史经验的研究,认真总结“驭夷之道”。加上他早年接触西洋人的阅历,到了19世纪70年代,他成了朝野公认的最“精透”洋务的人。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再次奉诏入京后,于次年以敏锐的目光明确提出:“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权,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调任礼部左侍郎,先出使英国,任中国驻英公使,继而兼任驻法公使,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公使。
此前,由于中国尚无派遣驻外使节的先例,郭嵩焘被遣使时,朝廷群臣视为奇耻大辱,撰联讽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湘籍绅士们更不愿与其为伍,亲朋好友也纷纷劝他推卸,郭皆不为所动,决心忍辱负重,毅然出使。光绪二年(1876年)9月,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等一行近30人,由上海启航赴英,途经东海、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他认真考察沿途各地的政教、军事、民情、风俗、物产贸易等情况,并在香港、新加坡、锡兰、马尔他等地逗留,参观游览,开阔视野,与船上的西方人士交谈,多方了解详情,提出了新的“夷夏观”,并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由伦敦寄回总理衙门刊刻。书中有对西方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有关于学习研究西方治国之道和科学技术及引进先进设备的建议,多为开明之举,却遭到国内守旧派的群起攻击和弹劾:“中洋毒”、“有二心”、“桧党”等罪名不约而至。但他不为所动,在英法期间,积极开展外交工作,广泛接触学者及世界名流,精心考究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国防、民俗、教育等得失情况,向清廷提出效法西方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当见到英国新闻机构关于中国吸鸦片者众的图片和报导后,光绪三年(1877年)连续2次上疏朝廷,阐述吸鸦片的危害及禁鸦片的具体措施;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他坚持《万国公约》准则,有力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为加强中国对世界的交流与了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此,当时《西国近事汇编》载他“……不失汉宫威仪,不愧‘国使’两字”。慈禧太后也说:“郭嵩焘是个好政事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光绪政要》(卷十七)载:“郭嵩焘在西洋三年,考究利病,知无不言,其品望最为西人敬服。”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卸任回国,托病径回故乡。船抵长沙时,然自巡抚以下,均对他冷漠无礼,无人邀迎。此后,郭嵩焘愤然退出官场,在长沙城南书院专事讲学、著述,度过晚年。然他忧国忧民之心不减,归隐后仍向朝廷提出了驳斥《里瓦几亚条约》、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伊犁争端和对法战争的主张。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六月,郭嵩焘病逝于长沙。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礼记质疑》、《大学中庸质疑》、《订正家礼》、《周易释例》、《毛诗约义》、《绥边征实》、《养知书屋遗集》等。
①金兰:谓友情契合,有深交。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后引伸为结拜兄弟。
郭嵩焘,一位砍树者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至亲好友,与曾还是亲家,但没有曾、左、李三大人物的功勋。郭曾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在学问上颇有心得,但也没有阮元、王闿运、张之洞的学术声望。然而从历史长河看,他的“远见”,远非乾嘉学者、咸同将相可及。所谓远见,指能超越前人之所思,敢挑战传统之权威,能与主流意见相左,指出正确的前程。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以“砍树者”与“爬树者”作比喻。人们习于在大树下纳凉,不仅讨厌“砍树者”多事,甚且谴责妨碍其纳凉。郭嵩焘在他的年代成为具有高度“争议”的人物,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砍树者”。
郭嵩焘的远见使其深刻体会到三千年变局的到来,并提出应变之道,他认识到西方列强有异于古代的夷狄,并无征服中国的意图,可有和平共处的余地。外国以通商牟利为要,中国只有面对已难改变的通商局面,更没有轻启战端、自取其辱的必要。所以他提出“战无了局”的结论。然而鸦片战争以后,接着英法联军之役,中法马江之役,以及于其身后发生的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一再重蹈覆辙,每次战争的结果,贻患一次比一次凶恶。他直白指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战争只会使中国割地赔款,屈辱更深。郭嵩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非天真无知,只是看准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也不想轻启战端,中国正宜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强,所以郭氏战无了局之说,绝非虚言。郭颇能在外交战术上有所掌握,但战略掌握在朝廷之手,无奈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士大夫又多浮嚣不实,无可行的战略。郭有战术而无战略依靠,难有作为。郭在当时守旧的中国,不讳言自家的弊端,因而遭遇到唾骂、讥讽与谴责。他受到极为无理的毁谤,虽感气愤,但并未动摇他的见解。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是寂寞的引路人,要引中国走向世界,却被拒绝,他的远见不容于强大的顽固势力。他个人的挫折,也是晚清中国的挫折。
当时最了解郭嵩焘的人,不是曾国藩,而是曾国荃,“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国荃心目中的贾生,就是郭嵩焘,以郭与受屈于长沙的贾谊相比,说出郭所遭遇的挫折,端因其见识超越时代,且直言不讳,很容易被时人视为用夷变夏,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甚者视他为奸人。当时即使略知洋务的人,亦仅知洋人可畏,而不察与洋人周旋之道。洋务派领袖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在郭嵩焘看来,也仅能考求富强之术,如枪炮船械之类,而昧于本源。他曾有诗云:“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出海浪翻,象征中国面临三千年的变局;一船痴顽,隐讽昧于中外情势的朝野保守派;风急而无计收帆,说明他内心的挫折感;不能独眠,正是他不能默而不言的写照。
郭嵩焘常被视为洋务派,唯洋务派的视野限于船坚炮利的物质文化,而郭则重视西学。他无疑惊羡洋人的武备,但认为只是洋人的末务,其本包括政制、法律,以及学术,尤其是西学,他曾说:“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学问才是根本。他一到伦敦,就参访各种学校,探明学制,认为斯乃西洋人才之所以盛。他知道英国大学之中,以牛津与剑桥最佳。他曾于1877年11月28日,赴牛津大学访问两日,印象极为深刻,体认到“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于此可见郭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所以一切莫急于学。相比之下,中国士子习为虚文,所学唯取科名富贵而已。为了矫虚征实,他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
郭嵩焘办理外交,知道国门已经洞开,事情日繁,与列强交涉日广。国际交涉唯凭条约,但条约几皆由洋人拟定,而地方官不知洋法,遇到事故,每生争议,予洋人要挟的口实。他认识到法律原是双方的,然而列强却以法来束缚中国,使郭益知法律的重要性,所以当他在伦敦,见到伍廷芳,就十分欣赏他懂西洋法律,要揽为己用,惜伍氏不肯屈就而前往美国。他到法国之后,立刻将法国通律寄往总署备用。足见他深知法律的重要性。但他并不一厢情愿认为法律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警觉到西方霸权的蛮横,他曾与英使威妥玛交涉,常受其辱,认识到若不能以其法还诸其身,全无置喙的余地。
郭嵩焘开启出使外国之端,之后驻日、驻美、驻德、驻俄公使相继派遣。郭到任英国后,在伦敦闻悉数十万华民没有法律保障,乃积极设法在华民较多的外埠,建立中国领事馆。不过,华民较多的地方,多是英国的殖民地,设置领事需要殖民地政府的同意,所以郭的构想并不顺利。几经交涉之后,通过当地殷商胡璇泽的协助,仅在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总理衙门于1877年10月31日同意后生效。即使如此,华民实同英民。中国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领事,异常缓慢,到清朝灭亡时,才逐步完成,这已经是郭氏身后20年以后的事了。
中国在十九世纪走向世界充满挫折,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不仅由“一带一路”走向世界,互惠双赢,而且经由上海合作组织,引领世界的走向。郭嵩焘若地下有知,会不会一扫当年的阴霾而笑逐颜开?
出洋内斗
在驻英大使任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员的支持,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于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郭嵩焘作为在首任驻英法公使,对欧洲仔细观察,不抱偏见,许多地方都抓住了关键,他认为在中国儒生一直期盼的“三代之治”在英国实现了,西学与儒教目标多有一致,也是的论。可惜当他想改变国人的偏见时,却被没见过世面的士人们和无知愚民的口水淹没,收效甚微。
洞若观火
郭嵩焘开馆伦敦,驻节英、法,以及驻日、驻美、驻德、驻俄公使的相继派遣,象征清廷已不得不从古老的帝国,走向世界列国之林。
不过清廷虽迈出一步,却心犹未甘,误将前进的一步视为向西方列强的退让,“心态”并不能与“行动”相配合。即使随同郭氏赴英的副使刘锡鸿,也竟认为“今日使臣,即古之质子,权力不足以有为”[1]。
但是郭嵩焘早已有“心理”准备,已经洞悉列国争胜的局面已不可能改变,必须在新格局中求生存、求自强。
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他于鸦片战争期间,即已领教。他默察中外情势,得出“战无了局”的结论。
他认为西方列强对华,主要在谋通商之利,至少一时之间不会鲸吞中国,中国更不可轻启战端以自取辱,而应师彼长技以图自强。作为使臣,明察沟通,正大有可为。
郭氏抵英之后,置身于西欧文明之中,不仅加深了对列国情势的了解,而且积极参与,留心观察,很想探求西方富强之源。
他不懂外语,却无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心理上也无障碍,甚至不讳言泰西文明高于中华。像刘锡鸿之辈虽也置身于西方世界之中,耳濡目染,有时也感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宏伟,但总觉得彼邦虽好,非吾可学或应学,仍然是望门止步的态度。
即使美才如曾纪泽,能通英语,接触西洋文化的条件较郭嵩焘好得多,但到英国后仍谓:
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财货不足,则器皆苦窳,苦窳则巧不如拙。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括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国,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2]
且不论中国上古多机器固无以证实,那种机械的宿命论即难以真正向西方学习。
然而郭嵩焘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是颇为积极的,只恨老大帝国之举步维艰。他本人已走向世界,只是他所代表的古国,不能随他前进而已。
水晶宫之盛
郭嵩焘所目击的伦敦与巴黎,乃当时西方文明的中枢,备集一时之盛。
伦敦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半圆式屋顶,由三十万片玻璃、五千根柱子筑成。宫中展出1851年英国博览会的科技成果,而水晶宫本身就是新科技的一个里程碑。

大清使节被水晶宫吓尿了
郭嵩焘于1877年5月24日,应水晶宫总办之邀,率同黎庶昌、张德彝(德明)等驱车往访,归后记道:
入门皆玻璃为屋,宏敞巨丽,张架为市,环列百余。其前横列甬道,极望不可及。中列乐器堂,可容数万人列坐。左为戏馆,就坐小憩。又绕出其左,为水晶宫正院。巨池中设一塔亭,高可数丈,吸水出其顶。旁为海神环立,所乘若龙,两眼吸水上喷,高约数尺,张口吐水,日夜渀湃。大树环列数十株,水晶宫最胜处也。曲折相接为巨屋,模仿各国形式……[3]
印象至为深刻。是夕,他们在水晶宫外还看了烟火,“见起火五彩,光焰熊熊”[4],尽兴而返。
郭嵩焘兼使法国前往巴黎时,又适逢“炫奇会”,也就是万国博览会。他以头等公使的身份,与法国总统同座,饱览西方科技文明之盛。[5]
郭之身份使他的接触面比一般人既广且深。西方人士也尽力介绍西方文明给这位首任中国公使,希望借他能改变中国人的视听。
举办茶会
郭在西欧,虽无前人的踪迹可循,但他积极参与伦敦、巴黎的社交,略无沮滞。
他经常出席茶会、宴会、舞会、化装舞会,与上层社会各界酬酢,从英国女王、法国总统到英、法两国首相、外相、议员、学者,以及各国公使,来往无忤。
他还在应酬场合晤及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巴西皇帝、波斯国王,以及英国前任首相勒色与格兰斯敦,尤钦佩格兰斯敦的学问和才辩,可知并非泛泛的交谈。[6]
当时西方社交场合,早已是男女同席共舞,虽与中国国情相距甚远,但郭也让夫人梁氏出席英国格非斯夫人的家宴,并拟由梁氏发请帖开茶会,唯经德明力劝而止。[7]可见郭氏诚心要扮演近代公使的角色。
他也仿效西方外交礼俗邀宴外国使节,并举行大型茶会,招待各界来宾。
他于1878年6月19日在伦敦中国使署,邀请了英国外交部各官员,英国社会绅商、学者,以及德、俄、奥、意、丹、荷、葡、土耳其、波斯、日本、海地各国使节,共七百余人。自5月28日即开始筹备,预算是五百英镑(合银一千七百五十两),并于6月2日议定邀请名单。
茶会那天,使署自大门至二层楼收拾陈设妥当,左右分置灯烛与鲜花,中间铺红色地毯,楼梯栏杆覆盖白纱,挂上红穗,并分插玫瑰、芍药和茶花。客厅与饭厅也悬挂鲜花与灯彩。
厅中横设长筵二桌,一桌置茶、酒、咖啡、冰乳、点心;另一桌置热汤、冷荤,以及各种干鲜果。桌上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瓷,光耀夺目。
客厅的对面,鲜花作壁,后面有红衣乐队。饭厅旁边的小间,作为宾客存放外衣之所。楼上第一层客厅两间打通连为一室,铺放红地毯,壁挂灯镜。窗外有鲜花台,搭上五彩冰塔。第二层郭嵩焘住屋五间也装饰得极为华美整洁。
从早晨到晚上,整天悬花结彩,鼓乐喧天。门外还搭了帐篷,雇巡捕六名守护。[8]郭嵩焘谓五百余人,一千四五百金,应是约数,德明经办此事,故其数字应较正确。[9]
中国驻英使馆在郭公使领导之下,刻意经营此一茶会,而且全部西式布置与招待,也可谓开风气之先。茶会开得十分成功,来宾莫不以受邀为幸。[10]
郭公使应酬之繁,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吃不消。但他理解到“宴会酬应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11],应酬非仅消遣娱乐,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工作。
郭氏及其僚属当然也有真正的消遣与娱乐,如游观宫殿花园、观剧看戏、听音乐会、水族馆夜游、参观画廊、欣赏赛马或花会,至于餐馆小酌,更不在话下。[12]
然而即使这些游观,也使他们浸润于近代西方文明之中。因于游观之际,自然目击西欧都市文明之盛,如伦敦的十二层高楼,四万辆马车,以及房舍的坚固、市肆的整洁,足使郭嵩焘感叹西洋物质文明之盛,远胜中国。[13]
检阅水师
西洋物质文明中,最得中国有识之士垂青的是武器与军备。坚船利炮与弓石矢矛,优劣立判。李鸿章就是一意经营军备以图自强,托人采购枪炮、铁甲、水雷等,并派遣留学生到英、德诸国学习军事。
郭嵩焘抵英后,一直与李鸿章保持联系,也为李照顾这一方面的事务。他既关心留学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也经常访问炮厂、船厂,参观赛洋枪会,并亲自升炮以及试演鱼雷大炮,考求西洋兵器和水雷图式,亦登军舰看操。[14]
他曾经跟随英国女王大阅水师,以及陪同法国总统阅兵。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规模之宏伟,当非李鸿章能够想象,在郭嵩焘心目中,自然留下难忘的印象。

郭嵩焘跟英女王谈笑风生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大阅水师,时在1878年的8月13日,地点是英南波斯穆斯(朴次茅斯Portsmouth)海口。郭应英国海军部之邀,率同武生林泰增,以及张德彝、罗稷臣、马格里四员同往。
他们在维多利亚站上火车,沿途“山势绵亘,树木丛密”,行数十里,抵达海口巨镇,“隐隐若城”。镇后有炮台数座。郭与荷兰公使、日本公使、希腊公使,以及外国参赞数人,共登费飞尔座舰。
舰长为一具有三十年经历、曾到过中国的军官,他设席款待各使。中午时刻,驶出江口,两旁有二十六艘铁甲船(Ironelads),以及不同式样的水雷船两只环列。
至江口迎接女王座舰。海军总司令座舰前导,各国公使船、上下院议员与士绅座船,以及机械学校学生船队随行。议员所坐船为一运兵舰,载有千余人。
女王座舰从中道直上,驶出江口,二十六艘兵舰同时鸣炮,官兵一一升立桅端。女王座舰每驶过一船,左右皆升炮送之。驶出数里后再折返江口,各船亦随之而返,最后进船坞上岸。本来舰队还要出大洋操练检阅,因风大而从简。[15]
法国总统麦克马洪(Mac Mahon)于1878年9月15日校阅马步各军。郭嵩焘应法国军部之邀,由马建忠(眉叔)陪同,前往参观。
法国总统约郭使至其帐殿相见,各国公使以及法国各部首长与高级军官俱在。总统帐殿朝南而设,高约九级,铺毡褥,设几,如宫殿式样。右边设二、三等行帐,逶迤而下。校阅各军面向帐殿整队而立,然后经东边沿围场环转向北,行十余里。
马步各军俱设方阵,总统骑马而至,由阿拉伯军一队作前导,二十余骑军官随之。再后则为各国武官,约二百余骑,中国的陈敬如也佩刀骑马相从。
总统由南边出于各军之前,绕东而北,转返帐殿之前,群皆起立并脱帽为礼。此时跟随总统的二十余骑迅速南驰,再北向而立。总统则南面东上立,各国从骑者依次而立,军乐队五十余骑稍偏西北而立。中间形成一甬道,宽六七十丈。
最前马队、炮队、步队依次而立。最后又是马队与炮队。凡马队都以二十骑为一行,以八行或六行为一营。凡炮队以八骑或十骑为一行,连三行用三匹马拖一炮车,又连三行拖一弹药车,每车必载炮车车轮二具,以备损坏时更换。每车两行之后,有炮兵一队随之。
步兵队则以五十人为一行,两行相连为一队,八队为一营。马队中又有救护车,连两行用马二匹拖一车,车大,有围,可载运伤兵。步队中有各类工兵,各按队伍前进,毫无喧嚣之声。
最后的马队、炮队连为一长蛇阵,奔腾踏蹴,尘埃飞扬。
受阅者共计五万多人。所有军官都有骑马,步兵的队长也骑马。总统在阅兵台上看到诸官兵即免冠为礼。官兵中执旗者,经过总统之前时则垂旗敬礼,总统答礼。
阅后马队千万骑仍北向而立,号声三响,万马奔向帐殿,距总统前约十丈许始勒马而立,统领数骑趋总统之前致敬而后折返大队。于是各军向左右撤离,总统也驰马离去,众骑随之。[16]
郭嵩焘详记这两次随同阅兵的经过,可见他观察之细微,以及印象之深刻。
他目击到了当时世界上最精壮强大的海军与陆军,对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当然心中有数。李鸿章亦一再嘱咐留意西方的武备,曾寄郭长函托购铁甲船、水雷、马提尼枪支等等,以备海防之需。
郭曾亲眼见到英国海军中最新、最先进的铁甲船,十分雄伟,并加详细描述:
“其样式与各船异:前后两旁中通间道,上有飞桥,通船一副机器,两炮台左右犄角为铁房,回环周转,炮二尊随以转动。房壁铁厚二尺,多为铁叶障其外,以御炮弹。船宽八丈二尺,长三十六丈。入水四丈,重一万三千吨,载八十吨大炮四尊。”[17]
留心制度
郭嵩焘虽惊羡西洋的武备,但他认为李鸿章积极购买兵器,派学生学习西方利器,“徒能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也”[18]。
什么才是本呢?他由西洋军队与军火的背后,更深一层看到西洋的政制、法律,以及学术。
郭嵩焘一到伦敦,就留心观察西洋的制度,亲自赴议院旁听,从中理解到两党政治的意义与长处,有谓“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因而剂之以平”[19],亦就是两党政治能够达到制衡的效果。
他亦亲自前往参观英国的监狱,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又远远超过在香港所见。
他的感觉是,西方人不轻易用刑。并注意到狱政,至于在监狱中一切工作,都由犯人们自己为之,令他尤有新奇之感,不免感叹:
“观其区处犯人,仁至义尽,勤施不倦,而议政院犹时寻思其得失,有所规正。此其规模气象,固宏远矣。”[20]
英国的财经制度,也获郭氏的注意。曾往观皇家制币厂(Royal Mint),细察制币的经过,极为严格,“稍有轻重,皆废而不用”,感其“精益求精如此”[21]。
也曾往观内地税务署(Inland Revenue)印造信票(以传递书信)、税票(以完税),以及存款票(票本)。[22]还去参观了英国银行(Bank of England)与英国税务局(England Revenue),对其运作,考求至细。[23]
也注意到西洋的专利之制,认识到西洋以营造为本业,“出一新式机器,得一营造方法,及所著书立说,则使独享其利,他人不得仿效窃取之”[24]。而西洋制造大都委之于民,官府征其税,实为国家生财之道。[25]
他已颇全面地接触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

郭嵩焘观察入微,见解卓越
郭嵩焘对西洋学校制度也一意考究。访问参观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探明其学制、学科、学分,知西洋人才之所以盛。
他知道英国大学之中,以牛津与剑桥最胜。1877年11月28日,曾应里格(理雅格James Legge)之邀,赴牛津访问二日,印象深刻。
是日,他乘汽车经类丁(雷丁Reading)到达牛津城,住入兰多甫(Randolph)客邸。得知牛津大学有二十一个学馆,住读生共二千零九十一人。每生都有卧房、书房,二房相连,极为精洁。选择天文、地理、数学、律法,以及科学各门,必先经考试合格才得录取,各科有专师督导,大约十多人一导师。
又对大学行政制度,如校长(Chancellor)为名誉性质,副校长(Vice Chancellor)乃实际校长等,询问得很清楚,并一一记入日记。
他于28日下午二时,赴纽科里治(新学院New College)。由副校长苏爱尔(Sewel)接待,二十几位学正(院长)与教师来见。
同日还访问了马克得林(莫德林Magdalen)学院——初创于1458年,故郭谓“学馆建立三百年”——学院正楼柱上有石雕人像,“形状诡异”;
阿勒苏尔士(万灵All Souls)学院,有一大藏书楼,曾与图书馆总管(馆长)谈佛经。
至克来斯觉尔治(基督教堂Christ Church)学院,参观其教堂和厨房。
又走访波里安(贝利奥尔Balliol)学院,此院藏书五十余万册,当时名列第三(仅次于巴黎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其中各国图书分藏,中国书亦别藏一处。阅览室为一圆屋,上下两层皆由石块建成,列有数十橱藏书。圆屋最上一层可以远眺,牛津一城皆在郭氏眼中。
之后,他又赴舍尔多里安剧场(Sheldonian Theatre)听里格讲康熙圣谕十六条,郭坐于上席,讲者特先致欢迎中国钦差之意,听讲者男女共三百人,寂静肃穆,但听至佳处,则鼓掌唱喏。晚上,郭出席里格的茶会,再与学院人士见面。
翌日,里格又陪同郭嵩焘前往波里安(贝利奥尔Balliol)学院观看考试及格学生受冠服,以及未试学生口试与笔试。考试有三级:学士、硕士、博士。郭氏视博士如翰林,必经三年始得考翰林。博士亦重前三名,郭氏比诸鼎甲。
不过,与翰林不同的是,所有考生,仅限于牛津学生,外人不得参与。毕业生或留任教师,或出仕,或终其身以所学自效。
郭氏见此,不免感叹:“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中午时郭与副校长午膳,饭后参观出版社,然后访阿阿客难德博物馆(艾希莫林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见金石、鸟兽、虫鱼各部。次至天文台(Observatory),台长为著名天文学家,殷勤接待介绍,并观察金星。下午六点钟,驱车返回伦敦。[26]
郭氏日记中邀其访牛津大学的里格即理雅格,苏格兰传教士,曾在华传教,王韬曾助其翻译儒家经典。
郭嵩焘盛称英国学制,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实由衷赞美之词。
三代学校遗制去古遥远,难知其详,但三代素为中国士大夫心目中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良法美意竟见诸于英国,他的惊叹可知。
他已认识到,西洋学校制度的完备精当,乃促使西洋人才辈出、西洋学术昌明的最主要原因。
学术为本
学校既为西学之本,而西学乃西洋科技与文明的泉源。
郭嵩焘已洞悉西洋矿电兵艺,莫不有学,故彼邦有格致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船机学堂、枪炮学堂、兵学堂、建造学堂、教习学堂(师范学校)、政治学堂、水师学堂、陆军学堂、军医学堂、女子学堂,不一而足。
而且无论学矿务、船炮、建造,必先入格致算学学堂立下基础,两年之后再视性向分门专习。[27]此即他已认识到的,“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28]!
因而他也尽力考求各种学问,诸如电学、矿学、光学、化学等基本科学,即其所谓的格致算学。
他深知“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后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29]。
他也出席学会,参观博物馆,更探究英国学术的源流。罗丰禄(稷臣)在皇家学院习化学,郭从罗处听到化学的原理与方法,并得知英国讲实用之学实肇自培根。
培根卒于1626年,二十年后英人始追求培根之学,创立学会,英皇查理二世尤崇信其学,加敕名于其学会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他亦听说天文学家伽利略,有地动新说;与伽利略同时还有英人牛顿,也穷天文窍奥。
郭氏认为二百余年来“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30]。
他不仅注意科学与实用之学,认识到西洋机器出鬼入神都有学问之本,而且也能欣赏西方经济学、哲学以及文学。
他从日本公使处得知亚当·斯密与约翰·穆勒,认为“所言经国事宜,多可听者”[31]。他于参加卡克斯顿纪念会(Caxton Celebration)时,得知莎士比亚为英国最有名的剧作家,与古希腊诗人荷马齐名。
郭嵩焘置身于西欧文明中,独具慧眼,窥得近代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他渴望理解西学,求知欲极强,只恨不通西文,仅赖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的译介,意犹未尽之情,呼之欲出。[32]
但此时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对西学及其重要性的理解,已远远超过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自强运动健将。
他于光绪四年十月(1878年11月)间致沈葆桢函中,所谓“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绝非一时兴会之言。
比观中外,他早已发现中国士子“习为虚文以取科名富贵,即学之事毕矣”,而泰西则“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
为了矫虚征实,他建议先在通商口岸开设西式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行之有效,渐次推广至各省以达县乡,以广益学校之制”[33]。一切莫急于学,正是他观察泰西的最主要心得。
法治文明
他也能理解到,如果西学乃西洋文明的动力,其文明程序的维持则有赖于法治。
郭嵩焘明确掌握到英国政治之善在于法治,而法治经由教化,浸淫人心,成为一种风俗习惯,故能行之不悖。若谓:
国家(英国)设立科条,尤务禁欺去伪。自幼受学,即以此立之程,使践履一归诚实,而又严为刑禁,语言文字一有诈伪,皆以法治之,虽贵不贷。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深矣。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34]
西洋治民以法,治民者亦不外于法,即张德彝所理解的“英主不尊,律例为尊”[35]。英主非不尊,而实是律法较君主更尊,一均按照法办。
国与国之间则有公法,也是办事的准则。郭嵩焘在出洋之前,已感觉到可与洋人讲理,而讲理的依据即在于法。他到英国之后,实际经验更使他深信法之重要。与英国外交部交涉,亦唯有据法力争,别无依傍。
如镇江趸船一案,商民肆意抗拒,久不能决,即因中国方面没有通商章程可据。郭氏致总署第七信,署六月初十日(未刊)。
自鸦片战争以来,通商口岸渐开,交涉日广,事情日繁,国际交涉唯凭条约。但条约均由洋人拟定,而中国法律与西洋各国相距太远,地方官也不知晓西洋律法,以至遇到事故,徒生争议,并让洋人据为口实,作为要挟,甚至连条约内订定的权利,也一并失之。
法原是双方的,然而外国却以法来束缚中国,“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36],故他力请纂成“通商则例”,以应付不得不改变的通商之局。
他在奏疏中要求朝廷,“明定章程,廓然示以大公,不独以释各国之猜疑,亦且使各口地方官晓然于朝廷用法持平,明慎公恕,遇事有所率循,庶不致以周章顾虑,滋生事端”[37]。
如果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参核各国所定通商律法,分别条款,纂辑《通商则例》一书”,审定之后,颁发各省,颁送各国驻京公使,共资信守,庶几办理各方面的洋案,都“有所依据,免致遇事张皇,推宕留难,多生枝节”[38]。
他于致总署第九封信中,再度强调:
窃以为与洋人交涉,万不能意揣求合也,必应参核西律,纂辑《通商则例》一书,以使有所依循。光绪三年七月初十日函(未刊)。
足见郭嵩焘深知法律的用处及其重要性。他到伦敦后,闻悉流寓外国的数十万华民没有法律保障,乃积极设法在华民较多的外埠,建立中国领事馆。他在奏片中说得很明白:
窃揆所以设立领事之义,约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远如秘鲁、古巴之招工,近如南洋、日国所辖之吕宋,荷兰所辖之婆罗洲、噶罗巴、苏门答腊,本无定立章程,其政又近于苛虐,商民间有屈抑,常苦无所控诉。是以各处民商闻有遣派公使之信,延首跂望,深盼得一领事,与之维持。揆之民情,实所心愿,此一端也。一曰弹压稽查,如日本之横滨、大阪各口,中国流寓民商,本出有户口年貌等费,改归中国派员办理,事理更顺。美国之金山、英国之南洋各埠头,接待中国人民,视同一例。美国则盼中国自行管辖,英国则务使中国人民归其管辖,用心稍异,而相待一皆从优。领事照约稍联中国之谊,稽查弹压,别无繁难,准之事势,亦所易为。此一端也。[39]
设置领事,固然于法有据,但华民较多的地方,多系英国的殖民地,非得殖民地政府同意不可。郭氏的想法并不太顺利,几经交涉仅设立了新加坡领事馆,主要还是因为领事人选胡璇泽为当地的殷商,虽系华裔,实同英民。总理衙门也欣然同意,于1877年10月31日生效。[40]
然而中国向世界其他各地派遣领事,速度仍异常缓慢,到清朝将灭亡时,才逐步完成,已是郭氏身后二十年后的事了。

郭嵩焘对世界的认知远在李鸿章之上
由于知道法律的重要性,郭嵩焘一到伦敦,见到懂西洋法律的伍廷芳,就十分欣赏,欲揽为己用,惜伍氏觉得官小职微,不肯屈就而往美国。[41]
他注意到印度人专程来伦敦学习法律,十分留心《万国公法》,曾与日本公使畅谈。到法国后即将《法国通律》寄往总署,关心马建忠(眉叔)在巴黎政治学堂专习公法,并详细询问其学习情况。[42]
郭氏虽然明白法律乃西洋文明中的重要支柱,以及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要了解西洋律法,制定中国自己的法律,但他并未一厢情愿,天真地认为法律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
他在叹赏近代西洋文明富丽堂皇之余,未尝没有警觉到霸权与蛮横。事实上,他与英国外交部的一再交涉,特别是与威妥玛的争论,可说是身受其霸、其蛮。如果不能以其法还诸其身,根本无置喙的余地。
19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秩序,大致靠经济上的自由贸易与政治上的霸权均衡来维持。[43]
关于前者,郭氏在出国之前即已洞察,通商已成定局,只有面对,无法逃避。至于后者,他到英国之后,日渐明朗,于注视俄土战争的发展时,看到英国防俄的策略。
他亦正确观察到欧洲列强的情势,英、法最富强,德国蒸蒸日上,俄国不如西欧。他还注意到1878年6月,英、俄、奥匈帝国、意大利,以及德国诸列强争权夺利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44]
他更知道,面临列强与通商的新世界,中国必须改弦更张,以求自立,如果“中国甘心受役而不自为计”,那么真正是无可奈何了。[45]
今人凭后知之明的历史知识,可知郭嵩焘对他所置身的西方世界,看得甚是清楚,理解也大致正确,亦因而使他更能看清当时中国问题之所在。
胡刺史招饮东园
清 郭嵩焘
时事艰危国论深,壮心低就酒杯斟。
西风鼓角孤城远,细雨荼蘼小苑阴。
大邑名贤心洒落,清春雅集夜萧森。
何缘料理平生事,一卧沧江鬓发侵。
[1]见李鸿章,《译署函稿》,卷八,页6。
[2]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册五,页2111。
[3]《郭嵩焘日记》,册三,页211—212。
[4]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401—402。
[5]《郭嵩焘日记》,册三,页484。
[6]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53、156、159、161、166、223、230、235、237、238、250、255、260—261、410、418、442、446、505—506。
[7]同上,册三,页263—264;《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页760;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560。
[8]此据德明之记述,详阅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560—561、567—568。
[9]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547。
[10]见《郭嵩焘日记》,册三,页547。
[11]同上,册三,页611。
[12]参阅同上,册三,页153、170—171、174—175、196、205、244、280—281、383、409、494、535。
[13]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305、451、561、563、579—580、676—705;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401、453、531。
[14]参阅同上,册三,页151、185—188、198—199、250、253、259、263、265—266、279、326、495、575、714—715;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324、331。
[15]据《郭嵩焘日记》,册三,页601—602。
[16]据《郭嵩焘日记》,册三,页629—631所述。
[17]《郭嵩焘日记》,册三,页601—602。
[18]同上,册三,页647;参阅页455—457;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九,页6、31。
[19]同上,册三,页389;参阅页104。
[20]《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77;参阅页175—177。
[21]同上,册三,页167—168;参阅页432。
[22]同上,册三,页194。
[23]同上,册三,页168、205—206。
[24]同上,册三,页628。
[25]同上,册三,页462。
[26]郭氏牛津之行详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343、348—353;《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页705。
[27]《郭嵩焘日记》,册三,页523—524;另参阅页190—193。
[28]语见同上,册三,页211。
[29]同上,册三,页518;参阅页172—173、182、204、221—222、323—324、431、454、570—571、673。
[30]同上,册三,页268、356。
[31]同上,册三,页169、267。
[32]见《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69、267。
[33]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一,页13。
[34]《郭嵩焘日记》,册三,页393—394。
[35]见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页384。
[36]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548;另参阅页538、691。
[37]《郭嵩焘奏稿》,页382。
[38]同上,页383;参阅郭致总署第七信。
[39]《郭嵩焘奏稿》,页384—385。郭氏对旧金山、澳洲(新金山)、古巴等地华民、华工之关心,可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60、509、566、599—600;郭与日本公使谈领事之重要,见页338。
[40]参阅Wong,A New Profile in Sino-Western Diplomacy,pp209—219。
[41]《郭嵩焘日记》,册三,页98、148;另参阅《郭嵩焘先生年谱》,下册,页576、579;张德彝,《随使日记》,页332。
[42]《郭嵩焘日记》,册三,页227、289—290、385、489—490、518—519、610。
[43]参阅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pxx。
[44]参阅《郭嵩焘日记》,册三,页170、383、466—469、489、649、701。
[45]同上,册三,页511。
本文节选自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来源:文史宴、文/汪荣祖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其中一项就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这里讨论的张国焘的错误主要是指1935年张国焘另立“中央”的...
-

伏路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这句话提到的两个人有多厉害?
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句话,叫“伏路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这里面提到的子敬和周郎又分别是谁,究竟有... -
 公元前338年,秦国大臣上奏秦惠文王,称商鞅有造反的嫌疑。商鞅无力自辩,干脆逃到边境想要出国。天色已晚,他被追兵穷追不舍,想要在客舍里暂住一晚,却被客舍主人拦了出来。...
公元前338年,秦国大臣上奏秦惠文王,称商鞅有造反的嫌疑。商鞅无力自辩,干脆逃到边境想要出国。天色已晚,他被追兵穷追不舍,想要在客舍里暂住一晚,却被客舍主人拦了出来。... - 前话:严格的说,孙坚不能算是三国人物(当然,把他作为三国人物也是很有理由的),不过由于他被其子孙权尊为始祖武烈皇帝,所以,吴国的历...
-
 文 = 鹿野马航MH370事件过去了整整十年。谁策划的?动机是什么?飞机在什么地方?至今,这些关键问题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最新消息,美国海底勘探公司“海洋无限”正在重...
文 = 鹿野马航MH370事件过去了整整十年。谁策划的?动机是什么?飞机在什么地方?至今,这些关键问题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最新消息,美国海底勘探公司“海洋无限”正在重... -
 共济会不是光明会。共济会早,光明会晚。但现在共济会的灵魂在光明会。共济会是中世纪时欧洲知识分子建立的组织,目的是有技术的专业人士便于联络交流,以为教会建教堂提供更...
共济会不是光明会。共济会早,光明会晚。但现在共济会的灵魂在光明会。共济会是中世纪时欧洲知识分子建立的组织,目的是有技术的专业人士便于联络交流,以为教会建教堂提供更... - 上关于林彪事件的学术史研究,学界同仁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近年来,海内外专题性的综述文章已有多篇[1],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资料不全,有的识力短绌,有的观点偏狭,较为全...
-
李鸿章签《辛丑条约》时,为何不签名字,只“画”了一个古怪的字符
《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法、德、意、日、奥、比、西、荷十一国外... -
 来源:大河报博览武汉,又称“江城”,有着3500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隔江鼎立。然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为了达到对中国实...
来源:大河报博览武汉,又称“江城”,有着3500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三镇武昌、汉口和汉阳隔江鼎立。然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为了达到对中国实... -
 原标题:“折腾”了10年,那个辞职去看世界的女教师,最终还是打脸了?十年前,顾少强写了一封离职信,里面的内容超简短,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没想到这让她一下...
原标题:“折腾”了10年,那个辞职去看世界的女教师,最终还是打脸了?十年前,顾少强写了一封离职信,里面的内容超简短,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没想到这让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