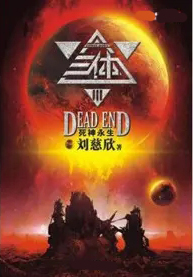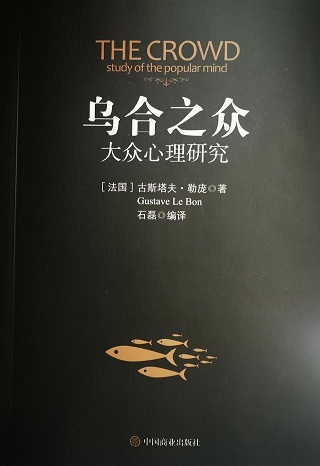乡里人事
文/舒维秀
乡下人纯朴善良,小时听来,至今不忘的几则小事,除了印证乡民的着实纯朴憨厚,细思更引起诸多联想……
(一)陪客
湘西侗家居住在大山上大山脚,过去年代,由于交通不便,人们往来大多走的花阶路,过的木板桥,去走一趟人家,得下好大的决心起好久的意,才能动身。哪家屋里来了客人,满寨子都晓得。真的是稀客贵客,千条路远,走累老火了,客人刚近屋边,主人家听得狗叫声,热情地迎出门来。侗乡人走人家,一般都要带些礼信(礼物),有粑、有糖、有肉,或者是当季瓜果蔬菜,主人家边接客人手里递过来的礼信,边客气地说,“人来了就行,还客气带礼做什么哟”。“没什么东西带,几个菜粑而已,送娃崽家尝鲜”,客人也会根据带来的礼信,顺口回答。
如是天冷季节,把客人请进木屋,上火铺坐好,主人家打来一盆热水,说客走累了,先抹个脸。然后办饭菜招待客人。视客人尊贵程度,办的饭菜丰俭也不同,有杀鸡宰鸭的、有煮块腊肉的、有炒碗新鲜猪肉的,但酒却一律要上,不管菜的丰俭。
过去年代,侗家的酒多是自煮自烤的米酒,也有苕酒、洋芋酒、高粱酒、包谷酒,甚至有南瓜拌米烤的南瓜酒。也有酿而不烤的泡酒。泡酒可以直接筛杯入口,而烤的酒则需酒罐煨开为好,加入红糖,把甲醛烧开走,趁温而喝,口味正好。遇上好饮的客人,主人家如也好饮,就棋逢对手了,如主人家酒量浅,则陪客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主人不吃客不饮,这是客人嘴边常念叨的一句话。
我伙计今天怕又老火了,来了几个客,个个都吃得酒。这天早饭后,二黄听说有客要来屋,他赶忙背了柴刀,和几个寨里人上山砍柴去了,把陪客的“苦差事”留给了伙计(兄长)。他们几个砍柴人走出四五里地,砍得担杂柴挑回来时,只听屋里猜拳声闹热哄哄,二黄放下柴担,用衣袖擦把汗,嘴巴头嘀咕着。二黄从小脑子不灵泛,只会做些砍柴割刀放牛看羊等直活路,而且吃不得酒,酒苦死了,他经常这么评价酒。他哥大黄却头脑聪明,能说会道,酒量好,陪客的事非他莫属。
你是叫花子可怜官哦,你伙计老火,他吃酒吃肉老火,你爬山砍柴,汗水爬纱,你没老火。一同砍柴的人,放下柴担,边歇气边数落二黄。我是宁肯砍挑柴,也不陪客吃餐酒,二黄坚持自己的观点。
自己不擅长,做不得,不喜欢的事,就认为别人也不擅长,做不了,也不喜欢,这是二黄的思维逻辑,也是山寨数十年来摆他门子(讲他故事)的原因。
此后山寨再也没有听到类似的故事了。当然,为了保养身体,不陪客吃酒,却选择砍柴劳动锻炼,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二)抬猪
这也是一个发生在多年前的故事。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侗寨群众按自然居住远近,划入一个个生产小队,由队长统一安排农活,栽秧栽苕,积肥伐木,看牛喂猪,打谷秋收等,大家一同出工一同收工,积极性不是蛮高,出工像条虫,收工像条龙,说的是出工时慢慢去,收工时火急火燎回,去忙自己的家务活。生产队畜牧场喂有猪,每年向公社食品站交一定头数的预购猪后,剩下的猪,喂大起,逢年节时,就杀了分吃。杀猪这天,我们一伙小孩子从捉猪看起,一直看到把猪肉砍成块,一字摆放在稻草上,编好顺序,生产队有几户人家就摆几块肉,凭肉眼进行肥瘦、骨头多少的搭配,各家按拈阄顺序确定拿哪块肉,记得那时分肉是按三等重量分的,按家庭人口多少,相对划分为三个等级。有年元旦节猪杀得晚,在电灯下分的肉,等我们分得肉回屋时,公和婆早煮好了饭,之前出屋门口问了两三回,还没分完肉?
除生产队有上交预购猪任务外,各家各户也有任务,根据家庭人口多少而定,一般家庭一年交一头,七八人的家庭,记得任务是两头。除了预购猪,就是年猪,喂起来也难,在生产队大集体时,要出集体工,而且自留地面积有限,上山上土下田打野菜喂猪是常事。
那时从寨子去公社食品站,没通公路,走的是小路,交预购猪,一般是三个人用猪架子抬去,两人抬,一人轮换。猪架子用两根长条杉树棒,在杉树棒两头各用竹篾条捆好一短截横担,在前后两根横担之间,用粽绳套扎成网状,猪就四脚朝天塞在网里,上捆索子,抬出寨时,猪还叫喊连天的,渐行渐远时,几乎就只听见哼哼声了。
有年热天,坡背寨子刘家交预购猪,早上三人浩荡抬去,下午回来时,只见两人抬着空猪架子,脚步沉重,翻那大坳时,两人还放下架子歇气。正砍柴路过的几个人,看见有人睡在架子网里,急忙问,他得什么病了,你们抬他转来。那两人气喘吁吁,说,我们三人打赌,哪个愿意当猪,另两个就抬他转来,他愿当猪,我们就抬了。
他是猪?我看你们两个抬人的才是猪哦。砍柴人纷纷嘲笑他俩。他俩似乎醒过味来,一掀猪架子,把那人翻下地来,气气地说,各走回去,不抬了。
多年后想想这事,也委实好笑,那自愿当“猪”者,虽一时名声上貌似吃了亏,却赚到了一趟免费滑竿之旅。而那两个抬“猪”者,虽心里获得一丝“他是猪”的虚幻快感,却付出了一路的脚力和汗水。
(三)少秤
还是在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大队,有一所小学,有一个简易加工厂,打大米,擀面条那种,有一个大队办公地点,还有一个代销点,这些构成了大队部的物质存在。每到上学季节,大队部比平时热闹得多,学生娃崽进进出出,吵吵闹闹,挂在小学木柱上的那块铁做成的钟,敲出的上课下课铃声,成了附近劳作群众的时间钟。一到寒暑假或星期天不上学,大队部就冷清下来。
但代销点却一年四季都不显冷清。买盐的,那时没买油的,农家都是年头吃年猪油,年中吃自种油菜籽榨出的菜油,买火柴的,那时还不时兴卖打火机,火柴是本地区洪江市生产的洪江火柴,买糖果的,大队部所在生产队,有两弟兄,父母死得早,成了孤儿,哥哥有时没煮饭,就去代销点买点糖果给弟弟吃,当餐饭,买煤油的,那时村里还没通电,晚上屋里照明除了枞膏就是点煤油灯,买酒的,那酒讲不清是自烤的米酒还是县酒厂出的酒,有年我和父亲去山上采摘麻栎籽,卖公社供销社,说是县酒厂收去做酒,过后不久,供销社有这种麻栎酒卖了,父亲吃后说酒苦,假口(方言,有涩味),那时农户家里吃饭都缺米粮,极少烤酒,有人客来,就去代销点打半斤一斤散酒,还可买学生铅笔,作业本以及其他一些日用货品。
代销点也收购山品,如粽皮,构皮,辣扣(麦冬),三步跳(半夏),茯苓,山楂等,我在大队小学读书时,还收购鲜金银花。开春后,路边田土坎边的金银花开了,这一蓬那一蓬的,我用早晚上学前后的时间,逐蓬去打那些开得正白的金银花,一朵两朵三朵,塞满两个小小的裤子口袋,又塞满稍大点的两个衣服口袋,压紧压实,有时早上露水大,金银花上的水把口袋都浸湿了。回到代销点,小心把金银花从袋中取出放入秤盘中,一称,三两,可卖六分钱,刚好可买一支铅笔。那些年那个季节,我读书的铅笔就是这么买的。
代销点的管理员开始是我们家族的亲戚,老场生产队的杨,他后来发生意外生病了,改由另一生产队的吴,再后来又由老场队的姚来管理代销点。少秤的故事发生在他身上。“你搞什么,称得这么Lia(读平声,指秤杆尾巴低低的)”,某天,一群众来称盐,见状质问姚,姚说,“刚才有个人也来称盐,称得旺(指秤杆尾巴高高的)了,你这盐称Lia点,店里刚好持平”。买盐人哭笑不得,“你店里是持平了哩,我就吃亏啦”。现在想来也是,自己的失误,怎么能要另一个人来买单呢。

舒维秀,侗族,湖南新晃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新晃侗族自治县审计局。作品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民族文学》等报刊和中国作家网等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