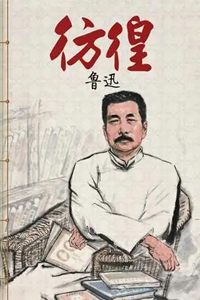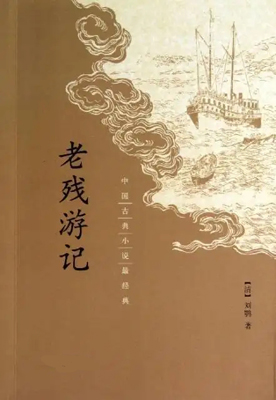文|王国梁
读到梭罗的句子:“我宁愿独自坐在一只南瓜上,而不愿拥挤地坐在天鹅绒坐垫上。”我不禁微笑起来,想起幼时与南瓜亲近的时光。
记得那时候,父亲特别喜欢把秋天收获的南瓜摆在窗台上,排满一排,既展示着丰收的喜庆,也是一种漂亮的装饰。金黄的南瓜,仿佛给农家小院镶上一道金边,让院子亮堂起来。我印象中,那些南瓜很长时间才吃得完,所以每每回忆起往事,脑海中总浮现出那个亲切的南瓜小院。

我放学后,坐在院子里的咸菜缸前写作业。写累了,我便跑到屋檐下,与那些南瓜嬉戏。我盘腿坐在一只大南瓜上,学着电影里老和尚念经的样子,闭着眼睛打坐,口中念念有词。那只南瓜大小合适,坐上去感觉很舒服。坐累了,再换另一只南瓜。有时我会躺在一排南瓜上,枕着自己的胳膊,跷着二郎腿,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南瓜。还有一次,我模仿起武打片中的镜头,像练梅花桩一样在南瓜上面走来走去,正摇摇摆摆地走着,父亲回家了,大喝一声:“干啥呢?”我一跃跳下南瓜,做个鬼脸说:“我练功呢!”父亲见我像个顽猴,没绷住笑。
在我眼里,南瓜作为食物的功能被忽略了,完全没有了功利性的利用价值,单纯就是一只只南瓜,是我的亲密伙伴。它们有时充当我的座椅,有时充当我的玩具,我与它们亲密无间,就像相伴成长的发小一样。我亲眼看着一只南瓜如何长成硕大无比的模样,它生长在园子里的日日夜夜,我都是见证者。它的脾性,我最了解。亲近一只南瓜,渐渐地,人也就有了南瓜的脾性:本色自然,淳朴敦厚,一身磊落,满腹清气。
其实不仅是南瓜,乡间的那些草木瓜果都是我们亲近的对象。你在一棵树上打过盹儿吗?记得那次我爬到一棵老树上,那些粗大的枝杈坐上去像椅子一样。开始的时候,我在上面威风八面地大呼小叫。等树下的小伙伴都走了之后,我靠在树枝上悠然地吹着口哨。不知不觉间,困意袭来,我竟然打起了盹儿。忽然,我的身子“忽悠”一下,差点摔下去。我惊醒了,往下一望,吓了一身冷汗出来。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她立即双手合十:“老树通灵,多谢保佑!”从那时起,我便觉得乡间的很多东西都是有灵性的。它们生在天地之间,吸纳天地精华,自带灵性。我曾经躺在麦草垛上数星星,在瓜园里看月亮,在草地上撒欢,在田野里狂奔,在苹果园里做梦……我曾经亲手种下一棵小桃树,曾经亲手撒下一粒粒种子,曾经亲手拔掉一棵棵杂草……那些身在天地之间、经常与草木亲近的日子,无忧无虑,快乐自由。人也像一株植物,恣意生长,畅快呼吸,身心都是清雅芬芳的。
可是,这些年里,我离自然越来越远,远得忘了亲近一只南瓜。南瓜也常见,但它唯一的功能是作为食物。我忘记了南瓜是那么有趣的伙伴,也丢失了南瓜带给我的淳朴自然。我的心变得麻木、生硬、冷漠,功利,长此以往,我将成为一台行走的机器,缺乏温度和温情。
是该亲近一只南瓜了,让一只南瓜把久违的自然之气带回来。蓝天厚土,阳光雨露,清风流云,一颗心只有回到自然之境,才会重新变得柔软。就像梭罗,隐居期间他与森林、湖水、月光、鸟鸣为伴,他独自坐在一只南瓜上,却是心灵最丰盈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