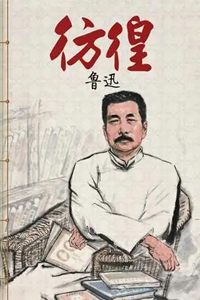下部 肃毒风云
一、芒市纪行
当地政府对海洛因迅速反击的标志之一就是各种规格的戒毒所争相涌现,密度最高的是吸毒最流行的德宏州。
芒市是德宏州的首府,也是我们采访的首选目标。
然而进芒市难,进芒市采访肃毒更难。
尽管在上海时我们即办妥了很过硬的边境通行证,但我们被告知:肃毒,是由缉毒和戒毒两大部分组成的保密性极强的工作,采访戒毒所须经过当地专门机关的批准或政府特殊部门的“担保”。
因为是外地记者,故而我们一开始就被认定“行迹可疑”和“图谋不轨”,谁也不会担保我们。
在五月的昆明,我们被足足风干了三天。
焦虑、虚惊、请愿、交涉甚至耍赖——辗转多人,总算荣幸地得到军界某系统有保留的庇护,获准采访云南西部至今仍蒙着厚帘的形形色色的戒毒所。
汽车尖啸着拖着滚滚的青烟,屁滚尿流地爬过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进入绚丽的滇西亚热带地区。
美丽的芒市浓绿得化不开。
肃毒气氛也浓得发稠。街上到处是通缉令。
毋庸讳言,近年来这座城市已成毒品最大的集散地之一。
十年来到底有多少海洛因通过这个城市转运各地,这问题就像当地有多少人吸毒一样,公安有公安的回答,武警边防有武警边防的回答,海关有海关的回答。。
感谢E少校一个电话。我们即可长驱直入市西北的“德宏自治州康复治疗所”。
这所60年代初的兵营式的建筑原先是座训犬所,如今围墙倾圮、杂草齐膝、下水道废湮,四周连市内到处可见的凤尾竹和大榕树也没一棵,破败得像刚刚经过一次轰炸。
在年轻的L中尉陪同下,我们尽量低调地踱入这块禁地,尽管显得对四周的秘密无动于衷。因为它虽然破败,但还足够森严。
皮肤黝黑的Z所长45岁左右,他坦率地告诉我们:州内4号客实在太多,全部收治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病入膏肓的也多,收治亦失去意义。
因规定只能先限收“吃皇粮”而毒瘾中等的在职职工,该所现押4号客46人。
戒毒所的中央是一块约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宿舍环墙而立。戒毒者一律称学员。
竟然没有床。所有戒毒者都用稻草打地铺。
药品少得可怜。
著名戒毒药品“盐酸美散痛”、“安那度”、“度冷丁”、“复方樟脑酊”、“鸦片酊”等根本看不到,药柜里全是那些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代用品——抗癫痫药“安定”、止咳药“可待因”、“二氢可待因”、“复方甘草棕色合剂”。
我们疑惑的目光和Z所长相遇。后者无奈地摊摊手:“实在没钱。药源也稀少。就是这些止咳药也来之不易,因含少量鸦片酊和其他麻醉成分,病人瘾发时也拿他们充宝。”
“没钱!”他再次摊摊手,“社会上有那么多无聊的赞助活动,就他妈没人赞助我们这项事关民族前途的大事,岂不是头等怪事!人穷心狠,我们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给药的,苦了病人。”
那么学员们用什么方法戒毒呢。
事实上没有什么方法。
所谓“意志戒毒”、“强制戒毒”,那根本不是什么方法,而是一种无奈。
就像死亡,那是一种状态的无奈的结束。所不同的是犯瘾者还得在下一轮犯瘾周期中再“死”一次,无处可遁。
憋急了,犯瘾的4号客便大洗冷水澡,据说能稍稍缓解症状。
按国际禁毒总署制定的戒毒康复标准,戒毒所应提供“令病人心旷神怡的环境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膳食应达到一级全能营养标准。”
环境姑且不追究了。
没钱。Z所长照例摊摊手。不要说黑白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无力购置。
晚上到规定时间熄灯后,学员们只好数星星。
至于膳食,这里的收费标准是每人半年420元,粮票180斤。
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理论上是2元3角。而食堂里倒腾出来的饭菜使人食欲全无。
所长讷讷地说:我们也想补贴他们的营养,但是——没钱。
征得所长同意后,我们直接和在押的学员们交谈。
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最大的年龄不过35岁。吸毒前都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外观黄、瘦、脏、嘴唇发青、喜蹲。
步入他们的宿舍就觉得有点异样,他们的眼睛看到我后,突然放出一种食肉类动物的荧光,令人头皮发麻。一个叫杨炼生的青年杀气腾腾地逼近我,在一眼瞥见我身后10公尺站着同样杀气腾腾“护驾”的武警军官后,这家伙突然弯腰仰头拱手,一个劲地哀求“阿泼”、“阿泼”,手指拼命点我衬衫袋里的外烟,其他学员也纷纷涌上来。在我毫不犹豫地给他一支后,L中尉已闪电般地闪到我身后,用电棒制止了一场“求烟骚乱”。他告诉我,“阿泼”是傣语,意即海洛因。
原来某时髦外烟含鸦片成分。我事后才知道我差点引发一场狱变。
为保证安全,Z所长介绍我们采访了几位女学员,她们的宿舍也稍微干净些。
吸4号的女子几乎都卖淫。
所长让我离她们远一点,并且别坐她们坐过的地方:她们有阴虱,穿裙子却偏偏不穿内裤。
在这群女人中,我注意到一群姐妹花。
姐姐赵晓云(音)18岁。妹妹赵晓虹14岁。前者原系某公司打字员,后者还是个学生,均为景颇族人。
正是最易害臊的年龄。但姐妹俩谈性事如谈女红一样随便。
“我12岁时就被人玩了,”妹妹若无其事地告诉我,“都是4号作的怪,那些臭小子骗我抽的。”
“我开始还臭骂她呢,”姐姐嘻皮笑脸地告诉我,“后来反而被她带过去了……嘻。”
她俩现在拉稀,便中带血。例假已好几个月不来,犯瘾时能吃上昆明中药厂制的“戒烟丸”,待遇显然好于男学员。
像滇西所有的戒毒机构一样,德宏州康复医疗所内也设禁闭室。
一切可能导致病人自残的利器都不能有。连餐具都是塑料的。为这,Z所长到处恳求赞助,但没人理他。人们宁可花上几百万集资去重建那些早已湮没的破寺烂塔或者弄几篇绝妙好辞,重复宣传芒市的那座古里古怪的“树包塔”,也不肯施舍点钱来确保禁闭室内学员的生命安全。
Z所长沮丧得直搓手。
只要有少许资金,他会有信心把戒毒所办得更好,甚至达到国际标准。
他拥有10天就戒断一个学员毒瘾的了不起的经验。
但他不能保证这些学员从此不再进来。
在世界三大毒品(海洛因、可卡因、大麻)中,海洛因以迷幻作用大、“极乐感”强、易成瘾而名列榜首。
它“易戒”。曾有7天就戒断的事例。然而“难忘”。戒断者可以暂时厌恶海洛因,犯瘾现象能稳定地消失,但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你会像念及自己的初恋一样地蓦然念及它并且如蚕抽丝般绵绵不断……
不能不考虑到人的动物性。人的大脑分泌一种内啡肽,那是快乐的源泉,也控制心跳血压和呼吸。一旦吸毒,则麻醉品中的成分“类内啡肽”已进入人体就取代人体原先的内啡肽,换句话说,内啡肽下岗,“毒品”上岗,时间一久,人体内啡肽完全停止分泌,由毒品全面取代,故一旦停止吸毒,人的呼吸、心跳与血压就全面崩溃,就出现强烈的“戒断反应”。
不能不考虑到人对麻醉品的依赖一旦形成,“想瘾”就归化为人体的新的生理机能甚至和性欲食欲一样被人体某些神经丛收编整饬录用。
意志能抑制一种技机能。但要消除一种机能又是谈何容易。
意志可以闪光,但不能永远处于闪光状态。
更何况,百分之八十以上的4号客文化素质低下,有没有意志本来还有待商榷。
据统计,滇中地区的4号客戒断后的复吸率为50%~70%;滇西达80%甚至95%.
这就是说,Z所长们的工作很可能将是著名的“西绪弗斯”式的劳作。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所长将要永远当下去?”Z所长咧开雪白的牙齿笑着问我。
“不。但你这训犬所将被改成永久性建筑。”
我向困惑的Z挥挥手并按他的指点驱车直驰警备更森严的畹町戒毒所。
只能碰碰运气。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2002年莱阳大案,两学生劫杀顶级科学家,改写了整座城的命运
“110吗?东关村水电办公室附近死人了!”2002年3月12日,山东莱阳一名行人下班回家,走到东关村水电办公室附近的一条巷子里的时候,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当时天色已晚,巷子... -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用车需求的改变,汽车经历了多次的升级换代,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以前的汽车设计,既简单又经典,不像现在...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用车需求的改变,汽车经历了多次的升级换代,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以前的汽车设计,既简单又经典,不像现在... -
 虎年春节,你是不是收到一大波俏皮又温暖的祝福语?如果穿越回千年前,你可能收到的吉祥话、祝福语是这样的:" 长乐未央 "" 与华相宜...
虎年春节,你是不是收到一大波俏皮又温暖的祝福语?如果穿越回千年前,你可能收到的吉祥话、祝福语是这样的:" 长乐未央 "" 与华相宜... -
 涠洲岛上藏着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或许我这样说,各位一定心存狐疑。那就不妨看下去,最后一定可以看到答案。我先来介绍一下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最大的海岛,位于北部湾...
涠洲岛上藏着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或许我这样说,各位一定心存狐疑。那就不妨看下去,最后一定可以看到答案。我先来介绍一下涠洲岛。涠洲岛是广西最大的海岛,位于北部湾... -
 重要提示:本页内容不适合24岁以下人士阅读,儿童和女士请勿浏览。最近的官场堪比娱乐场,不仅惊艳,还很俗气。乌烟瘴气之甚,堪称新官场现形记。出事之前,他们有的是“妙龄...
重要提示:本页内容不适合24岁以下人士阅读,儿童和女士请勿浏览。最近的官场堪比娱乐场,不仅惊艳,还很俗气。乌烟瘴气之甚,堪称新官场现形记。出事之前,他们有的是“妙龄... - 你家现在还挂挂历吗?我前几天在一位老人家院子里,看到房子去年(兔年)的挂历,化肥广告。广告没有广告文案,只有简单的化肥照片和地址和联系方式。老人说也没有挂过,要它...
-
 或许,你在古装影视剧中,常常看见这样一个场景。在闹市的街区,小孩、青年、老人,他们三五成群,围在一张桌子前,为几只打斗的小虫子呐喊...
或许,你在古装影视剧中,常常看见这样一个场景。在闹市的街区,小孩、青年、老人,他们三五成群,围在一张桌子前,为几只打斗的小虫子呐喊... -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70周年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见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远东乃至世界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停战协定全称长达45个汉字:《朝鲜人民军最高...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70周年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见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远东乃至世界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停战协定全称长达45个汉字:《朝鲜人民军最高... -
 “祝大家2017年金钱多多!运气好好!身体棒棒!酒量海海!艳遇多多!耶”2016年的最后一天,脑白金、游戏《征途》的缔造者史玉柱在微博上写下了这句话。简单的几组“叠词”,...
“祝大家2017年金钱多多!运气好好!身体棒棒!酒量海海!艳遇多多!耶”2016年的最后一天,脑白金、游戏《征途》的缔造者史玉柱在微博上写下了这句话。简单的几组“叠词”,... -
 史家胡同位于东四南大街东侧,大约是清代末期至民国时期的建筑,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条胡同住过许多知名人物。几百年的老胡同发生的故事数不胜数,历史随着时间一点点淡...
史家胡同位于东四南大街东侧,大约是清代末期至民国时期的建筑,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这条胡同住过许多知名人物。几百年的老胡同发生的故事数不胜数,历史随着时间一点点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