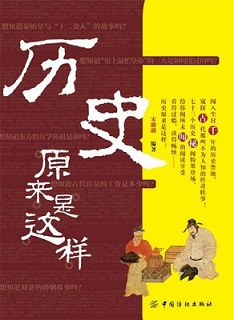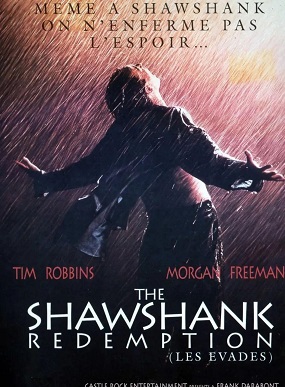宋代削弱地方自主权,财权军权向中央收拢,但中央腐化,则全盘衰弱,面对外敌侵略,连片溃败,先是北方沦陷于金,最后全盘沦于蒙元。
朱元璋设计分封制也是总结历代经验下的制度探索。
见识浅陋者只会用历史人物的专权私欲来解释,却看不见这里面存在一种群体意志,是要寻求一种机制,既能有效抵御外侵,又降低内部战乱冲突,尽可能在疆域广阔的领土上长时间保持和平,连续发展。
朱元璋分封皇子的用意,一方面加强边境蛮族冲突地区的军力,保境安民,又用皇室亲缘关系作为纽带维持住向心力,不至于边镇军阀坐大产生类似安史之乱那样的动乱。
封皇子,并不是让他们去享福,很多是北方荒凉之地,承担军事任务。
秦王在西安 晋王在太原,燕王在北平,辽王在辽东广宁,宁王在大宁,韩王辽东开原,岷王初封甘肃岷州后迁云南,肃王在甘州左卫,周王在开封,代王在大同,齐王在青州,鲁王在兖州。以上十二王在北方。
除了陕西、山西、北平这些在洪武前中期和北元势力交锋的前沿地区,可以看到仅仅在关外辽东一带,朱元璋就安排宁王、辽王、韩王三王坐镇。
如果这些藩王如朱元璋最初设想的那样保持相当大的自主性,维持住军力,那类似明末后金分裂势力是没机会崛起的。
沈王、唐王、安王、伊王、郢王等永乐时就藩的不一一说了,不过除了郢王在湖北安陆外,也都在北方。
洪武时就藩南方原定有四个:潭王在长沙,楚王在武昌,蜀王在成都,湘王在荆州,加上迁到云南的岷王。
这些在南方的藩王也多承担平息蛮族劫掠叛乱的任务。如洪武十八年楚王朱桢与汤和等一起平息铜鼓、思州诸蛮乱。洪武三十年,古州蛮叛,朱元璋让楚王朱桢、湘王朱柏一起出征。
封在成都的蜀王同样需要承担安境任务。“番人入寇,烧黑崖关。椿请于朝,遣都指挥瞿能随凉国公蓝玉出大渡河邀击之。”
“前代两川之乱,皆因内地不逞者钩致为患,有司私市蛮中物,或需索启争端。椿请缯锦香扇之属,从王邸定为常贡,此外悉免宣索。蜀人由此安业,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明史列传第五,诸王二)
朱元璋分封皇子还有一个动机,应该是弥补中央独大一元化体系的弊病。中央出问题,还有藩王加以制衡约束。
任何统治,缺乏竞争,都难免形成积弊,难以革除。实际的明代,中晚期文官清流势力过于膨胀,操控舆论,助长民粹,煽动中下层百姓只重视眼前短期利益,政府从民间征收财税的能力越来越退化,导致丧失足够应变能力。
朱元璋的错误可能是高估了文官系统对藩王分权的容忍度。文官群体对朱元璋设计的分封制度一点耐心,一点时间都不给。朱元璋一死,就怂恿建文帝主动出击,大举废削。这么一来平衡就彻底打破了。
虽然朱棣获胜,但平衡已破,中央和藩王之间的互信被撕毁,只能沿着限削藩王的方向走了下去。藩王军权近于被剥夺干净,政治权利被完全剥夺。本来在辽东的宁王、韩王也都被改到南方限制起来。
如果朱元璋设计的分封体系能持续下去,形成一个持久稳定的制衡,防止如宋朝一样中央积弊衰弱,遇外侵全盘沦陷。这有利于文明进步,不仅仅是中国的进步,对世界的发展都有好处。
把皇子分封完全看成一种维护皇权的私心,是不客观的。
三、杀功臣
许大师说这是“忌刻嗜杀,为了防堵有力者威胁皇权”。”
这都是指责朱元璋的陈词滥调了。
其实朱元璋真自私,真为所谓防止功臣威胁,大可不必杀什么功臣。效仿前代用田地美女让所谓功臣酒醉金迷,腐化堕落就行了,反正倒霉的是平民百姓,又影响不到他。
这对他来说没半点难度,至少威胁不到他自己安享权力。
他自己还可以落一个好名声。以前的朝代都是用这种办法。
可惜朱元璋不愿意。
相反他对功臣群体,三令五申,再三告诫,要他们自律,约束家人,约束手下,不能放纵害民。对比如这段
“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乃召徐达、常遇春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匪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育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我资将臣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岂宜有此?故与尔等言,此辈有横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四月)
洪武四年十二月,“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淩暴乡里,而诸功臣亦不禁戢。上乃召诸勋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小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淩暴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自纵不已,必累尔德也,”(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类似对功臣的直白告诫很多,不胜枚举。
能听他劝,改掉骄奢,约束家人的功臣都是善终的,如徐达、汤和、郭英等人。
那些屡教不改,甚至自作聪明,故意生活奢靡,侵占民产以为可减轻皇帝猜忌的功臣,朱元璋就不手软了。
胡惟庸, 蓝玉案本身这两人确实有谋反的证据,同时有各种骄纵害民的恶行。
许多功臣及其家属牵连在内被处死,确实残酷,指责朱元璋在这些案件中,株连过多,那是可以的。
但把动机仅仅归结成为忌刻嗜杀,还是一种鹦鹉式的条件反射。
四、所谓宦官垄断专利
许倬云说:“在国家专利的生产单位,例如矿、林、烧瓷、织锦和外贸单位,都由宦官直接管理,文武官员无置喙之余地。”
他可能对明代经济史缺乏基本的了解
所谓国家专利的生产单位,明代即便有,那也很少,远少于其他朝代,少于现代,甚至少于欧洲近现代。
宦官即便参与一些生产单位,也受文官的监督,经常被弹劾。
1、矿
吴承明教授说:“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1]
金银矿,在明代私人开采确实需要得到国家批准,否则属于盗采。
但现代也是如此,西方国家也是如此。类似英国之类,金银矿甚至是王室所有。
“英国的大多数金、银矿产的所有权属于王室,这些金属矿山被称作皇家矿山。在英国进行金、银矿的勘查与开采活动,必须先得到皇家矿山许可证”(孔庆友主编,地矿知识大系,第868页)”
明代君臣动辄认为官方开采银矿会加重百姓负担,这在事实上造成大部分银矿一直被民间开采,大多情况下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闹出为争夺利益抢劫杀人才去严格查禁。
前面说过朱元璋时期,有人建议官方开采某处银矿,被朱元璋拒绝。
这种记录在明代其他时期也很多。
“广西河池县民言县有银矿大发,长沙府民言其乡产铜,发民采炼,可获厚利。成祖曰:‘献利以图侥幸者,小人也。国家所重在民,不在于利。’皆斥之。”(皇明典故纪闻 卷七)
“广东南海县民叶发言,番禺县径口地有银矿,民多窃取烹炼,宜开冶置官。宣宗曰:‘今各处岁办银课者,往往害民,方革其弊,岂可再开银冶?’不听。”(皇明典故纪闻 卷十)
后面这种记录也多的是,不一一列举了。
丘浚曾经把宋代、元代和明代的情况做过对比:
“ 宋朝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輙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所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名臣经济录》卷二十四 丘浚 山泽之利)
也即宋代各种矿藏开采处所繁多,都派官吏主管。如开采时间长了,开矿本身收入不及原来数字,政府必定要求主管者把缺额补上。(这只能从矿藏所在地老百姓那里强行征收了)。
丘浚接着说“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数倍。”他慨叹“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十之一二”
丘浚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经过宋元等前代的挖掘,到了明代矿藏都差不多枯竭了。
这是不成立的,按古代的采矿消耗能力,全国可开采矿藏离枯竭远得很。更何况丘浚自己也说了明代民间各处照样很热衷开采银矿,开采团伙经常争斗起乱,为此他忧心忡忡提议要设法禁止。
更何况,就算部分矿藏真的枯竭,明代也完全可以效法宋代,让当地百姓把不足的部分贴补出来。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明代君臣认为开银矿害民,剥削百姓,能不开就不开。万历违反惯例要开矿,要征收矿税,就被骂得狗血喷头。
这是银矿的情况。
至于铁矿之类,朱元璋时期就允许民营。
洪武时期指定十三处官营铁冶所,其他地方任由民间开采。
上篇引用过王允道建议磁州临水镇产铁,可恢复元代设立的官营铁冶,被朱元璋杖责流放,并说“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那此地必然是任由民间自己开采冶炼。
即便是十三个指定的官营铁矿冶炼处,只要产铁满足国家需要数量,朱元璋也下令向民间开放。
洪武二十八年“上以库内储铁已多,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
其他铜矿、煤矿等等在明代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民营,不再一一论述了。
唯一能和许大师所说沾边的或许是万历时期收矿税,然而大部分也是民营,并不是国家专营。多数情况是宦官被派出去收税。文官不仅可以置喙,还把万历本人骂得狗血喷头,另外还煽动民众暴动抵制,打死税使,东林高官李三才甚至故意让死囚攀扯陷害太监手下税官。万历一死,矿税就被停止。
2、林
洪熙元年就有命令各处山场、园林,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明仁宗实录 卷十,洪熙元年正月)
3、烧瓷
这在明代更谈不上国家专利。
“明后期景德镇3000座窑中,官窑仅有几十座。崔、周、陈、吴4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远远超过官窑。这时京郊门头沟煤窑很多,官窑只一两座,余皆民窑。” [2]
“明代民窑比元代大3倍,平均每窑产量约5担。以每年烧40窑计,300座窑年产6万担。明代御瓷的烧造任务,除了隆庆五年(1571)一个引起大臣争议的特例外,最多不超过10万件,合500担左右。其中只是钦限瓷器官搭民烧,我们不知钦限部分占据多少,即以全部官搭民烧计,也只占民窑生产能力的0.8%,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明代民窑的99%的生产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的” [3]
【后续,关于垄断专营里,丝织业部分的分析比较长,单独另立一文。许倬云文中其他错谬后文也会逐一分析,因为他几乎每句话都错,只能分好几篇写了。原定上下两篇就完结是不可能了,标题只能用二三四了】
注释:
【文献出处能简短注明的,就放在正文里括号注明,比较长的才放在文末脚注里】
[1]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175页
[2] 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4期
[3]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578页

许倬云大师的朱元璋一文谬误(三)——明代官营丝织产量和民营相比
四 所谓宦官垄断专利
4、丝织
明代官营织造机构有两京的内外织染局和地方织染局。
内织染局属于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外织染局则为工部织染所,由工部官员管理。
地方织染局隶属地方,采用民间机户领织形式生产。[1]
明代宫廷如果在原定的每年织造任务之外,还要额外增加织造缎匹,指定地方完成这种额外织造任务,这叫坐派,多由皇帝派出宦官监督管理。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把设立包括内织染局的宦官二十四衙门的原因说得很清楚:
“凡内府饮食常用之物,官府上下行移,不免取办于民,多致文繁生弊。故设酒醋面织染等局于内,……,取其不劳民而便于用也。”(皇明祖训 内官条)
也就是为减少扰民才设立直属宫内的生产单位。
内外织染局和地方织染局合起来供应的丝织品都是为供应皇室宫廷和朝廷公用的需要。并不对民间销售。这和国家经营丝织业不是一回事。和唐宋等盐酒茶专卖,国家垄断生产以此获取高额利润更不是一回事。
明代官营织造本质不是什么国家专利的生产单位,和面向全体人口供应销售的民间丝织业相比,其规模必然小得多。
按万历时申时行的奏疏,每年定额织造数目为“累朝定制,岁造缎匹,不过三万余匹,上用赏赐俱在其中。”(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七,万历十五年六月)
至于额外增加的坐派织造数字,各朝不一,一般认为是万历时期最多。
清修《明史》对明代宫廷物资采办的叙述多有任意夸大失实,涉及织造也是如此。
比如万历时期加派数字:“自万历中,频数派造,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明史》食货志六)
按这种叙述,万历时期把额外加派织造数字提升到了一年十五万匹,并延续了下去,每年如此,成为常规。
实则这叙述属于故意造假,误导受众。
修明史的清廷奴才本来也不会列出参考史料,大部分读明史的人也不会去核查。
所谓“岁至十五万匹”,其实只是万历九年分派织造任务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六十四匹。
但这十五万匹并非一年内完成,而是分年完成,多次解运。到万历十四年三月,才完成解运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三匹。五年时间才完成五分之一多点。
申时行要求裁减。万历同意在未完成数额内裁减一万。(《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之十四,石星,执掌事宜疏[2])
至于真正按每年来计算:
“万历一朝前后共加派9次加派量为545530匹平均每年加派多达11365匹实际织造量应该略少于此数。” [3]
也即万历朝总的加派织造量为54万5530匹,平均每年一万多匹。加上本有的定额岁造,也不过是每年四万多匹。实际还达不到。
按照明熹宗时的记录,“浙江、福建、苏、松、常、镇、徽、宁、扬州、广德等府州县自万历四十年已前拖欠岁造缎匹,除已徵收在官及起运在途者照旧解纳外,其余查系小民拖欠,尽数蠲免。”(明熹宗实录 卷四十,天启三年闰十月)
万历时期派发的织造任务,到天启三年都没完成,被明熹宗给蠲免掉了。
这里就按照万历时期平均每年岁造3万匹,坐派1万匹来考虑。
那相当于多少价值的银子呢?
在温纯的文集里有这么一条记录:
“今据该司呈称,查得浙省原奉坐派缎二万五千匹,估工料银一十八万二千六百五十一两四分零,分为十运,每年一运,扣至万历二十年止 ”(温纯《温恭毅集》 卷三 )
按这个计算,坐派的绸缎每匹价值7两三钱银子。
不同用途品类的绸缎价值不一样,按王德万的奏疏,用于婚礼的皇室袍服大约二十两银子一匹。但不可能所有坐派的绸缎都是这个规格。姑且取一下平均,算坐派的绸缎13两银子一匹。
至于定额岁造的缎匹的价格要比指定加派低许多。
万历三年有官员说解运上来的绸缎每匹价值十二两银子,圣旨批复说哪里值这么多。
“奉旨这缎匹以备供用赏赐,必不可缺的。著照前旨陆续解运,本内说纻丝罗每疋该价银十二两,其实解进的都粗糙不堪,不值原价三分之一,且不分轻重一例重估。”(卷四十二,万历三年九月)
不值原价三分之一,那就是四两银子。
供给两京下层官吏所需的缎匹,每匹按例折银3两。[4]
万历那时候才十三岁,应该不懂绸缎价格方面的事情,这个旨意批复必然是出自张居正内阁之手。
皇室指定用途的绸缎不能太过粗劣,只能另外加派织造。这也不是皇帝变得更奢侈了,是按定例解运上来的绸缎过于粗劣,皇帝基本的体面总要维持。
万历时期织造额外坐派最多的十五万匹任务,恰恰是万历九年发布的,这还是张居正主政时期。
张居正起于民间,对民间各种奢侈消费,衣服华丽程度,肚子里门清吧。让皇帝穿的绸缎质料比一般富商都粗劣,那总说不过去。
根据以上所得价格,万历时期平均每年官营织造,定额加坐派(其实坐派里主要是民间领织,属于市场行为了,但这里姑且也算进去),应该是25万两银子的价值。
至于明代其他时期只会比这更少。
25万两银子对明代丝织产业每年创造的价值而言,应该远低于百分之一。
按晚明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对明代广州出口贸易情况的记载:
“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处(引者注:这里指的是广州)运往各地,因为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6个邻国的土著和异邦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葡萄牙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类丝绸,每箱装有100匹真丝,如天鹅绒花缎和缎子、轻料如半花缎、彩色单层线缎。还有250块金子,及每块重12盎司的2200块金锭” [5]
按此记述,仅仅葡萄牙人每年从明代广州运出去就高达53万匹丝缎,即便按照平均每匹丝缎3两银子来计算,也高达159万两银子。
明代朝廷官营丝织品产值仅相当于经由葡萄牙商人出口的丝绸贸易价值的五分之一不到
而经由这个渠道出口的丝绸应该仅仅是当时明代民间丝绸出口的一小部分。
如《晚明史》所说“必须指出,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量,在中国与菲律宾贸易中所占比重是不大的。”[6]
明代海商自己也大量把丝绸运往日本和马尼拉贩卖。
“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晚明史 上册 导论,第53页 )
“尤其受欢迎的大宗货物是丝织品。中国精美的生丝、丝绸极受西班牙人喜爱,往往以高价向中国商人收购,中国商人因此获利甚厚。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菲律宾,专门从事商业中介职业,与西班牙人约定价格,回国代为采办。”(晚明史 上卷 导论,第57页
当时福建海澄(月港)也是明代出口贸易的一个大港口,其出口货物数量应该不比广州少。
曾德昭说:“(福建省)这个省滨海,是中国输出大量商品又一个优良港口,当地的勤劳百姓,把货物运往马尼拉、日本等地区”[7]
按最保守的估计,葡萄牙人经由广州出口的中国丝绸占据当时中国整体丝绸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实际上不可能占据这么高的比例),那当时一年中国丝绸出口量至少也是200万匹,价值600万两银子以上。
明代中国本土的丝绸产量和消费量至少是出口量的十倍以上,按此估算,晚明时期民间每年丝绸的产值至少是6000万两银子以上。
明代官营织造的丝绸(把民间领织)都计算进去,每年价值也只相当于25万两白银,只是民间丝织业产值的0.4%多一点,也就是千分之四。
以上是从出口量来推国内产量。
我们还可以直接从明代国内消费的角度来分析明代民营丝织业的产量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
没有足够的产量,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消费量。从明代丝绸的消费水平,可以反推明代丝绸产量。
明代各阶层丝绸的消费普遍到了什么程度呢?
按照来华传教士的记载明代连穷人都穿丝绸。
“我也毫不怀疑,这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过度,因为在远东,除了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以致不仅那个国度的居民,不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和世界其他地方。”(利玛窦中国札记 第一卷 第二章)
“而在中国,人们虽俭于消费,但穿绸缎很是普遍的”,“农夫皆备有一两件好看的衣服”,“一般老百姓与贵族的服饰又不一样,但外观都很好看。”(利玛窦书信集第四七页,第五十页)
比利玛窦更早的西班牙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也有类似描述:
“中国人男男女女都很严格地遵行他们的礼节,穿着十分整洁,因国内有大量丝绸,他们一般穿得很好”(绪论)
“那里生产的绒、绸、缎及别的织品,价钱是那样贱,说来令人惊异,特别跟已知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价钱相比”(第一卷第三章)
“达官贵人的服装是用不同颜色的丝绸制成的,他们有上等和极佳的丝绸,普通穷人穿的是另一种粗糙的丝绸和亚麻布、哔叽和棉布,这些都很丰富”(第一卷,第十章)
传教士的记载是否夸张呢?
和明朝本土的记载对照,并不夸张
“今帷裳大袖,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名山藏,货殖记 马一龙》
“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松窗梦语)
“不衣文采而赴乡人之会,则乡人窃笑之,不置之上座”(万历《通州志》)
又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客座赘语)
“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嘉靖建宁县志)
“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 (周玺《垂光集》 论治化疏)
“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万历通州志)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蚕桑不种麻;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棉袄午穿纱”(天下水陆路程[8])
这些中外独立的记载,都可以看出一个事实,明代当时无论南北,不管穷富,都普遍穿着丝绸。这和满清乾隆时期相比,英国使者马尔噶尼沿途所见百姓都衣着粗陋寒酸,都是粗布衣服,是截然不同的。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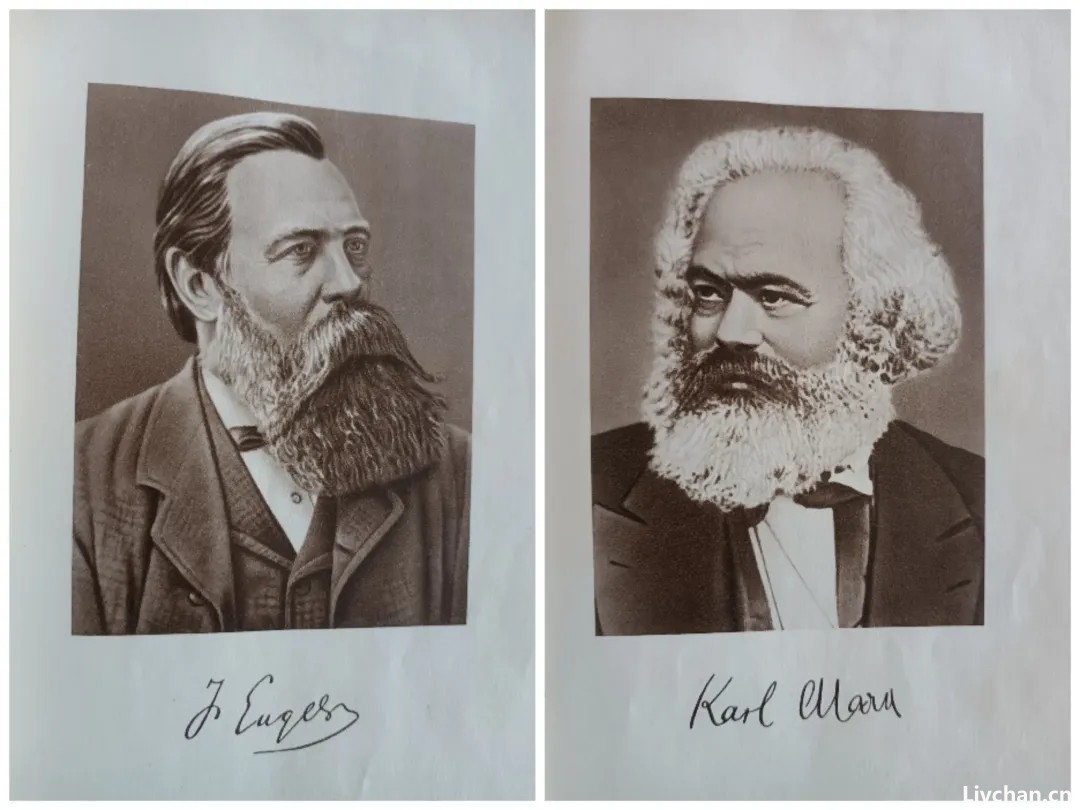 汉宣帝时,有个叫桓宽的人写了本书叫《盐铁论》。这本书是根据汉昭帝时的一场关于国家盐铁政策的辩论会记录改编的。桓宽在整理那些记录的时候,不仅忠实地保留了当时的辩论内...
汉宣帝时,有个叫桓宽的人写了本书叫《盐铁论》。这本书是根据汉昭帝时的一场关于国家盐铁政策的辩论会记录改编的。桓宽在整理那些记录的时候,不仅忠实地保留了当时的辩论内... - 震撼!黄帝内经十二时辰养生秘诀,养生防病延年的秘密!通过遵循《黄帝内经》中的十二经络流注规律,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身体,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养生之道,从而...
-

二战时期,日本的“神风特工队”果真不怕死?看看他们留下的遗书
二战后期的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势已日趋明朗,轴心国的败局已定。在太平洋战场上,号称“世界第三海军”的日军联合舰队连连受挫,... -

(图文)一文看懂五胡乱华:华夏至暗时刻,究竟是谁拯救了汉族?
公元304年-439年是汉人最不愿回想的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来到中原开趴体爱种地的汉人差点儿被团灭这就是史书上一笔带过的五胡乱华那么,五胡究竟是哪五胡呢? - 国学成语,浓缩历史精华;曲径通幽,遇见不一样的中国。公元前403年,春秋列强之一的晋国发生了一起震动“国际社会”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
-
 本文转自文汇报古代人物画的传统,是被尊为画圣的顾恺之立下范式的。《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
本文转自文汇报古代人物画的传统,是被尊为画圣的顾恺之立下范式的。《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 -
 少时曾听老人说,日子不过就是笑笑别人,再被别人笑笑。因为生活总是有苦有甜,若是太较真,难免太辛苦。有时候,乐天一点,化解人生尴尬,又能悠自己一乐。所以,今天我们来...
少时曾听老人说,日子不过就是笑笑别人,再被别人笑笑。因为生活总是有苦有甜,若是太较真,难免太辛苦。有时候,乐天一点,化解人生尴尬,又能悠自己一乐。所以,今天我们来... -

甲骨-曾经风靡清朝末期的“神药”,能快速止血生肌,如今为何消失了?
我国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医学的理论知识,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步发展为如今的医学理论体系。直到目前为止民间依旧流传着许多药理知识,随着... - 傅索安,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员,中国一个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一个很具号召力的活跃分子。因为挑起村民械斗,她叛逃到前苏联,成为了一名克格勃特工并且参与了...
- · 海兰泡惨案中遭到处决的中国人1910年,俄罗斯境内的大乌里火车站发生肺鼠疫,疫情很快沿铁路线传入中国境内,在东三省大爆发,数月内夺取六万人命。面对疫情,俄国政府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