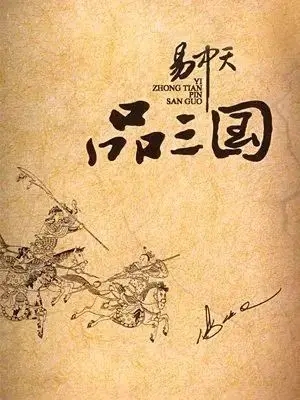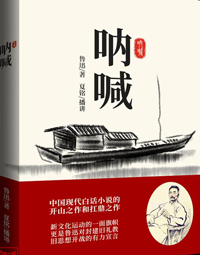只有极其巨大的民营丝绸生产力才能支撑晚明如此普遍的丝绸消费。
民间丝织业有工人起家而成资产百万的巨富者。
“潘氏起机房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万历野获编 卷二十八)
可见明代民间丝织业的暴利程度。这里的百万应该是百万两白银,把白银价值算成现代的,就是资产过亿的富豪了。
从一些记载来看,明代晚期仅苏州城内的丝织业规模从业者就接近半个城市的人口。
明晚期朱国祯说苏州人“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四,矿税,《四库禁毁丛刊》史部第29册第118页)
《镇吴录》有相似的记载:“东半城,贫民专靠织机为业,日往富家佣工,抵暮方回。”[9](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0页)
苏州城当时人口至少百万以上,即便半城的说法夸张,那估计十万人口以上从事丝织业也是合理的。
蒋以化说;
“我吴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西台漫纪,卷四 纪葛贤,续修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53页)
这仅仅是苏州城,晚明时期还有大量专业从事丝织业生产和贸易的市镇,其繁荣程度不下于大城市,如苏州府的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不一一详说了。
以对晚明人口保守估计两亿来算(其实远不止),即便算当时人口五分之一穿丝绸,每年平均一人消费一匹丝绸,那也就是四千万匹丝绸,以每匹丝绸平均3两银子计算,那就是一亿两千万两银子。
按此计算,明代官营丝绸每年价值25万两银,只是民营丝绸业产值的千分之二。
以往论者断言什么明代丝织业是处于封建势力的严重控制和剥削之下,如同梦呓一般。
包括范金民虽然列举史料论证了《明史》关于万历加派织造数字的错误夸大,但依旧沿袭了明史中的陈词,什么加派缎匹“最为民害者”,“织造一项尤为最苦”。这属于偏见既定之下,无论事实如何,都要依附到既定结论。
且不说明代坐派的丝绸让民间机户领织,大部分情况是市场行为,支付等值报酬的,稍有让机户吃亏,官员就要在奏疏里连篇累牍的抨击,机户也能以价格低为理由调头不干。
“官府对于领织,若‘银两尽行给发,机户有利,接迹而来;内监挟朝廷之威权,银两不免减削,机户无利,掉臂而去。’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这正说明,领织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每遇争执,机户就‘动以料价不敷为词’,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10]
即便明廷把岁造加坐派的缎匹每年从民间机户那里无偿征收,那也远低于正常的税收比例。
明代丝织业税收低到几乎没有(对行商征收的税都被偷漏大半),宫廷和政府自己从其他收入里腾挪筹措经费组织自用生产,还被连篇累牍的攻击贬损。
在明代是工商从业者和其利益代言人完全被娇惯坏了,至于现代的许多人,则是长时间偏见灌输下,只会鹦鹉学舌。
明代不必说什么宦官专营,哪怕宦官接受委派,正当查税,想对丝织业征收合理税费,都会被文官用一切手段抵制。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中,记录了织造太监孙隆,想要在丝绸业征税。
“织造太监孙隆,带管税事。本安静识事机,四月中至苏会计,五关之税日缩,借库银以解。颇严漏税之禁。”
所谓 “安静识事机”,也即士大夫都觉得这个太监不怎么搞事。但因为当地偷税漏税实在太过猖獗,本就很低的商业税收还不断缩减,以至于挪借其他银子填补。孙隆这才要打击偷漏税行为。
此外到苏州听从当地人建议,希望对丝织业征税。
结果孙隆反而被苏州丝织业工人打死手下人员,驱赶出苏州,再不敢过问收税之事。而这些丝织业工人的暴乱明显是受官绅的纵容乃至煽动阻止。被抓起来承担责任的工人领袖葛成,关在狱里,被官绅们当英雄来优待,还替他改了名字叫“葛贤”,最后被释放,“缙绅皆待以宾礼,称曰义士。”
打死人命,就因为是和宦官、和皇帝捣乱,不但半点事情都没有,反而成了官绅宠儿,这又是明代才有的怪象。
许倬云大师说的明代政府专利,宦官管理而文武官员无置喙余地,那只能是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和明代现实毫不相关。
————————————
【注释,文献出处简短的,都写正文括号里,比较长的放在文末脚注】
[1] 范金民 明代官营丝织业三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 石星奏疏原文“查得万历九年十月内。该内织染局署局事、御马监太监张诚等题织上用等龙袍共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六十四匹。本部覆奏钦依派行浙直司府去后。又查得万历十四年三月内大学士申时行等题諴织造袍服等项。随该本部查得前项袍服巳解过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三匹,未完一十二万一千三百八十二疋。以五分为率,解进者。已一分矣。题请裁减节。奉圣旨这造袍服未完数内准减一万疋钦此,已经通行钦遵”
[3] 范金民 明代官营丝织业三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 明神宗实录卷5 隆庆六年九月“工部题在京并南京官中使长随共一万四十员名,共该纻丝绫二万六千六百九十三疋,每疋照例折银三两,共该银八万七十九两”
[5] 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 李申翻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第10到11页
[6] 樊树志《晚明史》上卷 导论,复旦大学出版2003年,第58页
[7] 曾德昭《大中国志》何高济, 李申翻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第10到11页
[8] 转引自《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1981年,第267页
[9] 《镇吴录》万历时刊本,转引自《明代城市研究》第80页
[10]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157页

许倬云大师朱元璋一文谬误(四)——皇帝不行的事,宦官能行么?
五、宦官批红权问题
许倬云说:“有明一代,宦官假借皇权,以司礼监的名义代表皇帝批核奏章,文官系统无法反抗”
明代皇帝都做不到的事情,许大师轻飘飘就让宦官做到了。
他大概是看了《明史》里的话:“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 ‘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职官志一)
但这和明代的政治实际不相干。
明代不要说宦官的批红不可能是最后拍板,就是皇帝本人自己的朱批,也还要经过内阁的审查,内阁如果不同意,可以封还御批,让皇帝修改意见。
内阁通过了,还不算完事,还要下发六科,经过六科给事中审查,给事中不封驳,才能作为正式圣旨下发给六部等有关部门自行。
这个流程简单示意如下:
内阁票拟——皇帝有反对意见的批改或留中,没有意见的送司礼监批红——内阁审核,如果不同意皇帝修改意见,封还。审核通过,拟旨,发给六科——六科审核不通过,封驳回去重新修改,通过——交六部执行
明代史料里,内阁封还皇帝御批、驳回皇帝旨意的记载很多,
“间于民情有干,治体相碍,亦不敢苟且应命以误陛下,未免封还执奏,至再、至三”(徐溥 徐文靖公奏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十五)
“廷和每召对,上必温旨谕之,而持不可者三,封还御批者四,前后执奏几三十疏,上益忽忽有所恨”(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
“帝令内阁宣谕。廷臣叶向高留弗宣,帝又遣中使促之,向高反覆上言,封还手谕。帝不得已从之。”(元明史类钞)
“指陈乘舆之非,封还成命不以为戆”(沈鲤 《亦玉堂稿》)
“大学士沈一贯以原本原票封还御前,因上揭力言其不可”(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万历二十九年十月)
通过内阁这一关,还需要通过六科给事中这一关,旨意被给事中封驳,还是不能作为国家政令下发。
顾炎武说:“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故给事中之品卑而权特重。”(顾炎武 日知录,卷九 封驳条)
另外也可参看明实录相关记载:“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如六科不封驳,诸司失检察者,许御史纠弹”(明穆宗实录 卷三十九,隆庆三年十一月),
给事中的封驳权力是朱元璋建立给事中制度时就赋予的。
“上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岂能一一周徧?苟政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悉心封驳,则庶事自无不当。”此六科稽查号件,封驳章奏之例也。”(《春明梦余录》 卷二十五)
明代宦官批红,不是和许倬云想象的那样用自己意见的去批示奏折,而只能是用红笔把内阁的拟旨原样誊抄一遍,这本质不过是一个文书工作,是多个太监轮流值班完成。
这点在天启时任职的太监刘若愚写的《酌中志》里交代得很明白:
“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正。”(《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识掌)
也就是皇帝觉得需要修改的,自己亲笔批改,剩下的让太监分工有朱笔按照内阁票拟誊抄,遇到有错别字的可以略微改正。
另一处说:
“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笔分到直房,即管文书者打发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阁中原票用朱笔誊批,事毕奏过,才打发。此系皇祖以来累朝旧制,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酌中志》卷十二,各家经管纪略)
也是依照内阁票拟誊抄。
明代确实有宦官掌握较大权力的时期,刘若愚亲历的魏忠贤时期即如此,但这不是某些人臆想的靠批红。而是宦官在皇帝许可下,和外廷文官达成合作共识才行。
《酌中志》说的,符合阉党意图诏旨本身就可以让内阁拟定。
“五日一比,追赃之严旨,四六骈俪之温旨,皆昆山等所票拟也。阁中俱有底簿可考,中书官可证也。凡逆子良卿之奖敕、诰券文,皆内阁词臣撰拟,用红掩面揭奏,亦阁中有底簿可考也。”
“一切削夺勒限追赃诸严旨,皆内阁顾秉谦等票拟,非中旨见,有阁中底簿中书官可证也”
至于魏忠贤等宦官也确实会遇见和内阁票拟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是去设法说服皇帝,让皇帝亲自修改内阁票拟。
“时逆贤、永贞、元雅、文辅,先将应处应点姓名及应改票帖俱托体乾口奏,曰:万岁爷某系门户,该处某票某字当改,或从臾。先帝御笔亲改。”
,认为太监依靠批红篡改内阁意见,然后发下去直接当成圣旨,以此实现对权力的掌控。这纯属搞笑。
有些记载说明武宗时刘瑾自己改动过内阁票拟。但这个前提也是内阁默认,不对改动提出异议,本质还是太监在皇帝授权下和内阁外臣之间形成了合作关系。
明代真正太监得势,掌控大权的时间是极少的,把王振、刘瑾、魏忠贤当权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十四年。
除王振是死于战时,刘瑾、魏忠贤本身就是文官排挤倾轧下倒台惨死的。
许倬云说的“有明一代,宦官假借皇权,以司礼监的名义代表皇帝批核奏章,文官系统无法反抗” 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信口开河
六、锦衣卫、东厂之类
这些也是老生常谈了、
许倬云所谓锦衣卫“其权力之大,汉唐皇朝从未有过。”
汉唐宋的皇权在满足皇帝个人私欲、财税控制、对民间剥削方面远比明代大得多。
汉唐宋没有锦衣卫、东厂这是怎么实现的?
一提锦衣卫、东厂就认为代表皇权大,是不动脑筋的条件反射,机械的刻板思维。
许倬云之类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明代舆论独立,不受皇权操控,加之政务几乎公开透明,这使得锦衣卫、东厂之类的威力远没有他们臆断的那么巨大。
明代这类直属皇帝的机构,本身就时时刻刻受文官系统的监督制约弹劾,稍微有错,就会招致雪片似的攻击。
说句某些人不爱听的话,明代这类所谓特务机构,其受舆论的监控程度,受文官的弹劾程度,还远在现代西方国家的特务机构之上。
现代西方国家有严格的保密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的内部事务,并不会随意让公众知晓谈论,其干下的各种丑事,不光彩事件也都有保密期限。
明代锦衣卫东厂则几乎从来就是明代舆论的重点监控对象,文官体系恨不能时时刻刻搜罗这些机构的负面材料,当做攻击靶子。
另外关于锦衣卫东厂在明代出现的历史背景,我过去写过,这里简要重复下。
从秦朝算起,中国皇权经历不断被削弱的过程.初期政府和皇室还没完全分开,政府相当于皇帝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皇室在政治领域进一步退缩。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皇帝对经济财政的控制权也完全丧失,这比起宋代皇帝还能大量财政收入纳入内帑私库来说是更进一步衰落。
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
皇权被削弱到极限的时候,也会产生一定反弹。
汉唐宋皇帝的权力还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满足私欲、操控财税,行使个人意志。到了明代,皇帝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后期废除),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这表面上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实质有一定的必然性。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文官系统面前,都需要另设机构来给自己增加力量感,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即便有了锦衣卫东厂,明代皇帝在许多事件上都依旧要屈服在文官的压力之下,这方面事例太多,前文也列举过不少,这里不赘言了。
七、廷杖
许倬云说“皇权的行使,更有所谓廷杖的暴力方式,群臣的奏对,一不合意思,就可能当场受刑,甚至立刻被扑杀。” 还说“明代这种皇权不测之威,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不知道他是不是受明史影响,认为廷杖是明代才发明的。
《明史》说:“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志七十一 刑法三)
修明史的清廷奴才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这么说?以他们对古籍的阅读量,不至于这么无知。
其实廷杖原本就在金和蒙古盛行。
如朱熹记载当时金虏情形
“王仲衡云:“虏中大臣有过时,用紫茸氊铺地,令伏其上杖之,尝有一宰相、一驸马受杖。驸马因此悒怏而死,非恨其杖也,恨不得紫茸氊也。”(朱子全书 第18册,第4159页)
蒙古国从第一代头目铁木真开始就喜欢用杖刑殴打官员。
蒙元时期官员也屡被杖死。
“诏哈玛尔惠州安置,苏苏肇州安置,临行俱杖死,仍籍其家”(元史纪事本末 卷四 托克托之贬.哈玛尔附)
“奏也先忽都违命,杖死之。年四十四。有诗集十卷。(元史 列传第二十七)
官员还会被元酋当众打耳光。
忽必烈时期,任用桑哥残酷搜刮民财,有官员批评桑哥,忽必烈大怒,就打耳光泄愤。
“彻里乃于帝前具陈桑哥奸贪误国害民状,辞语激烈。帝怒,谓其毁诋大臣,失礼体,命左右批其颊。”(元史列传第十七)
金和蒙元头目用这种方式来表明臣下本质不过是他们的奴仆。
当然以前的皇帝也有廷杖的记录,比如北周的宣帝宇文赟
“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北史 卷一十,周本纪下第十)
隋文帝:
“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
“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帝宠高颎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庭杀人,兵部侍朗冯基固谏,帝不从,竟于殿庭行决”(隋书,志第二十 刑法)
还有唐玄宗
“帝动不称旨,暴怒笞挞左右”(旧唐书,列传第一)
“监察御史蒋挺坐法,诏决杖朝堂”(新唐书,列传第四十二)
隋唐的廷杖应该是受北朝蛮族习俗残留影响。
明代的廷杖则应是受离其最近金元时期的陋习影响,
但这个刑罚在明代完全是相反的作用。
施行廷杖结果是皇帝名誉扫地,官员备受舆论尊崇。
明代的廷杖绝大部分情况只能对付四品以下的官员。
所谓群臣奏对,一不合皇帝意思,就可能当场受刑,甚至立刻被扑杀云云,纯属许大师的梦呓。
考察明代皇帝几次大规模动用廷杖
一是正德帝要南巡,官员死活不许他去,廷杖那么多人,也只能局限在四品以下,最后仍旧是没能如愿。一直到宁王造反,他才找到借口
一是嘉靖帝大礼议,要认自己的爹做爹,内阁不许,封驳了嘉靖那么多次,嘉靖都没办法,给内阁成员行贿也试过了,派太监给内阁成员下跪求情也试过了,都不行。
他那时候也根本没用廷杖对付官员。
直到群臣堵在宫门口鼓噪抗议逼迫他必须杀张璁。
嘉靖好言相劝都没办法停止他们的堵宫门示威活动,没办法了才廷杖下级官员,对内阁他仍旧是没办法,直到后来绕了大圈子才把张璁调入内阁。
一是张居正夺情,群臣抨击弹劾,不让张居正退休就不罢休。
换了其他时代,这类事件,根本没官员敢站出来反对。甚至直接当造反来处理了。
所谓廷杖,恰恰是群臣逼迫皇帝遵循他们的意志,
皇帝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动用的结果,是皇帝在舆论里被丑化
孟森在《明史讲义》早就评价过:“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
只能说许倬云的见识比百年前的孟森都不如。

许倬云大师朱元璋一文谬误(五)——明代科举只测儒家,独尊朱子么?
八、礼敬大臣,是否能坐下谈话的问题。
许倬云说:
“在中国历史上,汉代的中央文官,其高阶者可以和皇帝坐下谈话,唐代的朝廷上也有文官的座位,即使宋代,宰辅必须站着奏对,君臣之间有一定的互相礼敬”
其实汉代还没有椅子,跪和坐的姿势相去不远。
即便抛开这点不谈。
他的意思自然是明代的文官是不能和皇帝坐下谈话的,明代的君臣之间是不存在互相礼敬的。
这和明代的事实完全不符。
周怡在隆庆元年的奏疏里说:
“我祖宗朝优待三公之礼甚隆。其于辅弼之臣,必称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称。一则曰先生,再则曰先生毎。历朝实录可考也。仁宗以来未之有改也。先帝世宗皇帝初年于辅臣杨廷和等犹称先生。”(周怡《讷溪奏疏》 敬大臣 )”
皇帝称官员为先生,并且不敢用官名相称,不敢直呼姓名,注意周怡这里用的“不敢”的字眼,这礼敬的程度是很高了。
其实对品格高尚的臣民,尊称先生而不直呼姓名,是从朱元璋就开始的传统。
唐枢在《国琛集》里记载朱元璋对陈遇尊重备至的事迹:
“陈遇,金陵人。博究经史,有治才。太祖召见礼甚,称先生而不名,日侍帏幄,坐久必赐宴,间命厩马送归,车驾三卒其第。先生竭心摅悃,所献替悉保国安民至计。授学士者再,固辞。授侍郎,固辞。授礼部尚书,又固辞,乃不复强之以官。欲官其子,亦辞谢。眷待之隆,亚于勋戚。”(《国琛集》卷上)
朱元璋不仅尊称他先生,而且坐着谈话时间长,还一定会赐宴。
朱元璋一再委任他官职,他一再推辞,朱元璋也不生气,反而称赞他品格高尚,自己愿意成全他的高风亮节:
“戊午复除礼部尚书又固辞。上曰 士之有志节者 功名不足以介意 其卿之谓乎,朕不强卿以成卿之名也。自是每燕闲,辄召问古今得失”(焦竑 国朝献征录 卷一百十六 陈静诚先生遇传)
至于让官员坐下谈话,这在明代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时候不需要多高阶官员都行。
类似上面提到朱元璋和陈遇会面,陈遇就是坐着谈话。
这方面的记录数不胜数
“洪武中,大臣如魏国公达等不时赐宴预坐,及学士承旨宋濂等隅坐讲论。至仁宗亦然,”(王世贞 皇明异典述,赐座)
“汪叡,洪武初为春坊司直郎,上亦日召侍讲,周旋于两宫之间,与朱善、刘三吾二学士,趋朝则同班,赐座则联席,人称三老。”(《元明事类钞》 学士同班)
“又明年,独召还京,赐座与语,欢甚”(《三家世典》 郭英)
以上还是零散的记载,其实朱元璋对官员赐座谈话奏对都有制度规定
“凡赐座,洪武初令凡朝退燕闲及行幸处,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及勋旧文学之臣赐座,又令凡赐坐不许推让。坐后遇有顾问初时跪对,毕即坐,若复有所问,坐朝上对,不必更起,同列侍坐,或被顾问一人奏对,余皆静听,毋搀言剿説。如各有所见,候其人言毕方许前陈。 又令执政大臣年高者,,取自特旨免朝,倘有顾问于便殿赐坐”(《礼部志稿》 卷十)
王世贞似乎认为明仁宗之后,皇帝赐座的事情不多见。
但实际上后面皇帝赐座也常见,例子多的举不过来。
“(永乐)四年二月视学,上服皮弁行四拜礼,御彛伦堂,赐祭酒胡俨、司业张智坐讲,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坐坐以听,赐毕赐答,明日俨等率师生上表。”(殿阁词林记)
“(明宪宗)上视国子监,躬谒先师孔子,行四拜礼,幸彝伦堂。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学士皆赐坐,祭酒司业坐讲赐茶”(明宪宗宝训,成化元年三月)
“(明孝宗)御彝伦堂,授经于讲官,祭酒司业赐之坐讲,祭酒费訚讲商书说命,惟天聪明一节”(明孝宗宝训)
“我皇上(嘉靖) 绍帝王鸿烈 光祖宗旧制,肇御无逸殿,则命大学士坐讲。锡宴豳风亭,则命大学士坐飨。陪祀土谷坛,则命学士分直。临幸太学,则命学士侍坐听讲。”
“嘉靖十年八月癸卯,西苑豳风亭落成。上御无逸殿,命辅臣李时翟銮坐讲,暨日讲官顾鼎臣、谢丕、张潮臣、道南分撰书无逸诗豳风讲章进呈毕,设宴列坐于亭之两旁,天颜澄霁,玉音宣畅盖君臣同游之盛如此。”(殿阁词林记 明 廖道南著)
“(明穆宗)上御彝伦堂,命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学士坐赐茶,授祭酒司业经,坐讲”(明穆宗宝训)
例子太多,不必再举了。
我倒也不认为皇帝让官员坐一定就是君臣地位平等,但许倬云把什么汉朝高官可以坐下和皇帝谈话之类当成贬损明朝的理由,就也必要列举事实驳斥了。
九、明代科举是只测儒家,独尊朱子么?
许倬云说“明代科举,完全以测验儒家经典中的知识作为依据,儒家的学说中又独尊朱子学”
明代的事实并不如此。
明代科举策问测验考察的内容很多,绝不是只限于儒家经典的知识。
有农业、兵备,经济理财、水利建设、马茶盐铁、军事武略、乡情国情等等。这方面可以参考相关论文[1]。
明初甚至还有天文律历方面的试题:
“永乐初科,太宗思求博闻之士,命学士解缙择天文律历、礼乐制度,拟撰为题。上意士子必为所窘,及得曽棨卷,记诵详尽,叹异以为第一人。御笔批曰:贯通经史,识达天文,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资启沃,惟良显哉。”(黄佐《翰林记》,卷十四,殿试拟撰策问)
曽棨就凭着应答这份试卷的优异表现,成为永历初科的状元。
至于所谓独尊朱子学,本来这也没什么不好。许倬云喜欢强调对抗皇权之类,程朱理学恰恰是儒家学说里对抗君权的锋芒最犀利的学派。
这只要稍微看过点程朱原著,就不难明白。
科举士子人人都要读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里面就有朱熹的一句话“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但是明代的科举偏偏又谈不上独尊朱子学,甚至可能都不算独尊儒学。
可以参考张献忠的一篇论文《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2]
这里不妨择其要者,简单介绍一下。
万历十五年的礼部尚书沈鲤描绘他所见的科举情况:“以六经为滥套, 而引用《左传》、 《国语》矣。《史》、《汉》穷而用六子; 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 凿朴散淳、离经叛道”(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 卷八十四 科考四)
万历三十一年的礼部尚书冯琦则说当时科举风气:
“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朱程,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语道既为蹖驳,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 经学几为榛莽”(顾炎武: 《日知录》卷十八 《科场禁约》)
隆庆二年, 李春芳会试主考, “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 ( 指阳明心学) ”,“以 《庄子》之言入之文字”。顾炎武说 “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 顾炎武: 《日知录》卷一八 《破题用庄子》)
袁黄(他的《了凡四训》颇有名),万历十四年中进士,后来编写大量科举考试用书,贬损程朱的注释,否认程朱在科举考试中的指导地位,说:
“拘定一家之言, 不许分毫走动”会导致“士子之识见当愈卑, 而文风当扫地矣”。
他称赞包括张居正、李廷机、还有自己的科举考试文章不遵循程朱注释,“全不依注, 可称千古绝唱”(袁黄 《游艺塾续文规》卷一 “国家令甲”)
袁黄说要做出好的八股文需要满足这样的要求:
“时文虽小技, 亦有三昧在焉。要读尽三代两汉之书,又要胸中不存一元字脚; 要包罗天地古今之态, 又要赤洒洒不染一尘”(袁黄: 《游艺塾文规》卷一 “举业三昧”)
十、孟子节文和明代儒家是否沦为对君主绝对忠诚
许倬云说“明代的考试删除了儒家学说中一切与政权抗衡的部分,例如《孟子》里面有一些章节就被删除。”
从而就是所谓“儒生长期接受洗脑教育,儒家思想沦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
这指的是孟子节文,也即把孟子中类似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等内容删除了,出了一个节选本用作科举考试参考书
他说这话,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整个明朝始终都用孟子节文来科举考试。
实则孟子节文洪武二十七年才编写,使用到永乐九年就废除。
总共不过才十六年的时间。
而且即便这段时间内,《孟子》全本也在民间自由流通,没有任何禁止。
其实类似孟子的话,朱元璋自己的皇明宝训里就说过,比如这段话
“帝谕群臣曰:……盖臣不谏君,是负其君,君不受谏,是负其臣,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者,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天地,有功于社稷人民也。”(《皇明宝训》卷三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第8册第三五页)
这里的褒贬是把社稷人民,放君之前,君如果不能正确听取意见就是昏君,有功于天地,有功于社稷人民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前面引用过的,“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天之视听在民,民怨则天怒矣”
朱元璋在晚年编孟子节文选本,可能是觉得君臣合作关系,孟子的话过于激烈,容易挑起情绪,有负面影响。就实质性的思想而言,他和孟子并无本质分歧。
至于许倬云说的在明代“儒家思想沦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属于一点明代的思想史都不了解。
明代儒家的主流思想从始至终都不是什么对君主绝对忠诚。
到中晚期,甚至经常把人民可以推翻君主拿来威胁皇帝。
类似丘濬在大学衍义补里说
从社会征集来的财富,皇帝只能是履行为百姓理财的职责,而不能属于皇帝私有,“君特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
君主如果垄断利益,就是违背天意,“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
君主如果搞官营产业,禁止私营,垄断经济,那就就不符合上天设立君主的意图了:
“立官以专之、严法以禁之、尽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岂上天立君之意哉?”
官府不要自己去和老百姓做生意,非但食盐不应该专卖,其他事情也一样。民间自己方便做的事情,官府不要去做:
“官不可与民为市,非但卖盐一事也。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
君主必须顺从人民的意愿,不顺从人民的意愿,人民推翻君主就是合理的,老天爷也会响应人民的要求:
“吾咈民之欲则民不欲吾为之主矣,民不欲吾为之主则必将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这就是明代内阁大学士笔杆子里摇出来的话,这些思想和许倬云说的“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没有一毛钱关系。
至于到万历时期,官员动辄谩骂皇帝,威胁老百姓可以造反。如赵世卿说“民之心既天之心,今天谴频仍,雷火妖虫,淫雨叠至,变不虚生,其应非远。” 李三才之类说出“民又君之主也”,从思想脉络上说,都是毫不奇怪的。
[1] 黄俊官、黄明光 《关于明代科举考试试卷的相关探讨》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2年第2期
[2] 张献忠《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来源:杜车别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公司发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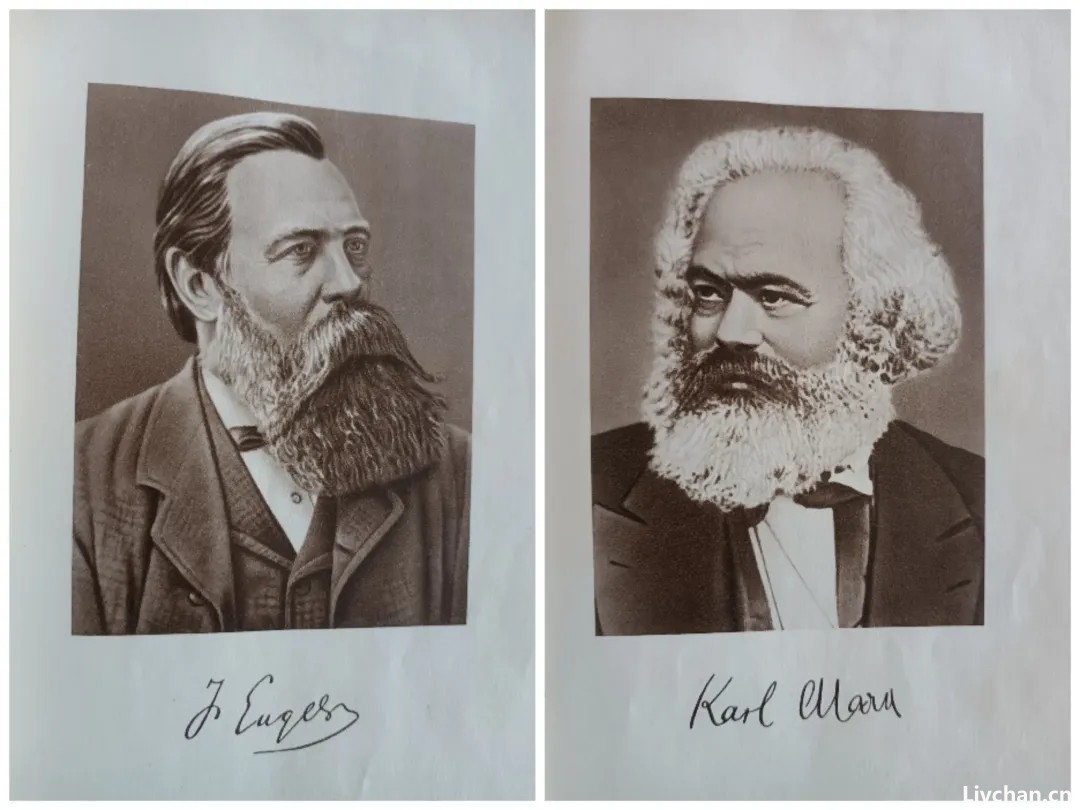 汉宣帝时,有个叫桓宽的人写了本书叫《盐铁论》。这本书是根据汉昭帝时的一场关于国家盐铁政策的辩论会记录改编的。桓宽在整理那些记录的时候,不仅忠实地保留了当时的辩论内...
汉宣帝时,有个叫桓宽的人写了本书叫《盐铁论》。这本书是根据汉昭帝时的一场关于国家盐铁政策的辩论会记录改编的。桓宽在整理那些记录的时候,不仅忠实地保留了当时的辩论内... -
 那两年,纪登奎与我的交谈,主要在出差路上、茶余饭后,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时。绝大多数情况是,他在说,我在听。闲谈中,我偶尔会提点问题,他也偶尔停顿一下,问我什么看法...
那两年,纪登奎与我的交谈,主要在出差路上、茶余饭后,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时。绝大多数情况是,他在说,我在听。闲谈中,我偶尔会提点问题,他也偶尔停顿一下,问我什么看法... -

统统上战场,乌克兰颁布最强“抓壮丁”令,国民党看了都自愧不如
《军武次位面》作者:大伊万目前,俄乌军事冲突已爆发540天。自从前几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气冲冲地宣布,说要对乌克兰的动员体制进行改革之后,乌克兰方面果然祭出了一整套... -
 今天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关于纳粹的。01我对纳粹史一直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纳粹的大屠杀不是孤立突发的事件,它人类黑暗面的一个象征,一个深渊,隐藏着某些人性的秘...
今天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关于纳粹的。01我对纳粹史一直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纳粹的大屠杀不是孤立突发的事件,它人类黑暗面的一个象征,一个深渊,隐藏着某些人性的秘... -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多也都是高速发展期的国家所共有的。如果处理得当、继续改革,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得到解决。不过,在这些所有的问题之...
-
 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所处的场合非常陌生,身边还站着许多不认识的人,第一时间肯定会认为自己被绑架或者落入歹徒之手,生死难测。在1978年,一对韩...
设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你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所处的场合非常陌生,身边还站着许多不认识的人,第一时间肯定会认为自己被绑架或者落入歹徒之手,生死难测。在1978年,一对韩... - 很多我们从小就听的故事,后来发现并不是那样。有些故事经过教科书的“筛选”变成了简单粗暴的“只要什么什么,就能什么什么”,或者只是为了解释它所在的章节,而忽视了故事...
- 如果想想袁崇焕的结局,或许洪承畴被俘之后的投降也就情有可原了。如果想想朱元璋,那么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做法也就可以理解了。崇祯皇帝并非庸君。然而,在面对祖宗家业的大...
- 提起浙江湖畔大学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但至于后来发生的种种变故,以及为什么关停等内幕信息却不足为外人道,因为这种毁三观而又错综复杂的事情根本无法对外公布。马云究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