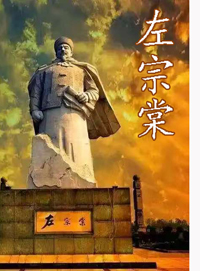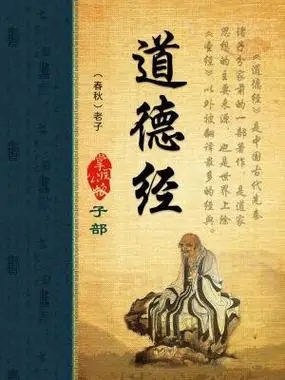八 苦乐童年
(一)
鄙人生性懒惰,出世就不高兴,在蒲团上一坐就是三年。
也不知道有多少代多少年了,在贫困的农民眼里,高粱可是一个宝。搭建一座茅屋,用麻经子将高粱秸秆编织在椽子上,便成了屋顶的里子。将高粱秸秆编织成的薄(音)篱加持在房梁下成为墙,使茅屋分为里外三间。在里间的北边或南边靠墙处,用土坯垒起三道长六尺宽二尺半的矮墙,铺上双层或三层的薄(篱),就成了床。用高粱秸秆顶端细长的一节(人称梃子),用麻绳将其竖横两面相搭穿成结实的多用途的锅拍子,来客人时将其放在正间的比较大的瓦盆上,就成了放食品招待客人的“桌子”(一般穷人家都没有木桌)。用梃子剐成的篾子,可以编织成类似清朝官顶子形状的“廉(音)帽”。梃子皮(裤)可以编成两种厚薄不同的蒲团。薄的蒲团厚度约3-5公分,直径约60-80公分,妇女用它坐在纺车前纺棉抽线。我就是在这种蒲团上坐了三年。厚的蒲团高约10-15公分,用于招呼客人坐的。那时候,穷人家一般都没有木凳,不是坐在门坎上,就是坐在土坯上。他们在院子里吃饭,或在邻里饭场上吃饭,都是习惯性地蹲着,或者是坐在地上。
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天一天地成长着。
据母亲回忆,大概在我一岁多的时候,东院六祖母(三曾祖的三儿媳)对她说:“你把这臭包子整天抱在怀里,也不嫌心烦。”说着,一把从她怀里夺过去,像栽树苗似的往蒲团上一戳,我竟然稳稳当当地坐住了。她和六祖母还有周围的人都开心地笑了。四岁那一年,我从蒲团上站了起来,抬起脚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小院,走进了社会,走上了数十年的风雨之路。
我从小很少说话,舌尖已经僵了,不会打转转了,说起话来就是一个大舌头。和小玩伴们一起玩儿,口齿不清。有一个小玩伴叫二娃,我叫起他的名字,就变成了“鹅娃”。
我家前边那条小水沟宽有丈余,呈东西走向。沟南边是一条官道,向东经村东北角的关帝庙通唐河名镇桐河,向西经西老坟可达南阳府。官道上虽然说不上有多热闹,可商贩挑夫,行人乞丐,也熙熙攘攘,往来不断。就连杆子,红枪会、社团、军旅,也偶尔打此经过。
这官道上就是我们小孩子很好的一个玩耍处。以前乡村农家子弟,不像现在城里的孩子有许多小玩具,诸如布娃娃、小汽车、小飞机、变形金刚之类,在爸妈百般呵护下尽情嘻戏。我们小时候,父母子女多,照顾不过来,稍大一点就自个玩去。我和玩伴们在宽阔的官道上追逐打闹,旱天滚一身尘土,灰头土脸,雨天玩一身泥,一个个成了小泥人。
暑天雨后,官道上会聚集更多的玩伴,摔泥炮是我们的最爱。大家一起肆意戏虐,摔泥炮,唱儿歌,饶有兴头。
摔泥炮得把揉搓得很滋润的泥巴蘸着水捏成盆状,底子要特别薄,然后小心翼翼地揭起来,一手高高托起,口朝下骤然摔到地上,便会砰然作响,就像现代小孩子玩的摔炮一样。那时的玩伴在摔泥炮前嘴里还要念念有词,一唱一和:“瓦屋瓦屋谁补(瓦房漏雨谁补)的?”“我补的。”“补个啥?”“补个泥巴片儿。”问者突然将泥盆摔下,越响越好,嘴里还要再来一句“糊你丈人屁股眼儿!”玩伴们兴致极高,乐不思归。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成了我一生中最清楚的追忆之一。那还是在1954年,新中国的经济刚刚恢复,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在农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可是到了1955年1月,毛主席发现一些地方出了问题,粮食统购统销统过头了。
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基层干部身上。建国初期,地方政权干部奇缺,毛泽东早先为夺取政权培养的干部只能配备到县区两级(人数也不多),而广大的农村管理,只能依靠在土改中发现的一些积极分子。乡一级的书记、乡长(其属员只有一名财粮),都是从青年积极分子中选拔出来的,而合作社的干部又多是一些文盲。这样的干部队伍积极性很高,政策水平却很低。
我们乡的乡长就是邻村的一个半文盲青年。合作社的干部,有半文盲,有文盲。我父亲就属于后者。为了搞好统购统销工作,他们连明彻夜地开群众动员大会。我那时还不到六岁,也曾亲临其境。我印象最深的是拉歌竞赛。会议主持者组织青年和学生队伍相互拉歌,一方唱罢,拉另一方唱,往来反复,好不热闹。
十四区区委书记白虹彩身着列宁装,留着齐耳短发,腰扎武装带,挎着盒子枪,一副英姿飒爽光彩照人的形象。她在集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农民代表一个接一个发言,表决心,一定要把粮食卖给政府。正是在这鼓舞人心的环境中,人们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了,争相报名为统购统销献出粮食。我父亲身为干部,自然不甘落后,几乎要“倾囊相授”了。
眼看就要青黄不接了,家里的余粮难以养活一家人,母亲只好领着我们外出乞讨。不多的粮食仅够父亲(干部是不能外出乞讨的)在家留守食用。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一家人第一站到了茶庵。母亲小脚走得慢,十五岁的二哥(人高马大,第二年便入伍去了朝鲜)挑着担子,一头是被褥,一头是五弟,走得快,只能走走停停,等一等母亲。我是由二堂兄(大伯的次子)带着,不紧不慢地跟着。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一路乞讨,晚上找人家借宿,或者睡在人家过道里、房檐下。有一次,我随着二堂兄到了一户人家,冷不防从旁窜出一条大黄狗,吓得我撒腿就跑,摔了一跤,手中的饭碗也摔了个粉碎。好在那家人喝住了大黄狗,又用他家的碗盛了饭让我端走了。
这次乞讨之旅,终点是宛城附近的菱角池(音,晚年我还曾打听过此地,人说在今迎宾大道南侧),时间将近半年,听说政府又返还了多征购的粮食,母亲就带着我们返回家中。
在解放初期,农村已经普及了小学义务教育。我这一代人终于可以进学堂了。那时候,我们农家孩子上学一般都比较晚。1958年秋,我九岁了,该上学了,母亲用几块旧布为我缝制了一个小书包,我便高高兴兴地和玩伴们一起,到仅有半里之遥的初级小学堂(简称初小,1-3年级)去报到。
那所初小位于我们村西北方向的一个小村子的东南角,离我们家很近。学校的东边并排两个教室,北边正中一个教室,东头一间房是教务处兼教师办公室,西边两间房是教师住室。
我的第一任启蒙老师,是一位姓许的白白胖胖的年轻母亲,她的女儿仅比我小几岁。许老师像慈母一样教育我们,关心我们。
可没多久,由于中央一位主要领导人趁着大跃进运动在河南强行推广军事化管理,取消小家庭,将村民男女分开集中住宿。在教育方面也强制推行撤点合班并校。我和小同学们便随着老师一路向北,第一天到了五里外的西张营。按照年级和另一个大的学校的学生,打乱重新分班,换了教师,配备了一名生活辅导员。不分男女同学,我们在一个大房子的地铺上睡了一晚。第二天又上路了,朝着东北方向,走走停停,走了大约二十余里路程,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叫锅场的学校,才安顿下来。
在那个学校逗留的时间并不长。我不记得有什么教室,不记得上过什么课,只记得早上出操人挺多的,很多很多的班级。“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各班比赛看谁的呼声高,步伐整齐。白天不是老师讲纪律,讲故事,就是班级之间赛歌,一班唱罢,另一个班接着唱。每个班都有一个打节拍的领头人,他如果高呼:“唱得好不好?”,众人会应声:“好!”领头人:“再来一个要不要?”“要!”“热烈鼓掌!”刚刚唱罢的班就不得不再唱一曲。如此热闹的挑战赛。倒也十分有趣。这是我第二次领略集体赛歌那鼓舞人心的非凡风采。
在锅场学校期间,我印象特别深的另一件事,就是同学们围成圈吃饭,除了喝汤以外,就是吃蒸红薯。老师监督着大家,都要带皮吃,不许剥掉红薯皮。谁剥了皮,都要受批评,还得捡起来吃下去。
正所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合班并校”的闹剧很快就破产了。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学校,换了一位李先生,开始了规范的教与学。这位女教师,虽然又黑又瘦小,可她嗓门大,又非常严厉,教学的水平也很高。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从我们这一届学生开始,接受的是新的汉语拼音教学,使我受益匪浅,为我后半生使用电脑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我上初小的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的夏天,我的家乡和其它一些地方一样,建起了食堂,吃饭不要钱,改变了妇女围着锅台转的传统习俗,这可是天大的稀罕事。
1958年大跃进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1959年夏季的小麦又获得了高产,粮食太多了。所以,在公共食堂里,无论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统统随便吃,撑破肚皮也不要钱。这下农民可高兴坏了,不但吃,还要拿,剩下的食物不少都扔掉了,浪费现象特别严重。
此时的“共产风”也刮起来了,大车大车的粮食都拉出去“支援”外地。存粮日渐减少,村干部还吹牛说没问题。上峰派人来检查存粮,村干部派人将麦秸装在囤子里,上面撒一层小麦,欺上瞒下。正所谓“乐极生悲”,在农历“年关”前后,我们大队各个食堂的食品相继告罄。苦日子开始了,每顿饭都是稀汤寡水,红薯面黑窝头也填不饱肚子了。
那时候,长兄夫妇外派到邻村公干,父亲被“拔钉子”运动清洗,拉到宛城批斗,二哥远在外地工作。每顿饭都由我和五弟去食堂领出,用一根木棍抬着一个小桶回去。由于父亲的原因,母亲,还有小妹,我们四个人的饭,不但被管理人员克扣,还要遭受他们的白眼。
小孩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时候感到饿一点也没什么,一疯玩起来什么都忘了,没感觉到有多苦,上学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大人可遭罪了。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偷偷地将食堂扔掉的坏红薯捡回家,还让我在放学后和玩伴们一起到地里去挖已经冻坏的红薯。有的已经发霉,可我们还是要千辛万苦地论起铁耙子刨呀刨的,找到一块烂红薯自然是欢天喜地,就像捡到了金子一样。
母亲将洗干净的坏红薯切成小丁儿,小块儿,放在石臼里捣碎,准备晚上做烧饼。白天谁家冒烟,村干部都会跑去搜查,所以,母亲只能在晚上偷偷地做。家里的铁锅早已被收走炼钢铁了,母亲将瓦盆架起来,将拍得很薄的饼子贴在瓦盆里,在下面用文火慢慢烧,将饼子翻过来翻过去,直到烤熟为止。被母亲叫醒的我们,躺在被窝里享受着母亲的劳动成果,那种幸福的感觉至今难忘。
苦日子一天一天地熬着,所幸的是,地里的豌豆苗也一天一天地长高了。这时候,我们这些虾兵蟹将派上大用场了。一放学,大家或结伙,或单干,偷偷地猫在豌豆地里,将割下来的美味带回家去享受。
村干部可成了我们的“夺命冤家”,他们将我们当毛贼来捉,一不小心就成了他们的俘虏。有一个外姓的小朋友,被一个“积极分子”捉住了,他让那个小孩跪在地上示众,还强迫小孩舔他拿来的树叶子上的鸡屎,实在是可恶至极!
说来也奇怪,那一年的豌豆苗割了一茬又长起来一茬,到后来还是一个丰收年。在收豌豆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做手脚,一边干活,一边将剥干净的豌豆粒偷偷地装在口袋里,带回家去。
我至今还以为,我们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是大集体的一份子,土地是我们的,产品也是我们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将自己家里能吃的东西拿来救命,怎么就成了“贼”,怎么就成了“偷”呢?
好在时间不长,上级将一部分粮食又返还了回来,解救饥民。大食堂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没有饿死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