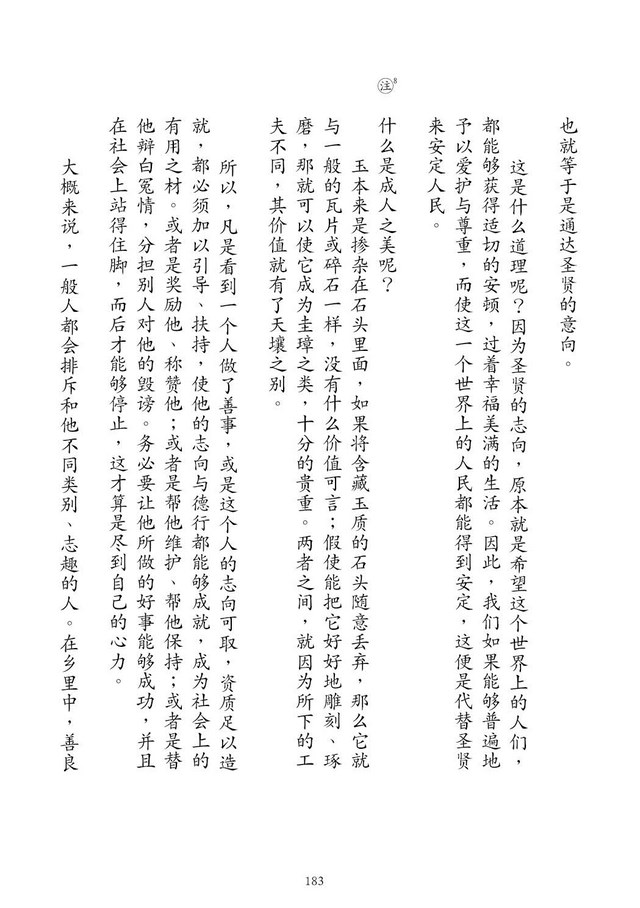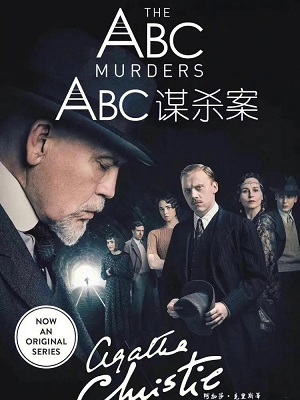王阳明《传习录》卷下 钱德洪录
【原文】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侯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
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对曰:“愿立‘必为圣人之志’。”
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
洪初闻时心若未服,听说到不觉悚汗。
【翻译】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王汝中和钱德洪在先生旁边侍坐。先生环顾他们说道:“你们这些人,学问没能有所长进,原因只在于还没有立志。”
李侯璧站起来回答说:“我也愿意立下志向。”
先生说:“不敢说你没有立志,只是立的恐怕不是‘必为圣人之志’。”
李侯璧答:“那我愿意立下‘必为圣人之志’。”
先生说:“如果你真的有了成为圣人的志向,在良知上就会用尽全力。如果良知上还存留有别的私心欲念,就不再是‘必为圣人之志’了。”
钱德洪刚开始听这段话时,心里还有所不服,现在又听到这话,就已经不觉警醒流汗。
【原文】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翻译】
先生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缔造了天地,生出了鬼神,真是无与伦比!如果人能够完完全全地恢复它,没有一点亏欠,自然就会手舞足蹈,天地间找不到什么快乐能够代替它。”
【原文】
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
答曰:“吾昔居滁①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②,方能察人病理。”
【注释】
①滁:指滁州(今安徽滁县)。
②医经折肱:语出《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意为久病可以成为良医。
【翻译】
一个朋友,他在静坐的时候有了一些领悟,便马上跑过来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我曾经住在滁州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注重在知识见闻上的辩论,对学问却没有帮助。因此,我便教他们静坐。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静坐中触及了良知的境界,短时间内很有效果。但是时间长了,有的人渐渐有了喜静厌动,陷入枯槁死灰的弊病;或者就致力于玄妙的见解,耸人听闻。因为这个原因,近来我都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了,无论你是到静处去体悟也好,或者在事情上磨炼也好,良知的本体本来就是没有动静的,这才是做学问的核心。我的这些话,从滁州到现在,我仔细琢磨过几番,只有‘致良知’三个字是没有弊病的。这就好比医生,要经历过多次折肱,才能了解人的病理。”
【原文】
一友问:“功夫欲得此知时时接续,一切应感处反觉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觉不见了。如何则可?”
先生曰:“此只认良知未真,尚有内外之闲。我这里功夫不由人急心,认得良知头恼是当,去朴实用功,自会透彻。到此便是内外两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翻译】
一个朋友问先生:“我想让‘致良知’的功夫持续不会间断,但一旦应对具体的事情,又觉得照管不过来。等到去事物上周旋的时候,又觉得看不见良知了。怎么办才好呢?”
先生说:“这只是你体认良知还不够真切,尚有个内外之分。我这致良知的功夫,不能心急。体认到了良知这个核心,然后在上面踏踏实实地用功,自然就能理解透彻。这样就会忘掉内外,又怎么会有心、事不统一的现象呢?”
【原文】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这个真机,如何得他充实光辉?若能透得时,不由你聪明知解接得来。须胸中渣滓浑化,不使有毫发沾带始得。”
【翻译】
先生又说:“做功夫,如果没有透彻地理解良知的关键,怎么能使它充实光辉呢?如果想要透彻地了解,不能仅凭你自己的聪明,还须净化心中的渣滓,不让它有丝毫的污染才行。”
【原文】
先生曰:“‘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
问:“如何道即是教?”
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翻译】
先生说:“‘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
有人问:“为什么‘道即是教’?”
先生回答说:“道就是良知,良知本来就是完完全全的。就像镜子一样,对的就还他个对,错的就还他个错。是非只需依照良心,就不会有不恰当的地方。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原文】
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①是说功夫否?”
先生曰:“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
【注释】
①“不睹”二句:语出《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翻译】
有人问先生:“《中庸》里的‘不睹不闻’,是指本体而言的吗?而‘戒慎恐惧’,是指功夫而言的吗?”
先生说:“这里首先应当明白本体原来就是‘不睹不闻’的,同样原来就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它并没有在‘不睹不闻’上还添加了一些什么。看得真切的时候,那也可以说‘戒慎戒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
【原文】
问:“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昼知夜的。”
又问:“人睡熟时,良知亦不知了。”
曰:“不知,何以一叫便应?”
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时?”
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①。今人不会宴息,夜来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魇寐。”
曰:“睡时功夫如何用?”
先生曰:“知昼即知夜矣。日间良知是顺应无滞的,夜间良知即是收敛凝一的,有梦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注释】
①上下与天地同流:语出《孟子·尽心上》。意为君子之心与天地同为一体。
【翻译】
有人问先生《易经》里的“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该如何理解。
先生说:“良知本来就是知道白天和黑夜的。”
那人又问:“但是人睡熟了的时候,良知不也就不知道了吗?”
先生说:“如果不知道了,那怎么一叫就会有反应呢?”
问:“如果良知是一直知道的,又怎么会有睡熟的时候呢?”
先生说:“到了夜晚便休息,这也是造化的规律。到了晚上,天地成为一片混沌,形体、颜色都消失了,人的眼睛和耳朵也没什么可以去看、去听,七窍都关闭了,这就是良知收敛凝聚的时候。天地一旦开启,万物显露,人的眼睛耳朵能够有所见闻了,感官再恢复正常,这就是良知发生作用的时候了。由此可见,人心与天地是一体的。所以,孟子才会说‘上下与天地同流’。今天的人到了夜晚不懂得休息,不是昏睡,就是噩梦连连。”
问:“睡觉的时候应该怎么用功呢?”
先生说:“白天知道如何用功,晚上也就知道如何用功了。白天,良知是顺应通畅的,夜间,良知则是收敛凝聚的。有梦就是先兆。”
先生又说:“良知在夜晚生发出来的时候,才是它真正的本体,因为它没有物欲混杂其中。学者如果在事物纷扰的时候,像‘夜气’生发时一样,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了。”
【原文】
先生曰:“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翻译】
先生说:“道家讲‘虚’,圣人岂能在‘虚’上再添加丝毫的‘实’?佛家讲‘无’,圣人又岂能在‘无’上再增添丝毫的‘有’?但是,道教说虚,是从养生的方面来说的;佛教说无,又是从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上来说的。他们在本体上又着了一些养生或脱离苦海的私意,便就不再是‘虚’和‘无’的本来面目了,在本体上有了阻碍。圣人则仅仅是还原良知的本色,不会夹带一丝一毫的私意。良知的‘虚’,就是上天的太虚;良知的‘无’,就是太虚的无。日、月、风、雷、山、川、百姓、物件等等,凡是有形貌颜色的事物,都是在太虚无形中发生运动的。从未成为过天的障碍。圣人仅仅是顺应良知的作用,这样,天地万物都在自己良知的范围之内,何曾有一物是超乎良知之外,而成为障碍的呢?”
【原文】
或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先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翻译】
有人问:“佛家也务求养心,但它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为什么呢?”
先生说:“我们儒家提倡养心,但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具体的事物,只是顺应天理自然,那就是功夫。而佛教却要全部断绝人间事物,把心看作是幻象,慢慢地便进入到虚无空寂中去了,他们与世间再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不能治理天下。”
【原文】
或问异端。
先生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翻译】
有人问异端。
先生说:“与愚夫愚妇相同的,便叫同德;与愚夫愚妇不同的,就称之为异端。”
【原文】
先生曰:“孟子不动心与告子不动心,所异只在毫厘间。告子只在不动心上着功,孟子便直从此心原不动处分晓。心之本体,原是不动的。只为所行有不合义,便动了。孟子不论心之动与不动,只是‘集义’。所行无不是义,此心自然无可动处。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动,便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挠了,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集义’工夫,自是养得充满,并无馁歉,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此便是浩然之气。”
又曰:“告子病源,从性无善无不善上见来。性无善无不善,虽如此说,亦无大差。但告子执定看了,便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在内。有善有恶,又在物感上看,便有个物在外。却做两边看了,便会差。无善无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时,只此一句便尽了,更无有内外之间。告子见一个性在内,见一个物在外,便见他于性有未透彻处。”
【翻译】
先生说:“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告子是在不动心上用功夫,而孟子却直接从自己的心原本不动的地方去用功。心的本体,原来就是不动的,只是因为行为有不合义理的地方,便动了。孟子不去管心动或者不动,只是‘集义’。如果自己的行为无一不合乎道义,自己的心自然没有可动之处。如果像告子那样,只要求自己的心不动,就是紧扣住了自己的心,也反倒会把它生生不息的根源阻挠了,这不仅仅是徒然无用了,而且又对它有所损害。孟子‘集义’的功夫,自然可以将心修养得充沛,没有缺欠,让它自然能够纵横自在,活泼泼的。这就是所谓的‘浩然之气’。”
先生又说:“告子的病根,在于他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性无善无不善,虽然这种观点也没有大的差错,但告子偏执地把它看成呆板的了,就会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夹在其间。有善有恶,又是从外物的感受上来看,就有个物在心外了,这样就是分成两边看了,就会有差错出现。无善无不善,性本就是如此。等领悟到了这里,这一句便能说尽了,再不会有内外之分。告子看到了一个性在心里,又看到了一个物在心外,可见他对性,还有了解不透彻的地方。”
【原文】
朱本思①问:“人有虚灵,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类,亦有良知否?”
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注释】
①朱本思: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靖江(今属江苏)人,曾入仕,学主道家。
【翻译】
朱本思问:“人有虚空的灵魂,才有良知。但是像草木瓦石等等,是不是也会有良知呢?”
先生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果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就不是草木瓦石了。岂止是草木瓦石是这样,天地间如果没有人的良知,也不会是天地了。天地万物和人原本就是一体的。它最精妙的发窍的地方,就是人心的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和人原来都是一体的,因此五谷禽兽可以供养人类,而药物石针,则可以治疗疾病。只因为他们同属一气,所以能够相通。”
【原文】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翻译】
先生游览南镇的时候,一个朋友指着岩石里的花树问先生:“天下没有心外之物,那么,就像这棵花树,它在深山中自己盛开自己凋零,跟我们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说:“你没有看到这树花的时候,它是与你的心一同归于寂静的。而你来看这树花的时候,这花的颜色一下子就明白起来了。由此可知,这树花并非存在在你的心外。”
【原文】
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①?”
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心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②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皆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个条理,便谓之信。”
【注释】
①厚薄:语出《大学》“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②燕:同“宴”。
【翻译】
有人问道:“您认为人与物同为一体,那为何《大学》又说‘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呢?”
先生说:“只因为道理本身就分厚薄,比如人的身体,它是一体的,用手脚去保护头和眼睛,难道是非要薄待手脚?理当如此而已。同样喜爱动物与草木,拿草木去饲养禽兽,于心何忍?同样热爱的人与禽兽,却宰杀了禽兽去供养父母、祭祀和招待宾客,又怎么忍心呢?至亲的人与路人也同样对他们心满仁爱,但是如果只有一箪食一豆羹,吃了便能活命,不吃便会死,无法保全两个人,就会救至亲的人而不是过路的人,这又怎么可能忍心?道理本该如此而已。说到我们自身和至亲的人,更不能分清楚彼此厚薄,大概‘仁民爱物’都出自于心,从心里生发出来。这里都能忍心,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了。《大学》里说的厚薄,是良知上自然而有顺序的,不能够逾越,这就称为‘义’;而顺应了这个秩序,就叫作‘礼’;懂得这个顺序,就叫作‘智’;始终保持这个顺序,就叫作‘信’。”
【原文】
又曰:“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翻译】
先生又说:“眼睛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颜色作为本体;耳朵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声音作为本体;鼻子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气味作为本体;嘴巴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味道作为本体;心也没有本体,它以天地万物感应到的是非作为本体。”
【原文】
问“夭寿不贰”。
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翻译】
有人向先生请教“夭寿不贰”。
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对于一切声色、利益、嗜好,都能摆脱干净。但是只要还有一丝一毫在意生死的念头牵累着,便会有和本体不能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人有在意生死的念头,是生命本身带来的,所以不容易去掉。如果在这里都能看破、想透彻,心的全部本体才能自由没有阻碍,这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原文】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
是友愧谢。
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
在坐者皆悚然。
【翻译】
一个朋友问先生:“想在静坐的时候,把好名、好色、好财的病根一一搜寻出来,清除干净,只怕也是剜肉补疮吧?”
先生严肃地说:“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的可以清除病根的,还是有大作用的。即使过了十几年了,也还能产生效用。如果你不用,就暂且把它存起来,别随便糟蹋了我的方子。”
于是朋友满怀愧疚地道了歉。
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说:“想来也不能怪你,一定是我的门人里那些略微懂一些意思的人告诉你的,反倒耽误了你的理解。”
于是,在座的人都觉得汗颜。
【原文】
一友问功夫不切。
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
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
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
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①提起。一日,其徒将其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又何可提得?”
少间,又一友请问功夫切要。
先生旁顾曰:“我尘尾安在?”
一时在坐者皆跃然。
【注释】
①尘尾:拂尘。古人用动物的尾毛或麻等制作拂尘。
【翻译】
一个朋友向先生请教功夫不真切该怎么办。
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我已经用一句话包括尽了。现在怎么越说越远,全都不着根基了呢?”
朋友说:“您的致良知的学说,我们大概都已经听明白了,然而也还需要您再讲明一些。”
先生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致良知,又还有什么可以再说明的呢?良知本来就是清楚明白的,只需切实用功就行了。如果不愿切实地用功,只会在语言上越说越糊涂。”
朋友说:“正是要麻烦您把致良知的功夫说明白。”
先生说:“这也需要你自己去探寻,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告诉你。从前有一个禅师,当别人前来问法,他只会把尘尾提起来。有一天,他的学生把他的尘尾藏了,想试试他没有尘尾怎么办。禅师找不到尘尾了,便只空着手把手抬起来。我的这个良知,就是用来解释问题的尘尾,没有这个,我有什么能提起来的呢?”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朋友来请教功夫的要点。
先生四顾旁边的学生们说:“我的尘尾在哪儿?”
于是,在座的人都哄然而笑。
【原文】
或问“至诚前知”①。
先生曰:“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邵子②必于前知,终是利害心未尽处。”
【注释】
①至诚前知:语出《中庸》“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②邵子:邵雍(1011~1077),字尧夫,谥康节,北宋哲学家,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屡授官不赴,后居洛阳,与司马光从游甚密,著有《皇极经世》等。
【翻译】
有人就《中庸》里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一句请教先生。
先生说:“诚,就是实理,也只是良知。实理的奇妙作用就是神;而实理萌发的地方,就是‘几’;具备了诚、神、几,就可以称为圣人。圣人并不重视预知未来。当祸福来临时,虽然他们是圣人,也难以避免。圣人只是明白‘几’,遇事能够变通罢了。良知没有前后之分,只要明白现在的‘几’,就能以一当百了。如果一定说要有‘前知’的心,那就成了私心,有趋利避害的意思。邵雍先生执着于‘前知’,恐怕还是他趋利避害的私心没有尽除的原因。”
【原文】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翻译】
先生说:“什么都知道但又什么都知道,本体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好像是太阳,它未曾有意去照耀万物,但又很自然地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被太阳照射到的。无照无不照,就是太阳的本体。良知本来什么都不知道,如今却要让它有知;本来良知是无所不知的,但现在却又怀疑它会有所不知。只是因为还不够信任良知罢了。”
【原文】
先生曰:“‘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
【翻译】
先生说:“《中庸》里说‘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以前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玄妙,如今再看才知道聪明睿智,原本就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耳朵原本就聪敏,眼睛原本就明亮,心思原来就睿智。圣人只是能做到一件事而已,那件能做到的事就是致良知。一般人做不到,也只是这个致良知。多么简单明了啊!”
【原文】
问:“孔子所谓‘远虑’①,周公‘夜以继日’②,与将迎不同,何如?”
先生曰:“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
【注释】
①远虑: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②夜以继日:语出《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翻译】
有人问先生孔子所说的“远虑”和周公说的“夜以继日”与刻意逢迎有何不同之处。
先生说:“‘远虑’并非指的是茫茫然地去思虑,只是要存养天理。天理在人们的心里,贯穿古今,无始无终。天理就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为了致良知。良知越想就越精明,如果不精深地思考,而只是随意地去应付,良知便会变得粗浅。如果以为远虑就是在事情上不着边际地思考,就难免会有毁誉、得失、人欲等掺杂其中,就成了着意逢迎了。周公夜以继日地思考,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明白了这一点,境界就自然与刻意地逢迎有区别了。”
【原文】
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①,朱子作效验说②,如何?”
先生曰:“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③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④,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无怨,于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注释】
①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语出《论语·颜渊》。
②“朱子”句:朱熹《论语集注·颜渊》“极言其效之甚远而至大也”。
③八荒皆在我闼:宋人吕大临语,见《宋元学案》卷三十一。闼(tà),门楼上的小屋。
④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语出《论语·颜渊》。
【翻译】
有人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句,朱熹先生认为它是从效验上说的。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圣贤只是一个克己的学问。重视自己所下的功夫而不会这么重视效验。仁者与万物同为一体。如果不能做到与万物同体,只因为自己的私欲没有完全忘记。获得了全部的仁的本体,天下便全都归入到我的仁里面了,也就是‘八荒皆在我闼’的意思。天下能做到仁,那自己的仁也就在其中了。‘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仅仅是自己没有怨恨,就像‘不怨天,不尤人’的意思。家庭、国家都没有怨恨,自己当然也就在其中了。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该重视的地方。”
【原文】
问:“孟子‘巧力圣智’①之说,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②何如?”
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③而极,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注释】
①巧力圣智:语出《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全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不力也;其中,非不力也。’”②“三子”句:语出朱熹《孟子集注·万章下》:“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三子,指伯夷、伊尹、柳下惠。
③柳下惠:即展禽,名获,字禽,春秋时鲁国大夫,食邑在柳下,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
【翻译】
有人问:“孟子主张‘巧力圣智’的说法,朱熹先生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这样说对吗?”
先生说:“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不仅有力,而且也还有巧,巧与力实际上并非两回事。巧也只在用力的地方,有力却不巧,也只不过是徒然,白费力气。用射箭做比喻的话,他们三个人里,一个能够步行射箭,一个能够骑马射箭,一个能够远程射箭。只要他们都能射到靶子那里,便都能叫作有力;只要能正中靶心,便都能叫作巧。但是,步行射箭的不能够骑马射箭,骑马射箭的又不能远程射箭,他们三个各有所长,才力各有不同的地方。而孔子则是身兼三长,然而,孔子的‘和’最多也只能达到柳下惠的水平,而‘清’最多能够达到伯夷的水平,‘任’也最多只能达到伊尹的水平,未曾再添加什么了。如果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他们的力加在一起反倒能超过孔子了。巧、力只是为了阐明圣、智的含义。如果认识到了圣、智的本体,自然就能够明了了。”
【原文】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违’①,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②,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
“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霆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亦是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
【注释】
①“先天”句:语出《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②“后天”句:同上。
【翻译】
先生说:“‘先天而天弗违’,天就是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就是天。”
“良知仅是辨别是非的心,而是非仅是个好恶。明白了好恶,也就是穷尽了是非;而明白了是非,也就穷尽了万事万物的变化。”
又说:“‘是非’两个字是大规矩,而灵巧的地方就在乎于个人了。”
“圣人的良知,就像青天里的白日;而贤人的良知就像有浮云的天空里的太阳;愚人的良知则像阴霾天气里的太阳。虽然他们的明亮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一样能够分辨黑白的,即使在昏暗的夜里,也能够影影绰绰地辨别出黑白来,因为太阳的余光仍旧没有完全消失。在困境中学习的功夫,也只是从这一点光明的地方去精细鉴察罢了。”
【原文】
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
【翻译】
有人问先生:“良知就像太阳,而人的私欲就像是浮云。浮云虽然能够遮蔽太阳,然而也是气候里本就具有的。莫非人的私欲也是人心本就具有的吗?”
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就是所谓的‘七情’。这七种感情都是人心本来就具有的,但我们需要把良知体认清楚。就比如太阳光,也不能指定一个方向照射。只要有一丝空隙,都会是太阳光的所在之处,即使布满了乌云,只要天地间还能依稀辨别形色,也是阳光不会磨灭的表现。不能因为浮云遮蔽了太阳,就强求天空不再产生浮云。上面所说的七种情感顺其自然地运行,都是良知在发生作用,不能认为它们有善、恶的区别,更不能对它们太执着。如果执着于这七情,就成了‘欲’,都是良知的阻碍。然而刚开始执着的时候,良知自然能够发觉出来,发觉后便会马上清除这一阻碍,恢复它的本体。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够看透,才是简易透彻的功夫。”
【原文】
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的,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翻译】
有人问:“圣人生知安行是天生就有的,这话对吗?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功夫呢?”
先生说:“‘知’‘行’二字,就是功夫,只是这功夫有深浅难易的区别罢了。良知本来就是精明的,比如说孝敬父母,那些生知安行的人,只不过是依照自己的良知,切切实实地去尽孝而已;而那些学知利行的人,则需要时时反省察觉,努力地去依照良知去尽孝而已;至于那些困知勉行的人,他们受到的蒙蔽禁锢已经非常深,虽然需要依照良知去尽孝,但是又被私欲阻碍,因此不能够做到尽孝。这就需要他们用别人一百倍、一千倍的功夫,才能够做到依照良知去尽孝。圣人虽然是生知安行的,但他们在内心里也不敢肯定自己,所以愿意去做困知勉行的功夫。那些困知勉行的人,却时刻想着去做生知安行的事,这怎么可能成功呢?”
【原文】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
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①,周公系爻②,孔子赞《易》③,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注释】
①彖(tuàn):《易传》中说明各卦基本观念的篇名。分《上彖》《下彖》两篇。
②爻(yáo):指爻辞。说明《周易》六十四卦中各爻要义的文辞。每卦六爻,每爻有爻题和爻辞。爻题都是两个字:一个字表示爻的性质,阳爻用“九”,阴爻用“六”;另一个字表示爻的次序,自下而上,为初、二、三、四、五上。如乾卦初爻:“初九,潜龙勿用。”“初九”是爻题,“潜龙勿用”是爻辞。
③《易》:指《易传》。是对《易经》所做的各种解释。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亦称《十翼》。相传为孔子作。据近人研究,大抵系战国或秦汉之际的作品。
【翻译】
有人问先生道:“快乐才是心的本体,但是遭遇到了大的变故的时候,痛心哭泣,不知道这时本体的快乐是不是还存在?”
先生说:“必须是痛哭一番之后才会感觉快乐,如果没有哭,也就不会觉得快乐了。虽然是在哭,自己的内心却得到了安慰,这也是快乐啊。快乐的本体未曾有什么变化的。”
又问:“良知唯有一个而已。但是文王作象辞,周公作爻辞,孔子写《十翼》,为何他们看到的理都分别有所不同呢?”
先生说:“圣人岂会拘泥于死旧的模式呢?只要都同样是出自于良知,即便他们各自立说又何妨呢?就以一园翠竹打比,只要枝节相差不大,就是大同。如果一定要拘泥于每一根的枝节都一模一样,那就并非是自然的神妙造化了。你们这些人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相同,就不妨各自间有些差异存在了。你们这些人如果不愿意用功,就连竹笋都还没有生长出来,到哪里去谈论枝节呢?”
【原文】
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
柴鸣治入问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
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间大慈的父。”
鸣治愕然请问。
先生日:“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时,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个慈父。”
【翻译】
乡下有两父子要打官司,请先生裁决。侍从们想要阻止他们,先生听说了之后,开导的话还没有说完呢,父子两个就已经就抱头恸哭,然后相拥着离开了。
柴鸣治便进来问道:“先生的什么话让他们这么快速地感动悔悟了?”
先生说:“我跟他们说舜是世界上大不孝的儿子,而瞽瞍则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
鸣治惊讶地问先生为什么。
先生说:“舜常常觉得自己大不孝,所以他才能尽孝;而瞽瞍常常自以为自己是很慈爱,所以他不能做到慈爱。瞽瞍只记得舜是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就不曾取悦过自己呢?他不明白自己的心已经被后妻改变了,仍然觉得自己是慈爱的,因此就越发不能做到对舜慈爱。而舜则只想着从小开始,父亲照顾自己的时候是如何如何地疼爱自己,可是现在却不疼爱了,恐怕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孝,所以每天都在想自己没有做到尽孝的地方,所以他就越发能尽孝了。等到瞽瞍高兴的时候,也不过是恢复了心里慈爱的本体。所以,后人都把舜当成是古今的大孝子,而认为瞽瞍则是个慈爱的父亲。”
【原文】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①。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注释】
①“孔子”之句: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翻译】
先生说:“有农夫前来找先生请教,孔子也不会事先准备好了知识来回答他。孔子的内心也是空无一物的。但是他可以帮助农夫分析他心里明白的是非,替他做出一个决策,这样农夫的心便比较开朗了。农夫知道自己的是非,便是他原本就有的天然准则。虽然圣人聪明,但对这种准则也无法有丝毫的增减。只是他们不够自信,所以孔子给他们进行了剖析之后,他们心里的是非曲直就会显现无余了。如果孔子和他们说话时,还保留有一些知识在他们心里,就不能够尽显他们的良知了,而道体也就分为两处了。”
【原文】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奸’①,本注说象已进于义,不至大为奸恶②。舜征庸后,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
【注释】
①烝烝乂,不格奸:语出《尚书·尧典》“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瞽子,指舜。象,舜之弟。烝,进。乂(yì),治理,安定。格,至。
②“本注”二句:汉代孔安国传注说:“谐,和。悉,进也。言能以至孝和谐顽象昏傲,使进进以善白治,不至于奸恶。”
【翻译】
先生说:“《尚书》中的‘烝烝乂,不格奸’,孔安国的本注认为,象已经慢慢上进到了道义的境界,而不至于去做大奸大恶的事。舜被尧征召之后,象仍然整天想要把舜杀死,这是何等奸邪的事?而舜则只是学习自己修养、自我克治,不直接去纠正他的奸恶,而是用自己的克制来感化他。文过饰非,用以掩盖自己的奸恶,这是恶人们的常态;如果去指责他的是非,反倒会激发他的恶性。舜最初让象起念杀害自己,也是因为想让象变好的心意太过急切,这就是舜的过错。等事情过了之后,才明白原来功夫只在自己,不能责备别人,因此最后能有‘克谐’的结局。这就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地方。古人的言论,都是自己经历过的,所以说得特别确切。而流传到了后代,歪曲变通,仍然合乎人情。如果不是自己曾经经历过,又怎能体会到古人的苦心呢?”
【原文】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
未达,请问。先生曰:“‘韶’之九成①,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曰:“洪要求元声②不可得,恐于古乐亦难复。”
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
对曰:“古人制管候气,恐是求元声之法。”
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元声只在你心上求。”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曰:“古人制候气法,是意何取?”
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后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必须定至日。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又何处取得准来?”
【注释】
①九成:九乐章。下文“九变”即九成。“韶”为舜的乐,“武”为武王的乐。
②元声:古代律制,以黄钟管发出的音为十二律所依据的基准音。故称元声。
【翻译】
先生说:“古乐不流行已经很久了。现在戏曲倒有些与古乐能意思相近。”
德洪不懂,便向先生请教。先生说:“《韶》乐里的九章,都是舜的一个戏本;而《武》乐的九变,是武王的一个戏本。圣人一辈子的事迹,都被记录在戏曲当中了。所以,德行高尚的人听了,就明白他是尽善尽美的还是尽美而未尽善的。后代人写作乐曲,只作一些陈词滥调,跟教化民风全然没有关系,这怎么能用来感化百姓呢,怎么能让风俗淳善呢?现在要让民俗返璞归真,把当今的剧本里的妖淫词调都去删除掉,只利用起当中忠臣孝子的故事,让愚昧无知的百姓们都懂得其中的道理。在不知不觉中感化他们的良知,这样对风化才会有好处。同时,古乐也就逐渐恢复本来面貌了。”
德洪又说:“我连找基准音都找不到,只怕古代的音乐也很难得以复兴吧。”
先生问:“你觉得基准音应该到哪里去寻找?”
德洪回答说:“古人制测管来测量气候的变化,这应该是寻找元声的办法。”
先生说:“假若要从葭灰黍粒中寻找元声,好比就是水底捞月,这怎么能成功呢?元声只能去内心寻找。”
德洪问:“在心上如何寻找呢?”
先生说:“古人大治天下,首先需要培养人们心平气和,然后才是作礼乐教化。就像你吟诵诗歌的时候,心里很平和,听的人才会自然愉快,激发起兴趣。这里只是元声的开始罢了。《尚书》说‘诗言志’,‘志’,就是音乐的根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根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求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就是制作音律的根本。又何苦要到心外去寻求呢?”
德洪又问问:“那么,古人用律管测量气候的方法,根据又在哪里呢?”
先生说:“古人具备了中和的本体之后,才去作乐。而心体的中和,原本就是与天地间的气相相符合的。候天地之气,与凤凰的鸣叫相谐,不过是为了验证我的气是不是真的中和,这是制定了音律之后的事情了,不一定要依据这个才能制定音律。如今通过律管来候气,必须确定在冬至这天,但是,当到了冬至子时,只恐又不准确,又到哪里去找标准呢?”
【原文】
先生曰:“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翻译】
先生说:“学问也需要别人的点化,但总不像自己理解觉悟的那样一了百当,否则的话,即使别人点化再多,也没有作用。”
【原文】
“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却倒做了。”
【翻译】
“孔子的气魄很大,凡是帝王的伟业,他无一不会领悟到,但也都只是从他自己的心上生发来的。就像大树,它有许多的枝叶,但也都只是从根本上培养功夫,所以能长成这样,而不是从枝叶上做的功夫。学者们向孔子学习,却不学着在心上用功,只是心急火燎地去学习他的大气魄,这是把功夫做反了嘛。”
【原文】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①,其流必归于文过。”
【注释】
①甑(zēng):古代炊具。
【翻译】
“人犯了过错,大多会在那个过错上用功。这就像是补破了的饭甑,必然会有文过饰非的弊病。”
【原文】
“今人于吃饭时,虽无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翻译】
“现在的人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没有其他事情摆在眼前,他们的心仍然忧虑不止,只因为自己的心忙碌惯了,所以收都收不住。”
【原文】
“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
【翻译】
“琴瑟与书籍,这两者学者们缺一不可,因为有了事情做,心就不得放纵了。”
【原文】
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
崇一曰:“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
【翻译】
先生感叹说:“世间懂得学问的人,就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做不到‘善与人同’。”
崇一说:“这个毛病实际上只是个好高骛远,不能舍己从人罢了。”
【原文】
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
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翻译】
问:“良知原本是中和的,却怎么会有过和不及的现象呢?”
先生说:“知道了过和不及的地方,就是中和了。”
【原文】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①
【注释】
①所恶于上,毋以使下:语出《大学》。意为上级的无礼让我讨厌,将心比心,我对下级不要无礼。
【翻译】
先生说:“《大学》里说的‘所恶于上’,就是良知;‘毋以使下’,就是致知。”
【原文】
先生曰:“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①,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注释】
①肯綮(qìng):筋骨结合的地方,比喻要害处。
【翻译】
先生说:“苏秦、张仪的智谋,也是圣人的资质。后代的许多事业文章和豪杰名家,都只学到了张仪、苏秦的旧智慧。而苏秦、张仪的学术里,善于揣测人情,没有哪点不是说中了别人的要害,所以说他们的学问真是难以穷尽。张仪、苏秦也能看到良知的妙用处,只是没有把它们用在善上面。”
【原文】
或问“未发”“已发”。
先生曰:“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
问曰:“‘未发’未尝不和。‘已发’未尝不中。譬如钟声,未扣不付谓无,即扣不付谓有。毕竟有个扣与不扣,何如?”
先生曰:“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即扣时也只是寂天默地。”
【翻译】
有人请教“未发”和“已发”的问题。
先生说:“只因为后世儒生们已经把‘未发’和‘已发’分开来说了,所以,我只能说个没有未发、已发,让人们自己思考明白。因为如果我说有已发、未发,听的人就还是会沦落到后世儒生们的见解当中去。如果真的明白了根本没有什么未发、已发,再说有未发、已发,那也无妨。因为原本就是有未发和已发存在的。”
又问:“未发,未尝不平和;已发,也未尝不中正。好比敲钟的声音,没有敲击的时候不能说它就不存在,而敲击了之后也不能说就有了。毕竟还是有个敲和没敲的区别。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没有敲的时候原来也是惊天动地的,敲打了之后,也同样是寂静的天地。”
【原文】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
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①,是从流弊上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
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
先生曰:“然。”
【注释】
①荀子性恶之说:荀子主张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立。《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翻译】
有人问先生:“古人谈论人性时,各有不同的说法,应该把哪种当成定论呢?”
先生说:“人性没有固定的体,因此关于它的论述也没有定论。有从它的本体上谈论的,有从它的作用上说的,有从它的源头上谈论的,有从它的流弊上说的。总而言之,人性唯有一个,只是人们对它的见识有浅有深罢了。如果你执着在哪一个方面,就会出错。人性的本体,原来就是无善无恶的。而它的运用与流弊,也是有善有恶的。就好比眼睛,有喜悦时的眼睛;有发怒时的眼睛;直视的时候,就是在看的眼睛;偷看时,就是窥视的眼睛,等等。总而言之,还只是这一双眼睛。如果人们看见了发怒时的眼睛,就说从没有过喜悦的眼睛;看到直视时的眼睛,就说没有看到过偷窥的眼睛。这都是执着的表现,是错误的。孟子说人性,是直接从源头上来说的,也只不是说了个大概;荀子‘性恶’之说,则是从它的流弊上说的,也不能完全说他不对,只是不够精全罢了。但是普通人却失去了心的本体。”
问的人说道:“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求人们在源头要弄明白;而荀子则是从流弊上说性,功夫都用在末流上,以求费力补救。”
先生说:“是这样的。”
【原文】
先生曰:“用功到精处,愈著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著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
“杨慈湖①不为无见,又著在无声无臭上见了。”
【注释】
①杨慈湖:杨简(1140~1226),字敬仲,号慈湖,浙江慈溪人。陆九渊弟子,南宋哲学家,官至宝漠阁学士。
【翻译】
先生说:“功夫越到了精妙的地方,越不能用语言表达,说理就越困难。如果执意于在精妙的地方,全体的功夫反倒会被拘泥了。”
又说:“杨慈湖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他又执意于无声无臭上罢了。”
【原文】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岩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
【翻译】
“人在一天当中,就把古今的世界都经历了一遍,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当夜气清明的时候,没有视觉和听觉,也没有思虑与行动,心怀平定淡然,这就是羲皇的世界;而清晨的时候,神清气朗,气息明朗,庄严肃穆,就是尧、舜时代的样子;到了中午之前,人们用礼仪交往,气度井然,就是夏、商、周三代时的状况;而到了正午之后,神气渐昏,人事往来繁乱,那就是春秋战国时的世界。待到渐渐进入了昏夜,万物都安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灭的世界了。学者只要信得过良知,不被气扰乱,就能时时都做个羲皇时代的人。”
【原文】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叹先生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众;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
诸友请问。
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方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翻译】
薛侃、邹守益、马子莘、王汝止在先生身边侍坐,众人慨叹先生自征伐平定藩王以后,天下的诋毁和非议也与日俱增,于是先生让他们各自谈一下当中的缘故。有的说,先生的功业权势日益显赫,因此天下人有所嫉妒的一天天变多了;也有的说先生的学说日益昌明于天下,所以替宋儒争是非对错的人也就日益变多了;有的说自打正德九年(1514)以后,志同道合的人当中相信先生学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四方来的排阻的人也更加卖力了。
先生说:“你们各位所说的原因,当然也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方面,大家还没有提到。”
各位都向先生询问。
先生说:“我在来南京以前,尚有一些当老好人的想法。但是现在,我确切地明白了良知的是非,只管去行动,再不用有什么隐藏。现在我才真正终于有了敢作敢为的胸襟。即便天下人全都说我言行不符,那也毫无关系了。”
薛侃站出来说:“有这样的信念,才是圣人真正的血脉!”
【原文】
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盖汝止圭角未融,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
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涂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见之?”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惧。
【翻译】
先生点化学生的时候,往往一句话,便能感人至深。
有一天,王汝止出游回来。先生问他说:“你在外面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呢?”王汝止回答道:“我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先生说:“你看到满街人都是圣人的话,满街的人反过来看你也是圣人。”
又有一天,董萝石也出游回来。他见到先生便说:“我今天看到一件奇怪的事。”先生说:“什么奇怪的事?”他回答说:“我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说:“这也只是寻常事情而已,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大概王汝止的棱角还没有磨去,而董萝石却早有省悟。所以虽然他们的问题相同,先生的回答却是不同的,先生是依照他们的话来启发他们。
钱德洪、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丙戌年(1526)的时候参加会试回来的路上,谈到先生的学说,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先生说:“你们扛着一个圣人去给别人讲学,别人看到圣人来了,早就吓跑了,这还怎么讲?必须做个愚夫愚妇,才能够去给别人讲学。”
钱德洪又说,现在要看出人品的高低是很容易的。先生说:“何以见得?”
钱洪答道:“先生您就像是泰山,摆在眼前,只有那些有眼无珠的人才会不知道敬仰。”
先生说:“但是泰山又比不上平地广阔,平地怎么发现呢?”先生这一句话,说破了我们终年好高骛远的毛病,在座的人无不有所警惧。
【原文】
癸未春,邹谦之来越问学,居数日,先生送别于浮峰。是夕与希渊诸友移舟宿延寿寺,秉烛夜坐,先生慨怅不已,曰:“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
一友问曰:“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
【翻译】
明嘉靖二年(1523)春天,邹谦之到浙江来求学。住了几天,先生到浮峰为他送行。晚上的时候,先生与希渊等几位朋友,留宿在延寿寺,众人秉烛夜坐,先生感叹惆怅不已,说:“江水滔滔,烟柳蒙蒙,谦之瞬间就到了百里之外的地方了。”
一位朋友便问:“为什么先生对谦之的思念这么深切呢?”先生说:“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这样的人,和谦之非常接近啊!”
【原文】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德洪曰:“此意如何?”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
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翻译】
明嘉靖六年(1527)九月,先生重新被起用,再次奉命讨伐思恩(今广西武鸣县北)和田州(今广西田阳县北)。出征前,钱德洪和王汝中讨论先生的学问。汝中便引用先生的教诲说:“无善无恶才是心之体,而有善有恶则是意的作用,知道善恶是良知,而为善去恶则叫格物。”
德洪说:“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
汝中说:“这句话恐怕还只是个引子,没有说全。如果说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也应当是无善无恶的,知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物。如果说意有善恶之分,那还是因为心体终究是有善恶之分存在的。”
德洪说:“心的本体是天生的性,本来就是无分善恶的。但是,人有受习性沾染的心,所以意念就有了善和恶。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正是恢复心体的功夫。若果意本来就没有善恶,那么,谈功夫还有什么用呢?”
当晚,德洪和汝中在天泉桥坐在先生旁边侍坐,各人说了自己的看法,请先生来评判一下。
先生说:“现在我将要走了,正要给你们来讲明白这一点。你们两位的见解,恰好能够相互补充利用,不能够偏执于一方。我这里引导人,原本就只有两种:资质高的人,便直接让他们从本源上去体悟,而人的本体原本就是晶莹无滞的,原本就是未发之中的。所以资质高的人,只要稍稍去体悟本心就是功夫了。人和己、内与外一齐都悟透了。而资质较差的另一种人,他们的心难免受到了沾染,本体便被蒙蔽了,因此便暂且教他们在意念上去踏实地用功。等行善去恶的功夫纯熟之后,渣滓清除干净之后,人的本体也就自然明亮清洁了。汝中的见解,是我用来开导聪慧的人的说法;而德洪的见解,则是用来教导资质较差的人的说法。如果你们两位能够互相补充借用,那么,资质中等的人就都能够被引入正途了。而如果你们两位都偏执一个方面,那么眼下就会误导别人,对圣道也不能够穷尽。”
先生接着说:“以后与朋友们一起讲学,万万不能抛弃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要根据我这句话,因人而教,自然会没有问题的,这本来就是贯通上下的工夫。资质高的人,世上很难遇到了。能将本体功夫全都参透,这是连颜回、程颢也不敢自认的,又怎么敢随便对别人寄予这样的期望?人心受到了习性的沾染,如果不教导他在良知上切实地去下为善去恶的功夫,只去凭空想一个本体,对所有的事都不去切实地应对,只会养成虚空静寂的毛病。这个毛病可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不能不早跟你们说清楚。”
这一天,钱德洪和王汝中又有所省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