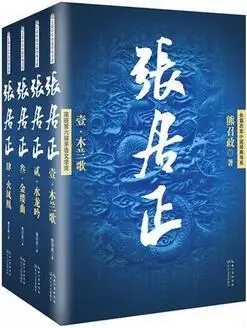王阳明《传习录》卷下 黄以方录
【原文】
黄以方问:“‘博学于文’为随事学存此天理,然则谓‘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其说似不相合。”
先生曰:“《诗》《书》六艺皆是天理之发见,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诗》《书》六艺,皆所以学存此天理也,不特发见于事为者方为文耳。‘馀力学文’亦只‘博学于文’中事。”
【翻译】
黄以方(黄直)问先生:“您认为‘博学于文’是要在遇上的事情上面去学习存养天理,但是这与孔子所说的‘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似乎并不一致。”
先生说:“《诗》《书》等六经都是天理的表现,文字都包含在里面。仔细考究《诗》《书》等六经,它们都是为了存此天理,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事情上,便是文。孔子说的‘馀力学文’,也是‘博学于文’里的一部分。”
【原文】
或问“学而不思”①二句。
曰:“此亦有为而言,其实思即学也。学有所疑,便须思之。‘思而不学’者,盖有此等人,只悬空去思,要想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实用其力,以学存此天理。思学作两事做,故有‘罔’与‘殆’之病。其实思只是思其所学,原非两事也。”
【注释】
①学而不思: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翻译】
有人就“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句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这两句话是有所指的。其实,思考就是学习,学习时有了疑问就需要思考。‘思而不学’的人也有,他们只是凭空去想,想要得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切实地用功,学习存此天理。把思考和学习分而为二,所以就有‘罔’和‘殆’的弊端。其实,思也只是思考他学到的东西,原本就不是两回事。”
【原文】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大学》之所谓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
“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意之所发,既无不诚,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诚意’。功夫到,‘诚意’始有着处。”
“然‘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更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如何得意诚?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
“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如意在于为善,便就这件事上去为,意在于去恶,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去恶,固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为善,则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归于正也。如此,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而意之所发,好善去恶,无有不诚矣。‘诚意’功夫实下手处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
【翻译】
先生说:“程颐先生说,格物就是穷尽天下的物。天下万物怎么可能完全穷尽?只说‘一草一木亦皆有理’,现在你怎么去草木上一一地去‘格’?而且纵使格尽了草木,又怎么让它反过来‘诚’自己的意呢?我觉得‘格’就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的意思。《大学》里所说的‘身’,就是耳、目、口、鼻及四肢。想要‘修身’,就是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非礼勿动。想要‘修身’,身上怎么能用到功夫呢?心,是身的主宰。虽然是眼睛在看,但让它看的是心;虽然是耳朵在听,但让耳朵听的是心;口与四肢虽然能说能动,但让口与四肢说和动的是心。所以,想要修身,主要在于自己的心体,让它常常廓然大公,没有不中正的地方。心一旦中正了,眼睛就自然能够非礼勿视;耳朵就能非礼勿听;口和四肢就不会有不合于礼的言行。这就是《大学》中的‘修身在于正心’。”
“然而,至善就是心的本体,心的本体怎会有不善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哪个地方能用功呢?所以必须在心发动的地方用功。心的发动不可能没有不善的,所以,必须在这里用功,就是诚意。如果念头都发动在喜好善上,就切切实实地去好善;如果念头都发动在讨厌恶上,就实实在在地去除恶。意念的发生处既然是诚的,那么本体又怎么会有不中正的?所以,想要正心主要在于诚意。这样诚意才会有着落。”
“然而,诚意的根本又在于致知。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这就是我的良知的所在。然而,如果知善,但不遵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也不遵循良知去做,那么,良知就是被蒙蔽了,就不能致知了。本心的良知既然不能扩充到底,虽然知道善是好的,但也不能切实地去做,即便知道恶是不好的,也不能切实地去除恶,这怎么去诚意呢?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
“但是也不是凭空去致知,致知还是要在实事上格的。例如,意在行善,就要在善事上做,意在除恶上,就要不去做恶事。除恶,本就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从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纠正了,也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这样,本心的良知就不会被私欲蒙蔽了,就可以发挥到极致,而意的发动就是好善除恶,没有不诚的了。所以,格物就是诚意工夫着手的地方。像这样格物,人人都能够做到。《孟子》里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原因。”
【原文】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提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翻译】
先生说:“世人总以为‘格物’就要按照朱熹的观点,他们又何曾切实去拿朱熹的观点实践过?我倒是真正地实践过的。以前我和朋友一同探讨,成为圣贤首先就要格天下之物,现在哪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呢?于是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朋友从早到晚去妄图穷尽竹子的道理,费尽了心思,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因过度劳神病倒了。开始我还以为原因在于他精力不足,便亲自去穷格,从早到晚,但仍旧全然不理解竹子的理。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也卧床不起。因而我们互相慨叹道,圣贤真是做不成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格物。等到后来,我在贵州龙场住了三年,很有些体会,这才知道,天下之物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己的身心上下。所以我觉得人人都能够成为圣人,这样就有了一种圣人的使命。这些道理,都应该说得大家知道。”
【原文】
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
先生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这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
又曰:“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功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翻译】
学生里有人说,邵端峰主张儿童不能格物,只应该教他们洒扫应对的功夫。
先生说:“洒扫应对就是一件事,孩子的良知只有这个水平,所以教他们洒扫应对,也是致他的良知。又比如,小孩知道敬畏教师和长者,这也是他的良知的表现。所以,虽然是在嬉闹,看到了教师和长者,也会去作揖表示恭敬,这就是他的格物,致他尊敬师长的良知。小孩子自然有小孩子的格物致知。”
先生又说:“我在这里说的格物,从小孩子到圣人,都是这样的功夫。但是,圣人格物就会更加纯熟些,不用费力。这样的格物,即使卖柴的人也能做到,公卿大夫与天子,也都只能像这样做罢了。”
【原文】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艰”①二句为问。
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门人问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学之’,又说个‘笃行之’,分明知行是两件。”
先生曰:“博学只是事事学存此天理,笃行只是学之不已之意。”
又问:“《易》‘学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
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学存此天理,则此心更无放失时,故曰:‘学以聚之。’然常常学存此天理,更无私欲间断,此即是此心不息处,故曰:‘仁以行之。’”
又问:“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两个了。”
先生曰:“说‘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为私欲间断,便是‘仁不能守’。”
【注释】
①知之匪艰:语出《尚书·说命中》“知之匪艰,行之惟艰”。意为懂得道理不难,难的是去实践它。
【翻译】
有弟子疑心自己知行无法合一,因此向先生求问“知之匪艰,行之惟艰”两句话。
先生说:“良知自然能知,这本来是很容易的。只是因为不能致这个良知,才会有‘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情况。”
有弟子问先生:“知行怎样才能合一?而且就像《中庸》里,说了一个‘博学之’,又说了一个‘笃行之’,很明显,是把知行当两件事情的。”
先生说:“博学是指事事都要学会存此天理,而笃行则仅仅是指学而不辍。”
弟子又问:“《易》里说‘学以聚之’,又说‘仁以行之’,这又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同样的。如果事事都学习存养天理,那么这颗心就再没有放纵的时候了,所以说‘学以聚之’。但是,时刻学习存养这个天理,又没有私欲把它间断,这就是本心的生生不息,所以说‘仁以行之’。”
又问:“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不就把知和行分而为二了吗?”
先生说:“说‘及之’,意思就是已经行了。但如果不能做到常行不止,那就是被私欲间断了,就成了‘仁不能守’。”
【原文】
又问:“心即理之说,程子云‘在物为理’,如何谓心即理?”
先生曰:“‘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
先生因谓之曰:“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朱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翻译】
弟子又问:“心就是理,程颐说‘在物为理’,为什么要说心就是理呢?”
先生说:“‘在物为理’,‘在’的上面应该添加一个‘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例如,心在侍奉双亲上就是孝的理,在辅佐君王身上就是忠等。”
先生又说:“大家应当明白我立论的宗旨,我现在说心就是理,用意何在呢?只是因为世人将心和理分而为二,所以出现了很多弊病。比如五霸攻击夷狄,尊崇周王室,都是私心,因此就不合乎理。人们却说他们的行为很合理,只是世人的心不纯净,往往艳羡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求外表做得漂亮,与心却完全不相干。把心和理分而为二,只会让自己陷入霸道虚伪而无法觉察。所以我说心就是理,就在心上下功夫,不要袭义于外,就是王道的真谛,也是我立论的宗旨。”
【原文】
又问:“圣贤言语许多,如何却要打做一个?”
曰:“我不是要打做一个,如曰‘夫道,一而已矣’①。又曰‘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②。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
【注释】
①夫道,一而已矣: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云:‘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②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意为天地的法则是至诚纯一的,所以它化育的万物无法测量。语出《中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
【翻译】
弟子问:“圣人的言论有很多,为什么要把它们概括成一句话呢?”
先生说:“我并不是要把它们概括起来,只是像《孟子》所说的‘夫道,一而已矣’,《中庸》里说的‘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都是一个整本,怎么可以把它们分开呢?”
【原文】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便是心也。”
【翻译】
“心并非指那一块血肉,凡是有知觉的地方都是心。比如耳朵眼睛懂得听或者看,而手脚懂得痛和痒。这个感觉就是心了。”
【原文】
以方问曰:“先生之说‘格物’,凡《中庸》之‘慎独’及‘集义’‘博约’等说,皆为格物之事。”
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独’,即‘戒惧’。至于‘集义’‘博约’,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数件都做格物底事。”
【翻译】
黄以方问先生:“您的格物学说,是否是把《中庸》里的‘慎独’、《孟子》里的‘集义’、《论语》里的‘集义’‘博约’等学说,都概括成了格物呢?”
先生说:“不是的。‘格物’就是‘慎独’、就是‘戒惧’。而‘集义’和‘博约’,仅仅是一般的功夫,不应该把它们都当作格物。”
【原文】
以方问“尊德性”①一条。
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②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功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己。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
【注释】
①尊德性:语出《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②子静:陆九渊的字。
【翻译】
黄以方就《中庸》里的“尊德性”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道问学’,就是所谓的‘尊德性’。朱熹说:‘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他是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分而为二,当作两件事了。现在讲习讨论,下了许多的功夫,只非就是要存养本心,让它不会丧失自己德性罢了。哪会有尊德性却只是空洞洞地尊,不再去问学了呢?问学怎么能只是空洞地去问,而与德性再没有别的什么关涉呢?这样,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讲习讨论的人,究竟学的是什么东西。”
【原文】
问“至广大”二句。
曰:“‘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盖心之本体自是广大底,人不能‘尽精微’,则便为私欲所蔽,有不胜其小者矣。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则私意不足以蔽之,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如何广大不致?”
又问:“精微还是念虑之精微,事理之精微?”
曰:“念虑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翻译】
又向先生请教“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两句话。
先生说:“‘尽精微’就是为了‘致广大’,‘道中庸’就是为了‘极高明’。因为心的本体原本就是广大的,如果人不能够‘尽精微’,就会连细小的地方也战胜不了私欲,被私欲所蒙蔽。因此在细微曲折的地方也全都能做到精微穷尽,那私欲就不足以蒙蔽心的本体了,自然不会有许多障碍和隔断的地方,这样心体又怎么会不广大呢?”
又问:“精微是指思虑的精微,还是指事理的精微呢?”
先生说:“思虑的精微也是事理的精微。”
【原文】
先生曰:“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皆是说性,非见性也。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矣。”
【翻译】
先生说:“现在讨论人性的人,都纷扰着争论异同。全都是嘴里谈性,而实际上从未见过性。见性的人根本无异同可争。”
【原文】
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
先生曰:“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
【翻译】
又问:“声色货利,恐怕良知里也不会没有。”
先生说:“当然是这样!但是,初学者用功的时候,就务必要把这些荡涤干净,不要让它们存留在心里。这样的话,偶尔碰到也不会成为牵累,自然而然能够依循良知来应对。良知仅仅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如果能够精明地致良知,没有丝毫蒙蔽,那么,即便与声色货利交往,也都是天理的自然运行了。”
【原文】
先生曰:“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
【翻译】
先生说:“我给各位讲致知格物的学说,天天如此。讲了十年二十年,也是如此。你们各位听了我的话之后,切切实实地去用功。然后再听我讲一次,自然会感觉有了一番长进。否则的话,只把我说的当作一次泛泛之谈,即使听了,又有什么用处呢?”
【原文】
先生曰:“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①”
【注释】
①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程颐语,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翻译】
先生说:“人的本体,一直是寂静不动的,又常常是感应相通的。正如程颐先生所说‘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
【原文】
一友举佛家以手指显出问曰:“众曾见否?”众曰:“见之。”复以手指人袖,问曰:“众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不见性。此义未明。
先生曰:“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骋,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学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着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
【翻译】
有位朋友举出了一个例子,说一位禅师把手指伸出来问:“你们大家看见了吗?”众人都说看到了。然后禅师又把手指缩到袖子里去,又问:“你们还能够看见吗?”众人都说:“看不见了。”禅师便说众人还没有见到性。这位朋友不懂得这段话的意思。
先生说:“手指有时能看到,有时看不到,但是,你悟到的性是一直都在的。人的心神只在所见所闻上驰骋,而不在看不到或听不到的东西上切实用功。但是,不见不闻才是良知的本体,戒慎恐惧则是致良知的功夫。学者时时刻刻都去寻找他看不见或听不到的本体,功夫才会有一个着落。待时间长了,功夫变得纯熟,那就不用再费力了,不用再提防检点,而真性自然也会生生不息了。岂能因为外在的见闻,而被它们牵累呢?”
【原文】
问:“先儒谓‘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同一活泼泼地。” ①
先生曰:“亦是。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功夫。”
【注释】
①“先儒谓”句:程颢语,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三:“‘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无心正’之意同一活泼泼地。”程颢认为鹰飞蓝天、鱼跃深渊所体现的天地阴阳之道和人致良知的“必有事焉”一样是生动活泼的。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语出《诗经·大雅·旱麓》。
【翻译】
有人问:“程颢先生说‘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都是生机勃勃的。”
先生说:“是这样的。天地间生机勃勃,无非是这个天理,也就是我们良知的不停歇的运动变化。致良知就是‘必有事’的功夫。这个天理不仅不能够脱离,实际也脱离不了。一切皆是天理,一切都是功夫。”
【原文】
先生曰:“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拳血’①,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
【注释】
①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拳血:语出《朱子语类》,比喻做事要痛下决心,功夫扎实。
【翻译】
先生说:“大家在这里求学,务必要先确立一个做圣人的志向。时时刻刻都要有‘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拳血’的精神,这样在听我讲学的时候,才能觉得句句铿锵有力。如果只是浑浑噩噩地度日,像一块死肉一样,打也不知道痛痒,最终恐怕无济于事。回家之后还只是以往的老伎俩,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原文】
问:“近来妄念也觉少,亦觉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功夫否?”
先生曰:“汝且去着实用功,便多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会妥贴。若才下得些功,便说效验,何足为恃?”
【翻译】
有人问:“近来我感觉虚妄的念头少了,也不去想一定要怎么怎么用功,不知这是否也是功夫?”
先生说:“你只管去实实在在地用功,即便有了这些想法也无妨。等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变得妥当。如果才刚刚用了一点功夫,就想要效果,怎么可能靠得住呢?”
【原文】
一友自叹:“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
先生曰:“你萌时,这一知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翻译】
有位朋友感叹道:“内心萌发了私意的时候,心里明明很清楚,只是不能够马上把它剔除掉。”
先生说:“私欲萌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就是你立命的功夫,而当下就能立刻把私欲消磨掉,这就是致良知的功夫。”
【原文】
“夫子说‘性相近’①,即孟子说‘性善’,不可专在气质上说。若说气质,如刚与柔对,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则同耳。人生初时,善原是同的。但刚的习于善则为刚善,习于恶则为刚恶。柔的习于善则为柔善,习于恶则为柔恶,便日相远了。②”
【注释】
①性相近:语出《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②刚善、刚恶、柔善、柔恶:此为周敦颐对善恶的分类。周氏《通书》云:“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
【翻译】
“孔子主张‘性相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这不可以仅仅专门在气质上来谈。如果说气质,刚和柔相对,又怎会是相近的?只有性善是相同的吧。人初生的时候,善原本是一样的。但是气质刚的人在善上面容易成为刚善,而在恶上面容易成为刚恶。同样,气质柔的人受善的影响会变为柔善,受恶的影响便成为柔恶,这样,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原文】
先生尝语学者曰:“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
又曰:“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
【翻译】
先生曾经对学者说:“心体上不能有一丝私念存留,就像眼里不能有一点灰尘存在。沙子能有多大多少呢?但是它能让人满眼都昏天黑地了。”
先生又说:“这个念头不只是指私念,就算是好的念头也不能存留一点。就像眼里放了一些金玉屑,眼睛也睁不开了。”
【原文】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
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几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
请问。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
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 ②
曰:“人又甚么叫作心?”
对曰:“只是一个灵明。”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鬼神万物尚在何处?”
【注释】
①感应之几:意为主体与客体之间微妙的感应。
②人是天地的心:语出《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翻译】
有人跟先生说:“先生说人心与物是同为一体的。就像我的身体,原本就血气流通,所以说它是同体。但是对于别人,我就是异体了,和禽兽草木,差得就更远了。可是为什么还说是同为一体的呢?”
先生说:“你只要从感应的征光上看,就会明白,岂止是禽兽草木,天地我也是同为一体的,鬼神也是和我一体的。”
那人又问该如何解释。
先生说:“你看看,天地之间,什么东西才是天地的心呢?”
那人回答说:“我曾听说人是天地的心。”
先生说:“那人又把什么东西当作心?”
说:“只有一个灵魂。”
先生说:“由此可见,充盈天地间的,唯有这个灵魂。人为了自己的形体,把自己跟其他一切都隔离开了。我的灵魂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如果天没有我的灵魂,谁去仰望它的高大?如果地没有我的灵魂,谁去俯视它的深厚?鬼神如果没有我的灵魂,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天地鬼神万物,如果离开了我的灵魂,也就没有天地鬼神万物的存在了。我的灵魂,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同样会不存在了。这些都是一气贯通的,怎么能把它们间隔开来呢?”
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长在,为什么没有我的灵魂,它们就不存在了?”
先生说:“现在你去看那些死了的人,他们的灵魂都已经游散了,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还在哪里呢?”
【原文】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①。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②。
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
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说本体。”
先生然其言。
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
【注释】
①严滩:西汉末年严光(子陵)隐居于浙江桐庐县富春江边的富春山,后人称此处为严子陵钓台、严滩、子陵滩。
②实相、幻相:佛教名词。实相,指宇宙间万物的实体,又名佛性、法性、真如、法身、真谛等,相当于哲学上的本质。幻相,指宇宙间万物的现象。佛教认为所有的相即万事万物的现象都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只有佛性才是不变不坏、永恒不灭的真实。
【翻译】
先生启程去征讨思恩、田州,钱德洪和王汝中送行送到严滩(今浙江桐庐县西)。汝中向先生请教佛教的实相和幻相的问题。
先生说:“有心都是实相,无心都是幻相。无心都是实相,有心都是幻相。”
王汝中说:“有心都是实相,无心都是幻相,是从本体上来谈功夫;无心都是实相,有心都是幻相,是从功夫上来说本体。”
先生对汝中的说法表示赞同。
当时,钱德洪还不是很明白,经过了多年用功,他才相信本体和功夫是一体的。但是,先生当时是因为王汝中问话而偶然论到的。若我们儒家要开导别人,也不必一定要引用它。
【原文】
尝见先生送二三耆宿门,退坐于中轩,若有忧色。
德洪趋进请问。
先生曰:“顷与诸老论及此学,真圆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终身陷荆棘之场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说也!”
德洪退谓朋友曰:“先生诲人,不择衰朽,仁人悯物之心也。”
【翻译】
曾经有一次,德洪看到先生送两三位老先生出门后,回来坐在长廊里,似乎面有忧色。
德洪便上前去询问怎么情况。
先生说:“刚才我和几位老人谈至我的良知学说,真是像圆孔和方榫一样,彼此间格格不入。圣道像大路一样平坦,世俗儒生往往自己让它荒芜阻塞了,最终陷入荆棘丛中也不懂得悔改,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德洪后来对朋友们说:“先生教诲他人,不管对象是否老朽,真是有一颗仁人悯物的心啊!”
【原文】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与丹朱俱不肖①,亦只一‘傲’字,便结果了此生。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无我’自能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注释】
①象:舜的弟弟,为人狂傲,常怀杀舜之心。丹朱,尧的儿子,傲慢荒淫,尧将王位禅让于舜而不传丹朱。
【翻译】
先生说:“人生最大的毛病就是这个傲慢。子女傲慢就必然会不孝;臣子们傲慢就必然会不忠诚;父母傲慢就必然不会慈爱;朋友傲慢就必然不守信。所以,象与丹朱都不贤明,也只是因为这个傲慢,而让他们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你们各位要常常体会这个,人心原本就是天然的理,精明纯净的,没有纤毫沾染,只是有一个‘无我’罢了。心里万万不能‘有我’,有了便是傲慢了。古代圣贤有许多长处,也只是‘无我’罢了。‘无我’自然能做到谦谨。谦谨就是众善的基础,傲慢则是众恶的源泉。”
【原文】
又曰:“此道至简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诸掌乎。’①且人于掌何日不见?及至问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讲便明,谁不知得?若欲的见良知,却谁能见得?”问曰:“此知恐是无方体②的,最难捉摸。”
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③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注释】
①其如示诸掌乎:语出《中庸》:“明乎效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②方体:语出《周易·系辞传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方,方位。体,形体。
③“其为道也”七句:语出《周易·系辞下》。意为易的法则常常变迁不止,在六个爻位之间流动,或变在上,或变在下,阴变为阳,阳变为阴,没有一定的模式,不可拘泥,只有顺应它的变化才能恰当应用。
【翻译】
先生说:“圣道其实极其简单易行,也极其精细微妙。孔子曾说:‘其如示诸掌乎’。人的手掌,哪一天不曾看到呢?但是问他手掌上有多少纹理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了。就如同我说的这良知二字,讲了就能够明白,谁不晓得呢?但如果要他真正理解,又有谁能做到呢?”
有人便问:“良知恐怕是没有方向、没有形体的,因此最难捉摸。”
先生说:“良知就如《易》理:‘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这良知怎么可能捉摸得到呢?只要把良知理解透了,就变成圣人了。”
【原文】
问:“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①是圣人果以相助望门弟子否?”
先生曰:“亦是实话。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②,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
【注释】
①回也,非助我者也:语出《论语·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意为“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我的话他都欣然接受”。孔子认为颜回对于自己的学说能够悉心领会,得其主旨,所以视颜回为同道中人,而非仅仅是自己的助手和学生。
②颜子闻一知十:语出《论语·公冶长》“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十分强调举一反三的能力,所以十分赞赏颜回。
【翻译】
有人问先生:“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圣人是真的期望他的门徒们来帮助他吗?”
先生说:“这也是实话。圣道本来就是没有穷尽的,疑难质问越多,就越能显现出它的精妙来。圣人的言论原本很周全,而有问题的人则心里堆满了疑虑,圣人被他一问,就能发挥得更加精确神妙了。但是,像颜回那样,闻一知十,心里对什么都了然于胸的人,怎么会发问呢?所以圣人也只能寂然不动,没有什么发挥,因此孔子说‘非助’。”
【原文】
邹谦之尝语德洪曰:“舒国裳曾持一张纸,请先生写‘拱把之桐梓’一章①。先生悬笔为书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顾而笑曰:‘国裳读书,中过状元来,岂诚不知身之所以当养?还须诵此以求警。’一时在侍诸友皆惕然。”
【注释】
①“拱把之桐梓”一章:语出《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两手合握。把,一只手握。身,指人自身。
【翻译】
邹谦之曾对钱德洪说:“舒国裳曾经拿一张纸,请先生帮他写《孟子》里‘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写到了‘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的时候,回过头来笑着说:‘国裳读书,还中过状元,难道他是真的不明白怎么修身吗?只是他仍需要背诵这一章来警诫自己。’一时间,在座的各位朋友都警醒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