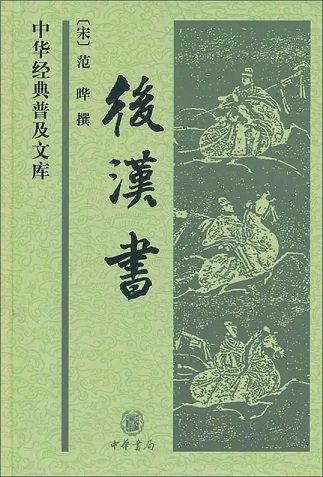第四节 更大的猜想: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隐秘斗争
一、本人探究各种宗教的不精彩经历
本人书呆子气较重,除了见花落泪,恨鸟惊心之外,也喜欢了解各种各样的宗教,加之人缘比较好,因此遇到过各种信教的朋友来动员入教,有信新教的兄弟会,有喜欢拿着《易经》炒股的道教哥们,有信佛教的,有信喇嘛教的,有信“克瑞希那”(Krishna)的,前两年居然还有从海外回来的女同学来动员加入某轮的。前几个月,还在与两个朋友热烈讨论云南某个少数民族的放蛊神功,希望破解以后能够用到哪个富婆身上,让她发疯一样的爱上自己,以后就免去了终身的劳苦。
本人亲自去观摩过韩国、台湾传教士们传教的工作,有一次差点把命丢在大凉山的悬崖绝壁之间。不过那次大难不死,老天给了我巨大的补偿,在从西昌回昆明的火车卧铺上,半夜里醒来,听到对面有两个美女在用地道的成都话喁喁私语,第一次觉得成都美女低声讲话真的堪比吴侬软语,实在是妙不可言。
这里,讲几个本人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饭局上,有人问最近在研究什么,我回答说正在研究佛教,话音刚落,只听啪的一声,另外有人一掌拍在饭桌上,大声赞道:“好项目!”原来,正有人找他投资修建寺庙。吃饭间,那人又说,有家公司把鸡足山的高僧请来给二十八辆奥迪车开光,然后每辆车涨价一万八,本人那时嘴巴很刻薄(估计死后必下拔舌地狱),立刻来了句:“怪不得,网传昨晚某公去大理找小姐,结果价钱翻了一倍,都说是刚开过光。”也是话音未落,旁边一人喷出饭来,害得做东的朋友叫服务员换了好几盘菜。
又有一回,一个朋友带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开始没有说明,等去了成都土龙路上那边的一处所在,才知道有一百多个人来朝见一位甘孜来的活佛。那次场面上非常尴尬,本人有自己的原则,这一生只会向父母、孔子、老子和东坡先生磕头,不愿意去被摸顶、去磕长头,现场所有人只有我独自一人呆在一边,搞得带我去的朋友很有些下不来台,不停地向别人为我开脱,搞得大家非常难堪。但是我那个朋友对我很宽厚,也不在意,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十分亏欠于他。
(不过那次本人也有不小的收获,亲耳听到了歼20发动机测试车间的长久轰鸣声,终于懂得了歼20与歼10B在发动机上的根本区别。)
在与那些宗教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件事对我刺激太大。
十几年前,本人有一次应邀去参加基督教兄弟会的圣诞团契,餐会上,有一个年轻的中国教徒作了一次见证,他对着一百多个信教和未信教的中国人,发自肺腑地痛陈过去没有找到“主”是如何的痛苦和愚昧,最后,他总结说:
“以前我自认为我是华夏子孙,龙的传人,可是现在我终于知道了,龙是什么?龙其实就是蛇,蛇是什么?《圣经》上说,蛇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龙的传人其实就是撒旦的子孙。我不愿做魔鬼的子孙,我要作主的儿女!……”
那次,本人头脑嗡嗡作响,愤然中途离去,以至于从那以后,就对基督教充满了警惕。
其实这半辈子,本人始终记得东坡先生的那两句话:
“吾生不恶,料必不坠。”
“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二、世俗中国人永远不可能理解一神教教徒的精神世界
在几千年来都是世俗社会的中国,无论古今中国人,都实在难以深刻理解“一神教”体系下,一般人精神世界深处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甚至可以这样说,可能永远都理解不了。
中国人当中不乏各种教徒,但是,这些教徒当中最起码有大半以上都不具备真正的宗教徒精神。
信佛教的,绝大多数只是烧香了愿的香客,我捐了钱,菩萨你就得保佑我,否则这座庙的菩萨就不灵验,对不起,拜拜吧菩萨,我去找下一家了。信道教的,则多数是为了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等哪天摸到身上什么地方有了个硬块,对不起,赶紧飞奔医院,菩提老祖也好、太乙真人也好,都不如外科王主任的那把手术刀靠谱。
至于信基督的,则多是凑个热闹,赶个时髦,唠个嗑、解个闷,散个心,吃顿饭,领个包,也没几个真正沉迷进去的。而且就算当时沉迷进去,但发现没多大好处,很快又撤退了出来。
实际上,中国人自小就被培养出了一种完整的世俗道德,这个体系健全的世俗道德体系支撑了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精神世界,哪怕有的人最终触犯刑律,但其犯罪的自我辩护理由也是基于这些世俗道德,而不会因为宗教理由。
比如说,张扣扣杀人,理由就是为母复仇。
白银市的连环杀人案,凶手自述其最初的犯罪动机,也是因为“被女人抛弃,感觉被歧视”。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莫名其妙的宗教仇杀,没人见过和尚在街上砍了道士,然后指着道士的尸体大骂:你居然不念“阿弥陀佛”!
也从来没见过道士在街上没来由砍了回教徒,然后指着尸体大骂:你丫竟然敢吃牛肉!
但是在一神教社会,他们觉得就根本不可思议,连非洲的黑人兄弟都会觉得无法理解:
你们中国人居然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你们没有道德,没有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是无法无天的魔鬼。
因为在一神教社会里,只有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宗教道德,而没有宗教道德以外的世俗道德。
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旧约》里有那么多祭师、拉比会恶毒地诅咒那个“不再信神”的以色列国和犹太国,因为在一神教社会里,一旦失去了信仰,社会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地狱,就成了索多玛和蛾摩拉,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然而,对一神教的宗教道德观,中国人却并不认同。
中国不信宗教,自然没有宗教道德,但是,以 “仁”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世俗道德,以更高的境界和更辽阔的胸怀,把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在华夏文明的范围内,中国人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在在华夏文明之外的那些人,圣人们则要求“为政者”可以通过教化、通过修德政等等,来做到“来远附迩”,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
所以,在中国的世俗道德框架内,人只有接受不接受文明教化的“华夷”的区别,而没有种族、民族的区别。
有人说了,中国古代把天下区分为“华夏”、“夷狄”,这本身就是一种妄自尊大与排他性歧视。
不可否认,在古代、近代甚至今天,世界上各个民族、部落的文明发展程度是先后不一的,成熟的文明对落后的文明抱着轻视、歧视、蔑视的态度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是,这些成熟的“文明体”是怎样来对待那些落后的“文明体”的。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进入西周以后,中华文明就开始展现出了极高的人性光辉,在文化科技遥遥领先于周边民族的优势条件下,除了一些特殊原因之外,中国历史上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中央政权对境内外落后弱小民族的灭绝性的大屠杀。新中国建国后不久,解放军去把云南原始丛林里的“苦聪人”、“莽人”接出来,2021年之前,中国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扶贫攻坚战,在过去人迹罕至的峻岭峡谷间建桥、拉电线,在边陲盲肠地带建起一座设施完备的现代化中学、医院、社区,甚至远去非洲“授人以渔”,这种天下大同的伟大精神,就是中华文明的这种“仁义”内核的发扬与升华。
可我们来反观一神教社会,其尸山血海的历史就让我们掩目塞耳,根本无法去一一直视。
一神教社会里,由于没有世俗道德,宗教道德只对同样信仰的人起作用,换句话说,宗教道德只能约束教徒之间的行为,而在宗教以外,就在也不存在道德、公德、甚至人类之间起码的怜悯与同情,所以,一神教的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大掠夺、大屠杀、大灭绝。
在一神教的观念里,对待异教徒,一切“恶”都符合他们自己的宗教道德。
这些年,有很多中国人对欧洲的许多教堂很是神往,不断前去参观,但是,他们在很多教堂里看到了无数的堆在一起的累累白骨,惊讶不已。据介绍,这都是当杰出教徒们的伟大功绩——带回来那么多异教徒的头颅。
再想想中国那无数的文庙、寺院、道观里,供着的慈眉祥目的圣人、佛祖、观音、天师、道君,我们凭什么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凭什么没有“夷夏之别”?凭什么不自尊自爱?凭什么不誓死保护我们的文明?
三、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的现有关系
导弹在晴空中留下道道白烟;
炸弹爆炸后的满街血肉;
幼儿尸体漂浮在海面上;
卖做奴隶的少女的哭嚎;
被粉碎机打成肉酱的几百名儿童;
巴黎圣母院的冲天大火。
这就是犹太教、伊斯兰剑和基督教之间的现有关系。
四、“弘治碑”证明,《圣经》官方版本最起码在1663年左右都未最后成型
有许多神棍一天到晚吹嘘,《圣经》从撰写出来的那一天起,就再没有改动过一个字,但实际上,《圣经》在成型过程中做过许多次的增删修改,有些经文被天主教删除,但却又被东正教收录。
美国《圣经学者》巴特·埃尔曼指出:“我越是研究《圣经》的抄本传统,就越理解到这些经文在传抄者手上那几年,是如何被彻底改动过,抄写者不但保存了经文,也更动了经文。当然,现存抄本中所发现的数十万种经文修改,如果说这些经文更动对于经文意义或可导致的神学结论完全没有实质关联,那就错了。”
据说,欧洲在1456年就形成了《古腾堡圣经》古腾堡标准印本,印数为180本,直接印在精美的羊皮纸和纸张上,这个版本在18世纪才发现,而十八世纪正是欧洲人历史发明家们造假的高峰期。
(此段材料借引自董并生老师的内部交流,未经同意使用,在此致歉。)
《圣经》经文内容的变化,在“弘治碑”中也可见一斑。
“弘治碑”中说,亚伯拉罕创教的时间是在周朝146年,也就是公元前900年,也就是周孝王十年;又说摩西接替掌教的时间是周朝613年,而周朝613年则是公元前433年,这一年为周考王八年,或晋幽公元年,或楚惠王五十六年,离孔子去世已经过去了46年。
就算我们把《旧约》当做历史,按照《创世纪》的描述,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亚伯兰从乌尔迁徙到了迦南地的别是巴。亚伯兰的这次迁徙乃是受上帝指使的,一般认为,这一年就是犹太教的创立时间。同样,在《出埃及记》里面,大约是公元前1290年,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越红海,到达西乃旷野。
为什么差别会有那么大?
这说明,直到“康熙碑”面世的1663年左右,梵蒂冈教廷最起码对《摩西五经》的官方文本都还没有正式定型。
另外,到十八世纪,欧洲的的宗教礼仪和宗教规范又是个什么水平呢?
这里,再次借用一下董并生老师所介绍的伏尔泰《风俗论》中的滑稽一幕:
“人只是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才会想要到要锦上添花,然而这种基本需要当时几乎在整个欧洲还都很匮乏,在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和伦巴地北部,人们知道些什么呢?
在不少教堂,一直在庆祝驴子节、愚人节和疯人节,人们把一匹驴牵到祭台前,唱赞美歌,开头的迭句是这样的:
阿门,阿门,驴;
艾,艾,艾,驴老爷;
艾,艾,艾,驴老爷;
迪康吉及其后继者都是最严谨的编纂者,从在一本500年前的手稿中援引过来的这样几句对驴子的赞美歌:
哎,驴老爷,歌唱吧!
美丽的嘴,不高兴吧!
你将得到足够的干草!
一个年轻的女人扮演上帝的母亲,骑着这头驴到埃及去,她怀抱着一个小孩儿,身后跟着一长串的人,在弥撒结束时,神甫不是说弥撒礼毕,而是用最大力气学驴叫三声,参加弥撒的人都以同样的叫声来回答。”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西方史读多了、入迷了,一定会变傻,变成二傻子。 谁若不信,我就举两个“古罗马史”的例子给大家看。 第一个例子。美国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方史读多了、入迷了,一定会变傻,变成二傻子。 谁若不信,我就举两个“古罗马史”的例子给大家看。 第一个例子。美国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 无论古希腊史专家们如何努力地从“学术”高度去拯救,曾经横行一时的“古希腊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之类,都无可收拾地变成了童话、神话或者是茶余饭后的笑话。当然,...
- 基督教是佛教的分支吗?咱们看几副图。图一是欧洲现存最早的耶稣雕像,不但是张亚洲人的脸,他还穿了一副袈裟,看图二唐僧,耶稣袈裟跟唐僧同款。(欧洲现存最早的耶稣雕像)...
- 摘要南京博物院藏《坤舆万国全图》插图本的船舶插图全部悬挂中国特色的万字旗和牙边旗,没有欧洲船舶旗帜。明代中国海舶遍布沧溟宗(今误称太平洋),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
- 《奇器图说》也是伪史论者们经常“考证”的一本古籍,他们认为这本书是王徵所著。被西方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z)窃取,明朝人发明创造了自行车、自行磨,更有甚者号...
-
Deepseek认为埃及金字塔确实建于古埃及时代,不是近代人建造的
这几天经常看到关于质疑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年代问题,就想起无所不能的Deepseek,试着问问它怎么回答。问Deepseek:有人说埃及金字塔是近代人造的,但是我觉得金字塔里那么丰富的... -
傻子伪造的古希腊海战、海洋文明、地中海文明圈,被精英们当做高端知识
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因此,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成就了古希腊的科技文明、工商业文明、民主与开放的政治文明,进而成就了希腊帝国、希腊化,最终成就了西方文明。... - 这些年来搞西史辨伪,我经常十分疑惑:为什么有些人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我们,而且连生活常识、科技常识都不管不顾?为什么有些人在反对我们的时候,连脸都不要,总是要靠...
- 西史辨伪为什么总要揭露满清历史?因为西方伪史的总根源就是满清。现在的人们有一个误解,以为华夏古代是愚昧而生产力落后的,这是满清愚民华夏后的刻板印象。明朝军队的火器...
- 我们现在看到的《明实录》很可能被美国动了手脚。如今看到的明实录是民国时期根据红格本明实录重修的,红格本明实录据说是清朝明史馆的手抄本,最具权威。民国史馆决定以红格...
- 时至今日西方还在编造伪史,2023年7月10日,美国、加拿大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发现了一幅老虎追逐山羊得马赛克画(下图),年代在西元400年,距今1600年。发现的位置是在以色列一...
- 01北宋年间,江南柳庄有个秀才名唤柳忠,以教书为业,在当地颇受好评。妻子柳王氏诞下儿子柳雁,产后血崩离世。留下父子相依为命。自家日子不好过,但生性善良的柳忠还是收养...
-
 【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Ross方恩格】前两天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Ross方恩格,因为巴以冲突的相关话题,在头条上指责中国网友不同情犹太人的言论,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一个...
【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Ross方恩格】前两天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Ross方恩格,因为巴以冲突的相关话题,在头条上指责中国网友不同情犹太人的言论,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一个... - 01改革若不触动利益集团,就如同无根之木,难以成功。洋务运动醉心技术,忽视制度,因未触动利益集团,先进技术成了旧制度附庸,北洋舰队覆灭便是例证。这深刻表明,改革要触...
-
 12019年,莫言应邀为赵尚志将军殉国处所立石碑撰写碑铭,并为赵将军雕像撰诗一首:白山黑水建奇功,剑影刀光气若虹。首葬丘陵藏猛虎,躯投江海变蛟龙。身经百难心不改,体被双...
12019年,莫言应邀为赵尚志将军殉国处所立石碑撰写碑铭,并为赵将军雕像撰诗一首:白山黑水建奇功,剑影刀光气若虹。首葬丘陵藏猛虎,躯投江海变蛟龙。身经百难心不改,体被双... -
 编者按:2022年,乌克兰危机牵动人心。乌克兰危机升级源于美西方在地缘政治领域对俄罗斯不断施压、步步紧逼,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的结果。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
编者按:2022年,乌克兰危机牵动人心。乌克兰危机升级源于美西方在地缘政治领域对俄罗斯不断施压、步步紧逼,是双方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的结果。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 -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先祝各位看官节日快乐。本来是放假,我却在码字,真是“劳动节”啊,前脚董大姐被自己“惊世骇俗”的言论缠身,后脚董小姐“私人大瓜”铺天盖地,真是...
-
 为梦想窒息的贾跃亭,这一次可能要让自己窒息了。日前,贾跃亭努力多年要造的法拉利未来汽车发布了三季度财报,几个简单的数字直接让无数投资人脑溢血。▲ 图源:FaradayFutu...
为梦想窒息的贾跃亭,这一次可能要让自己窒息了。日前,贾跃亭努力多年要造的法拉利未来汽车发布了三季度财报,几个简单的数字直接让无数投资人脑溢血。▲ 图源:FaradayFutu... -
抗美援朝时,战犯吴绍周提出2条妙计对付美军,毛主席:提前特赦。
1959年12月,功德林内的战犯们迎来了第一次特赦,包括王耀武、杜聿明、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宋希濂、曾扩情、周振强、卢浚泉在... -

“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一代雄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个人的悲惨结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则是这个阶段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当我们研习春秋战国的历史,品读《战国策·赵武灵王平昼闲居》之时,对... -
 转自凤凰网最华人号作者:余叶子近日,4名中国公民在美国突然遇害的消息,震动了海外华人圈。嫌犯是谁?为何行凶?当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后,网友评价格外戳心:老乡见老乡,背后...
转自凤凰网最华人号作者:余叶子近日,4名中国公民在美国突然遇害的消息,震动了海外华人圈。嫌犯是谁?为何行凶?当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后,网友评价格外戳心:老乡见老乡,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