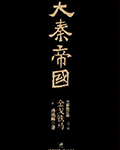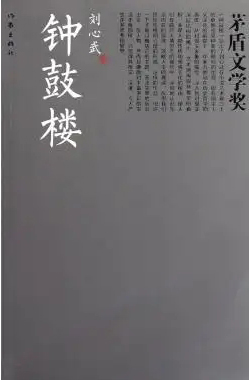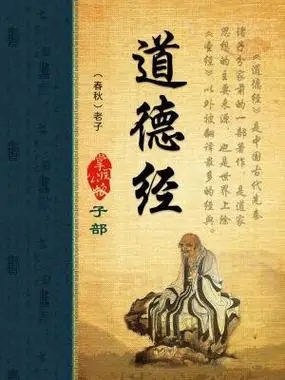三、“弘治碑”中的重重破绽
从立碑时间来看,所谓的“弘治碑”立于明朝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是“三大碑”中最早记录“开封犹太人”历史的一块碑,其碑文也把“开封犹太人”的来源交代得相对清楚一些,因此,我们重点来探究一下这块“弘治碑”的真伪。
在“弘治碑”中,“开封犹太人”的后裔们这样讲述了自己宗教的历史:
“夫一赐乐业(以色列——)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乃盘古阿耽(亚当)十九代孙也。……那其间立教本至今传,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乜摄(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也。生知纯粹,仁义俱备,道德兼全。求经于昔那山(西奈山)顶,入斋四十昼夜。”
第一个问题:“周朝146年”和“周朝613载”的纪年方式为何如此古怪?
碑文中“周朝146年”和“周朝613载”的说法,明显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纪年习惯,打开任何一本中国史书,你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年代记录。
中国历史上,如果说到哪朝哪年,都是采用一种特定的纪年方式。在汉武帝使用年号以前,一般都是采用“国号+君主谥号或者庙号+该位君主在位的时间序数”,比如“周武王九年”、“齐桓公元年”、“秦二世二年”、“汉高祖十一年”等等,在汉武帝开创使用年号之后,便采用“年号+君主在该年号内的时间序数”,比如“元朔三年”、“贞观五年”、“端平元年”等等。
比如,《史记•周本纪》在记述年代时,是这样表述的: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又如,《宋史卷六•本紀第六•真宗一》:
“三年三月,太宗崩,奉遗制即皇帝位於柩前。”
“九月庚辰,赐契丹降人萧肯头名怀忠,为右领军卫将军、严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戌朔,詔天下系囚死罪已下減一等,杖罪释之。”
又如,《金史•卷七•本纪第七•世宗》
“二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正月庚午朔,宋、高丽、夏遣使来贺。戊寅,诏有司:‘凡陈言文字,皆国政利害,自今言有可行,以其本封送秘书监,当行者录副付所司。丙申,’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
又如,《元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成宗二》
“大德元年春正月庚午,增诸王要木忽而、兀鲁而不花岁赐各钞千锭。”
又如,《清史稿•本纪六 圣祖本纪一》
“五年丙午春正月庚寅,以广东旱,发仓穀七万石赈之。”
…………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谁会把哪个朝代的全部时间当做一个整体,然后再来记载为“汉朝第一百二十一年”、“唐朝第两百三十五年”,比如说汉武帝“元朔三年”为公元前126年,同时也是汉朝建立的76年,但历史上从来就不会有人说是“汉朝七十六年”。从古代到今天,中国无论是史官还是其他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朝鲜民族、日本和越南,整个“中华文化圈”都从来没有过这种纪年方式和思维习惯,所以,这种非常别扭的“周朝146年”和“周朝613载”的说法,是非常明显的外来纪年方式。
然而,纵观整篇碑文,也是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文章的写作方式,中规中矩,从碑文落款来看,本文撰写者是一个叫金钟的开封府儒学增广生员(俗称“秀才”),照理说读经史子集的底子也不会太差,可为什么他却要采用这么一种古怪的纪年方式呢?
这里,碑文作者实际上有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来探讨。
第二个问题:“开封犹太人”到底是何时来到开封?
“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孝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癸未,列微(利未)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剌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杖。”
我们先来一下复述这段文字的内容:
1、北宋期间,一个有七十个姓氏的海外族群千里迢迢来到了东京开封;
2、这个族群把一种“西洋布”敬献给了北宋皇帝;
3、皇帝龙心大悦,勉励这个族群“归我中夏,遵守祖风”,让他们留在了汴梁;
4、到宋孝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也就是北宋亡后36年,这个族群由一个叫五思达的人掌教,并安排一个叫俺都剌的族人在开封建寺;
5、到元朝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五思达又在开封土市字街东南重建古刹清真寺。
应该说,这段资料的记录是非常模糊而混乱的。
1、整个宋朝,开封都称为“开封府”或者“东京”,到1126年金国攻陷开封以后,才改开封为“汴京”,而从元朝开始,开封又开始叫做“汴梁”。因此,在北宋期间,开封府是不可能被称作“汴梁”的。
2、在宋孝隆兴元年(1163年),开封已经被金国占领了36年,所以,作为女真人统治下的“开封犹太人”,就应该把那一年称做“金世宗大定三年”。
3、1163年,那个叫“五思达”的利未人开始掌教,并主持建立了第一所“犹太清真寺”,这一年就算他才刚满20岁,但是到了1279年,他又主持重建了“犹太清真寺”,掐指一算,五思达老先生最少已经有136岁了。
第三个问题:到底有多少“开封犹太人”来到了北宋?
按照“弘治碑”所说,北宋时候来到的这批“开封犹太人”有七十个姓氏,我们知道,一个姓氏就是一个家族,这帮最早的“开封犹太人”共有七十个姓氏,就算每个家族平均只有15人(犹太人的传统跟中国人一样也是喜欢多子多福),那么,这群人也有一千人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族群,加上他们携带的大量家产(犹太人一向是比较富裕的),估计最少也要有三四十艘船。这么庞大的一支船队,不远千里从天竺来归附华夏文明,专门给皇帝进献“西洋布”,像这样的盛事,怎么可能不轰动一方?
这里说句题外话,其实,陈垣先生也发现了“七十姓”这个数字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但是,民国学者特有的殖民地自卑心理让他失去了对西方人的怀疑勇气,所以他并没有以此为突破口,凭借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来对“弘治碑”进行证伪,进而推翻“开封犹太人”这段伪史,却反过来帮助弥补其漏洞。
陈垣在他的那篇被视为“开封犹太人”存在的重要考证基础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一文中,就毫无根据地将“七十姓”擅自改为“十七姓之误”,煞费苦心地来缩小了“犹太人来开封”的规模,从而让“犹太人来开封规模太小,因此不见于史料”的说法有了存在的空间。
但是,就算按照陈垣所说的“十七个姓氏”,那么,十七个家族,每家15人,也有250—300人,加上其大量家产,船队也会有十艘船左右,这个规模还算小吗?
因此,即使是陈垣如此苦心孤诣、严丝合缝地来“考据”,却照样掩盖不了“弘治碑”伪造历史的事实本质。
第四个问题:“开封犹太人”的事迹为何在中国史籍中无迹可寻?
一个三四十艘船的庞大船队,不远千里从天竺来归附华夏文明,不要说到达开封,一进长江口就会惊动地方官府,那些沿途的知府、知州、知县们,哪一个不会抢着专门派官员把他们一路护送兼解押到东京?
在那个以“来远附迩”、“远至迩安”为仁政标配的帝王时代,不管是宋太宗也好、宋真宗也好、宋徽宗也好,哪一个帝王不会兴高采烈地让史官在史书上大书特书一番?
然而,我们查遍《宋史》、《金史》、《辽史》、《元史》、《明史》,都没有找到一星半点的记载,甚至与此相关的间接资料也没有。正史没有收入,那么地方志会有吗?然而,从宋金到明清,所有的地方志也同样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有人说,“开封犹太人”的先祖来见北宋皇帝,事情太小,所以,史官根本不会记载下来。说这话的人估计不熟悉中国史籍,这里我们随便摘录一段,就可以深深理解中国史书的“事无巨细”。
如,《宋史•卷八•本纪第八•真宗三》:
“(宋真宗四年)二月戊申,赐扈驾诸军缗钱。华州献芝草。……壬辰,诏朝陵自西京至巩县不举乐。癸巳,禁扈从人践田稼。”
“五年正月乙亥,赐处州进士周启明粟帛。戊寅,雨木冰。壬午,幸元偁宫视疾。河决棣州。”
又如,《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徽宗三》:
“(徽宗二年)五月癸亥,虑囚。……冬十月乙巳,得玉圭于民间。”
“(徽宗三年)冬十月乙丑,阅新乐器于崇政殿,出古器以示百官。”
看了以上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你还会觉得数百人从海外来归附圣王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吗?
又有人说了,从“宋孝隆兴元年(1163年)在开封建寺”的表述来看,“开封犹太人”来的时候可能是金国时候,他们在开封见到的不是宋朝皇帝,而是金国皇帝,所以此事在《宋史》里没有记载很正常。
持这种观点的人就更无知了。
其一,1211年,成吉思汗在野狐岭大败金国四十万大军,金宣宗被迫在1214年将都城从中都迁往汴京开封,也就是说,金国皇帝从1214年才迁都来到开封,那么,1163年就在开封建“犹太教堂”的那帮“开封犹太人”,他们的“西洋布”献给了哪位金国皇帝?是称为“小尧舜”的金世宗,还是那位向宋、西夏、蒙古同时开战的愚蠢蛮横的亡国之君金宣宗?
其二,女真人入主中原后,即刻实行宋制,所以,金国史书跟宋朝史书基本上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同样是“事无巨细”。
如,《金史•卷六•本纪第六•世宗上》:
“(金世宗三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诏流民未复业,增限招诱。”
“(十二年)五月癸酉,上如百花川。甲戌,命赈山东东路胡剌温猛安民饥。丁丑,次阻居。久旱而雨。戊寅,观稼。禁扈从蹂践民田。禁百官及承应人不得服纯黄油衣。癸未,谕宰臣曰:‘朕每次舍,凡就秣马之具皆假于民间,多亡失不还其主。此弹压官不职,可择人代之。所过即令询问,但亡失民间什物,并偿其直。’乙酉,诏给西北路人户牛。”
“开封犹太人”的事情,不仅不见中国正史、地方志,甚至连《东京记》、《墨庄漫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大宋宣和遗事》、《齐东野语》这样的私人笔记,可以把“梓州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大相国寺外南门大街有一家唐家金银铺”、“曹婆婆肉饼做得香”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可在里面却依然找不出“开封犹太人”的半点影子。
我们从《东京梦华录》卷二的“饮食果子”专题中,随便摘上一段:
“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儿子,皆通谓之‘大伯’。更有街坊妇人,腰繋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子弟少年辈饮食,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菓子香乐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剳客’,亦谓之‘打酒坐’。又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如比处处有之,唯州桥炭张家、乳酪张家,不放前项人入店,亦不卖下酒,唯以好淹藏菜蔬,卖一色好洒。”
如果真有一千犹太人乘着几十艘大船,自天竺来皈依华夏,一路浩浩荡荡,如果真有所谓的“西洋布”,如果真有“犹太教堂”、“犹太清真寺”,如果真有“剔筋教”、“蓝帽回回”,这些爆炸性的新鲜玩意儿逃得过张择端们、孟元老们的那双敏锐的眼睛和细腻的艺术嗅觉吗?
第五个问题:该有的确有记载,不该有的确实踪迹难寻
宋朝时候,“开封犹太人”没有任何一点记载,相反,对同样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的记载倒是屡屡见诸官野资料。
两宋时期,阿拉伯帝国四分五裂,但是穆斯林商人却在中东、北非、欧洲、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十分活跃。宋朝的伊斯兰教徒大多数是自唐以后留下来的“土生蕃客”,有的到中国居住已达五世。同时,外国穆斯林仍在不断地向中国移居。如在海南,雍熙三年(986年)有100人、雍熙四年(987年)有150人、端拱元年(988年)有300人“内附”。
广州的辛押陀罗“家资数万缗”,曾要求助修广州城,并向府学捐过资,赠过田。
在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他被授予“归德将军”的称号。
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林湜〔shi石〕任泉州知州,向当地穆斯林募钱建造战舰,加强海防。
熙宁(公元1068—1077年)初年,广州府学开始招收各族学生,穆斯林子弟“皆愿入学”。到了大观、政和年间(公元1107—1118年),在广州、泉州出现了“番学”。所谓“番学”,即主要招收穆斯林子弟的学校。
第六个问题:《宋史》中“僧你尾尼”的记录,与斯坦因、伯希和在新疆发现的“希伯来文书”,以及《元史》中的“术忽回回”等,算得上“开封犹太人”存在的证据吗?
有坚决支持“开封犹太人”存在的人,曾经搜遍中国史书,举出了几个据说跟“开封犹太人”有关的证据。
第一,《宋史·本纪·真宗一》中曾有一段记载:
“咸平元年……辛巳,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称七年始达。”
根据这么寥寥数字,那些“开封犹太人”的支持者,就认为这就是《弘治碑》所说的十七姓犹太人向宋朝皇帝进贡的最早记录和确切证据,他们认为:
1、在“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那句话中,僧就是泛指一切信仰宗教之人,其中就包括犹太教徒;
2、那个叫“你尾尼”的犹太教徒,其姓“你”与“李”同音,所以,“你”就是“十七姓”中的那个“李”姓;
3、“你尾尼”来自西天,而中国常说的西天就是指天竺。
综合上述理由,那些支持“开封犹太人”存在的人就认为,《真宗纪》中的那句“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就是《弘治碑》中所说的那段犹太人来开封的官方记录。
这种观点甚至不能叫做证明,只能算是推测,而且属于捕风捉影、张冠李戴,荒谬牵强得简直不值一驳。
1、在中国历史上,“西天”一词,并非专指天竺。
在公元前6世纪年开始,汉语系佛教的传播路线是: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洛阳,然后再从洛阳传向中国各地。而在佛教的传播途中,真正把佛教发扬光大的是贵霜帝国,它位于中国西边,中国的佛教最初就是由贵霜帝国经由西域传过来的。故而,玄奘最初也是向西,先到西域、西亚学习了佛教的发展历史,搞清楚了“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来龙去脉后,然后再去到天竺,倒过来教授天竺佛教徒。另外,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也把玛旁雍错称为“西天瑶池”,而这里也并不在天竺。
所以,在小说《西游记》之前,中国人一般把西域、西亚、南亚等地都泛指“西天”,在《西游记》之后,一般老百姓才用“西天”一词来特指天竺。
2、如果说,把“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当中的几个要素“僧”、“天竺”分解开来,就能判断出他是犹太人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就建立了一个逻辑:“从印度来的僧人都是犹太人”,按照这个逻辑,只要是从印度来中国的僧人,不管是从汉明帝时期来洛阳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还有那个所谓活了1072岁的宝掌和尚,还有鸠摩罗什,还有禅宗的达摩老祖,都变成了犹太人。
3、那个“僧你尾尼”,因“你”音近似“李”字,就被当做姓“李”,实际上,在宋朝音韵中,“你”字跟“李”差别非常大,不可能被宋人作为同一个音。
4、如果把“你尾尼”中的“你”被望文生义地当做了姓,那么,那个最少活了136岁的的重要人物“五思达”,他是不是就姓“五”呢?既然犹太人在到达中国之前就有了七十个姓氏,并且到1279年,犹太人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一两百年,难道“五”是在中国发展出的第七十一个姓?这里会不会演绎出一个新的故事出来,说是一个姓五的中国人倒插门成了“开封犹太人”,最后还成了这群犹太人的掌门人?
5、僧你尾尼从天竺来中国,说是在路上走了七年。我们试想一下,一个有七十个姓氏的庞大族群,带着千把个老老少少,像玄奘一样翻越千山万水,尤其是还要穿过与宋朝敌对的吐蕃和西夏的防线,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目的就是向中国皇帝献上“西洋布”,这是在编写《出埃及记》(Exodus)2.0版的《出天竺记》吗?
(脑补一下,两大天后惠特尼·休斯顿和玛丽亚·凯莉深情对唱《When you believe》2.0版:
僧你尾尼你真美,万水千山跑断腿。
不求官位不求富,只给皇帝献匹布,献——匹——布。)
有人说,僧你尾尼来中国并没有说是走陆路,他带着族群里的那么多人,肯定是走海路。那么,兄台,你来解释一下,走海路需要七年吗?在潮湿盐重的海上漂泊七年,那个神奇的“西洋布”不知道会朽烂成什么模样了,还有资格献来给宋朝皇帝吗?
第二,1926年,法国人普瑞浮宣称在洛阳找到了三块叙利亚犹太人所使用希伯来文字体书写石碑的拓片,其时代属于东汉时期,这是犹太人从汉代起就进入了中国的最有利的证据,结果,这些拓片被证明是佛教徒使用的佉卢文,跟希伯来文毛关系都没有,立功心切的法国人普瑞浮只不过又演了一出闹剧而已。
第三,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据说在新疆和阗地区发现了一封希伯来文信件,1908年伯希和在敦煌据说发现一份希伯来文祈祷文,西方学术界认为,这两件东西都是唐代遗物的残片,由此,西方历史发明家们就把这两份残片当做了犹太人在唐代就进入中国定居的证据。
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
就算斯坦因和伯希和没有伪造文物,而且也没有把文物鉴别错误,这也不可能作为犹太人在中国定居下来并且生根发芽形成族群的证据,因为唐朝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非常多,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经商、学习的过客,以族群形式定居下来的极其稀少,起码在目前中国史书上,还没有找到过犹太人定居下来的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如果说找到两份希伯来文文书就可以当做犹太人定居的证据,那么,在中国境内能够找到的异族文件多得浩如烟海,那是不是所有这些民族都定居在了中国?
第四,《元史》中的“术忽回回”一词并非是指犹太人。
1、从北宋到元朝初年,“回回”一词泛指西夏以西的新疆至里海一带的民族,并不专指伊斯兰教教徒。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梦溪笔谈》。沈括曾这样说道:
“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予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吟之,粗记得数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
这里所说打的“回回”,是指当时居于高昌安西一带的“回鹘”,因为唐宋时被新兴民族黠戛斯所破,“回鹘”便迁到这些地方。要到河源(古称葱岭地为河源,意黄河发源地)须过安西,因此须打走盘据在安西的“回鹘”,总之这里的“回回”与“回鹘”诸词毫无区别。但是在这里,“打回回”只是“打敌人”的一种代称,因为北宋时或就从来走出过河西走廊,就更不要说去高昌安西打真正的“回鹘”去了。
照沈括的说法,当时的凯歌都是些“市井鄙俚之语”,因此沈括作凯歌时,也一定是尽量使用这种市井鄙俚之语,以便歌唱的边兵容易领会,所以用“回回”而不用“回纥”或“回鹘”者,一定因为“回回”这一词流行于当时社会的“大众语”,也就是沈括所认为“市井俚鄙之语”。
在南宋彭大雅和徐霆的《黑鞑事略》中,则屡见“回回”一词:
“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
这里所谓“回回字”在赵琪的蒙鞑备录中则称为“回鹘字”。备录云:
“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它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
蒙古人最初所用的字是“畏兀儿字”,有《元史》《塔塔统阿传》及《释老传》为证,所以这里的“回回”,一方是代替“回鹘”,一方又系指“畏兀儿”而言。这里要特别注明的是,当时“畏兀儿”信奉的是佛教。
“霆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回回诸种尽已臣服,独此一种回回正在西川后门相对……至今不肯臣服。茶合解征之数年矣,故此更增兵也。”
“其残虐诸国已破而无争者,西北曰……抗里(原注回回国名)……已争而未竟者……西北曰克鼻稍(原注回回即回纥之种),初顺鞑,后叛去,阻水相抗……”
上述所征的“回回国”当即花剌子模,第二段的“抗里”即《元史》中的“康里”、“克鼻稍”,据王国维先生考订为“钦察”。《元史》中的康里人和钦察人有传的很多,但皆看不出信伊斯兰教的特征来,所以,徐霆是把西夏以西新疆至里海一带的民族统称为“回回”。
2、元代开始,大批西亚和中亚的穆斯林随蒙古大军从陆路迁来中国,称为“色目人”,分居于全国各地,帮蒙古族治理辽阔的国土。元朝统治者发现这些西域人信教不一,高昌回鹘信佛教,西域其它地区信伊斯兰教,因此为了区分,便将信佛教的高昌回鹘按照他们的自称,称为“畏兀儿”,将其它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域人仍称为“回回”。
此时的“回回”便与宗教建立了联系,单指伊斯兰教徒。
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佛教成了国教,而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则占有极大势力,二者都是社会上的显要分子,自不能拿一个名称叫他们。这种不同的称呼至迟在元世祖时已经成立,有当时的公文诏书可证:
“中统四年,谕中书省于东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不以回回、通事、斡脱、并僧、道、答失蛮、也里可温、畏兀儿诸色人户,每钞一百两通滚和买堪中肥壮马七匹。”(《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引经世大典·马政篇》)
“至元二年六月,圣旨谕中书省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回回及诸色人匠,应据官中无身后人等,并不得骑坐马匹,亦不得用马拽碾耕地。”(《大元马政记》)
这两条是政府买马和禁人民骑马的诏令。“回回”与“畏兀儿”并列,足见当时对于二者的分别。同时还可使我们推想到这两名词是普遍的行于社会上。
这里“回回”之为伊斯兰教徒还可从当时的诏令中得到证明,《元典章》有一条云:
“答失蛮、迭里威失户若在回回寺内住坐,并无事产,合行开除外,据有营云事产户数,依回回户体例收差”。“答失蛮”是波斯文学者的称呼,《长春西游记》称为“大石马”,等于现在清真寺里的阿衡。“迭里威失”是回教中的一种苦修学派,足见回回寺是指伊斯兰教徒的寺,而“回回”则指伊斯兰教徒而言。
除公文诏令外,当时的志书也把这两种人分别得很清楚,陈垣先生的《元也里可温考》引元文宗时修的《至顺镇江志》关于户口的记载上这样说:
“侨寓户三千八百四十五:蒙古二十九、畏兀儿一十四、回回五十九、也里可温二十三……”
(以上部分资料,引自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先生的研究成果)
3、根据以上资料可见,从元初开始,“回回”一词,就专指那些跟随蒙古军队从西亚和中亚迁来中国的伊斯兰教教徒,这些人称为“色目人”,分居于全国各地,帮蒙古族治理国家。
《开封犹太人》出炉后五百年来的许多中外学人,他们把之前中国历史没有记载的原因,解释为中国汉人分不清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区别,因此,也把犹太人当做了伊斯兰教徒,都称为“回回”,因此,也就没有专门记载犹太人。
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
诚然,退万步说,就算元朝时候有犹太人在中国,中国人淡漠于宗教,分不出二者之间的区别,但是,那些同时代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们,难道他们也认不出他们的这些千年宿敌吗?不要忘了,在元朝时候,这些帮助蒙古人掌管政权的“色目人”,他们大权在握,他们还会容忍这些因背叛真主而遭到真主弃绝的“恶魔同党”(《古兰经》(2﹕14) ),让他们跟自己一起都叫做“回回”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陈垣先生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将《元史》中的“术忽回回”指向犹太人,以此证明“开封犹太人”从宋延续到金,从金延续到元,再从元延续到明清,这是十分不准确的,完全是“大胆假设,大胆求证”。
陈垣考据出来的“开封犹太人”的大量证明,都是1601年甚至1663年以后的证明,但是,他却用这些证据去证明1663年甚至1601年之前的历史,这岂不是成了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与此类似的荒唐结论:
A、1949年以后,新中国有了国旗、国徽等大量材料,这些材料证明了新中国的存在;
B、新中国以前,中国社会也存在过国旗、国徽;
C、所以,新中国早在191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非常遗憾地说,陈垣先生在他的那篇《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完全是在别人设定好的范围内(比如在1601年甚至1663年之后)鹦鹉学舌,望文生义,为某个结论而去强行臆造证据,想当然地到处进行所谓的“考证”,其结果却是却是一无考二无证,这种治学方法是极不严谨的,其结果就是无意间帮助利玛窦这些文化大盗当了一回傻不啦叽的吹鼓手。
惜哉。
综上,“开封犹太人”的支持者们,找到了一些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少得可怜的所谓证据,更是从反面证明了,“开封犹太人”只是欧洲耶稣会杜撰出来的一段子虚乌有的伪史。
第七个问题:“开封犹太人”在“留遗汴梁”之后,为何过那么多年才来建设他们极度重视的精神家园“犹太教堂”?
假设“开封犹太人”就是“僧你尾尼”那批人,他们在宋真宗咸平元年到达开封,住了下来,而到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才开始建寺,而时间已经过去了165年。退一步说,“开封犹太人”是北宋灭亡前十年来到开封的,那他们建寺也是在37年以后了。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和律法,犹太族群必须具备神文、神职和神所,会堂不仅是成年男人必须一天祈祷三次的地方,而且还是用于公共活动、儿童与成人教育的重要场所,犹太教堂是犹太教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精神殿堂。要是教堂不存在,犹太教教义就无法在浓厚的宗教仪式烘托下进行宣讲,那些年纪尚小的人就会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所吸引,宗教精神就会一代代日渐淡薄,宗教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所以,对于定居下来的犹太人来说,可一日无寓所,但不可一日无教堂。
但那些“开封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晚才给自己建教堂呢?
有人为之辩解说,犹太人初到开封,人生地不熟,买不起地皮,所以,在他们到达开封37—165年之后再来建寺,也情有可原。
那些首批到达开封的犹太人,他们很穷吗?
正好相反。“留遗汴梁”四个字恰恰说明,这批犹太人属于当时的“豪华旅游天团”。
1、这批犹太人有一千人左右;
2、这批犹太人留在了开封府,不管是租房也好、自建房也好,无论是在内城,还是在外城,即使是在新宋门、南熏门、万胜门和新酸枣门外的城乡结合部,他们全部都住在了大宋的首都东京。
今天,如果有一千多人来到北京,最后都在五六环以内买房定居,那么,这一千多人必定全都是山西来的煤老板。
闲聊一下,北宋时候,东京开封的房价有多贵?
宋真宗时候的宰相寇准说过:“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谨则住僧舍或僦居。”僦居就是租房子,不是住僧舍就是租房子。
宋仁宗时期的宰相韩琦曾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与韩琦同时代的欧阳修,在京城当官时就租住的小破屋,后来回忆时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里感怀道:“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晚年的时候,欧阳修终于在十八线城市安徽阜阳买了几处房子,也算告别了“房奴”的生活。
经欧阳修提携的苏轼也好不到哪去,他在首都为官多年,经常借住在同乡范镇家中,一直也没能在京城买上尺椽片瓦,以至于给儿子苏迈办喜事,请同僚吃饭都得借范镇的房子。后来,范镇死的时候,苏东坡还写了一幅挽联:“高斋留寓宿,旅食正萧然”,表达了对范镇留宿的感谢之情。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做官要比他成功得多,不过也买不起开封的房子,直到七十岁时才在许昌置办了一份不动产。苏辙不由得感慨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
大学士陶榖用“四邻局塞,半空架板,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形容了当时的“蜗居”境况。“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可想而知,建筑面积有多小,居然连张床都放不下,只能睡箱笼。
为啥开封房子这么贵?开封是北宋的首都,在当时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城市结构早已突破了唐代长安“坊市”式的城市格局,进而转向居民区与市场混一的城市制度。作为首都的开封,其城市化、商业化的速度与程度都史无前例。随着人口增多多,城市空间紧俏,地产市场也就日益火爆起来。东京房屋贵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当时的政府出台限购法案了。一是宋真宗发了道圣旨:“禁内外臣市官田宅”;二是宋仁宗又发了道圣旨:“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前面是说无论中央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不能购买公房。后面是说现任京官最多只能拥有一套住宅,禁止在首都购买第二套房。由此,当时开封房价有多贵?不用说数字,你根据今天的“北上广深”大概也能猜到了吧。
(北宋开封“房价”为何那么贵http://mini.eastday/mobile/180201184238057.html#)
(在这里我们又不妨脑补一下:
镜头一:一个肥硕的房东妇人双手叉腰站在垂花门下,对着抄手游廊里的一群奴仆喊道:“来人啦,寇准宰相他不交房租,把行李全部给我扔出去!”
镜头二:寇准站在一大堆箱笼被褥中,满脸无奈地说道:“夫人,这不怪我呀,朝廷把钱拿去当岁币交给萧太后了,这个月发工资大家都推迟了呀!”
镜头三:这时,参知政事温仲舒火急火燎地跑进院门,嘴里一迭声地喊着:“寇老西,借我二十两银子,房东扣着我的官帽不还,要不我明天怎么上朝呀!”)
因此,根据上面的信息,我们完全可以就可以得出结论,那么有钱的一大群犹太人,而且又那么热爱自己的宗教,他们拖了37—165年之后才来建设他们的“犹太教堂”,其中没有别的原因,这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第八个问题:“开封犹太人”是怎么逃过1233年蒙金血战的?
1234年,金国灭亡,南宋朝廷实施“端平入洛”行动,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宋将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然而,此时的汴京已再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梦幻般的繁华开封,除了大相国寺和宫城以外,井市焚毁,到处都只是荆棘丛中的断壁残垣和累累白骨,昔日超过百万之数的庞大人口,就只剩下了六百多投降了蒙古人的金国士兵,而居民就仅有一千多户人家,估计多是这些士兵的家属。
周密在《齐东野语》卷五中说道:“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
那么,那些“开封犹太人”呢,他们到哪里去了?
有人说道:“这个问题问得太愚蠢。既然战争来了,犹太人必然会跟所有开封人一起逃到城外,打完仗后,自然也就返回家去了。就算他们的犹太教堂烧毁了,他们不是在1279年又重修修建了吗?”
非也。
今天的人类,根本无法想象宋、蒙、金战争的那种炼狱一般的残酷。
自从1214年金国迁都汴京之后,蒙金两国就在中原一带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互相掘开黄河来淹没对方,时间几乎长达20年,到金国灭亡之时,整个中原地区(包括整个河南与河北、山西、淮北、湖北的部分地区)都几乎已经变成了无人区,不管是蒙古军队还是宋朝军队,都根本无法通过中原地区,原因很简单:无人居住,也就无法筹集粮食(说穿了,就是抢不到粮食)。
据《宋史·赵葵传》载:“端平元年,朝议收复三京,葵上疏请出战,乃授权兵部尚书等。时盛暑行师,汴堤破决,水潦泛溢,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
1232年,据《元史》记载:“睿宗(即拖雷)与金人战于三峰山,大破之。诏塔察儿等进围汴城。”随后,金哀宗突围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随后又逃往蔡州(今湖北枣阳西南)。1233年9月,蒙古军已经占领金国大部国土,都元帅塔察儿围攻金哀宗固守的蔡州,被金军屡败于城下,于是,蒙古军分筑长垒,死死围住了金哀宗,不得让其逃窜至别处。当其时,蒙古军队早已断粮,很多人挖掘尸体以食,后竟相活食金国百姓。蒙古军由于无法取胜,于是派使者邀请宋廷联合灭金,同时还要求宋军支援蒙古军部分粮食。
1234年正月初二,蔡州城中已经断粮三月,马鞍、皮靴、破鼓尽被煮食,金军以人和牲畜的骨头以及燕子筑巢的泥充饥,又“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到最后,宋将孟珙与蒙将张柔共同进攻蔡州,守城金军将城中的老弱孩童投入大锅,熬成热油,用以浇烫攻城的宋蒙士兵,号称“人油砲”。其惨状让孟珙心中实在不忍,孟珙遂请一名道士进城,劝阻金人野兽一般的暴行。据《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记载:“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说止之。”
通过以上历史背景介绍,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在1233年那年,汴京被蒙古人攻破之后,城中的百姓绝大部分都死于战火与屠杀,就算有少数平民能侥幸逃出城,但也无处可去,因为整个中原地区都成了千里赤地,逃出城的这些平民百姓,最终不是成为路旁的饿殍,就是成为蒙金军队的“两脚羊”。因此,在这种人间地狱之中,“开封犹太人”这种外来族群的生存能力本来就比不上当地百姓,他们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假设说,“开封犹太人”最后大部分都在开封活下来了,并且还重修“古刹清真寺”,那么,这些“开封犹太人”就必须打通以下几道地狱级的关卡:
1、从战火中逃出汴京开封;
2、快速从汴京开封逃到河南南部,并且要在这大片无人区搞到足够的粮食免于饿死;
3、穿过蒙古兵掘黄河河堤而形成的几百里的两淮沼泽区;
4、顺利到达淮南一带的宋军防线,由此逃出生天,劫后余生;
5、又离开相对富庶平安一点的中国南方,返回到蒙古人野蛮统治下的开封,再去重修那座“古刹清真寺”。
6、另外,由于宗教竞争的原因,伊斯兰教自创立的那一天起,就把犹太人当做了夙敌,尽管在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伊斯兰教对犹太人并不像欧洲人那般野蛮残忍,但是,其所作所为也仁慈不到哪里去,所以在整个元代,伊斯兰教徒“色目人”充当着蒙古政权的重要助手,他们还能容忍夙敌在开封建一座“规模很大的犹太教堂”?因此,即使当时真的存在“开封犹太人”,本来就人丁稀少的他们,能够在伊斯兰教徒手下活过整个元朝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除此以外,“开封犹太人”不可能再有第二条生存路线。
由此,从上面所述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来看,“开封犹太人”这个外来族群要逃过1233年的那场战火兵燹,以及安全度过伊斯兰教徒占上风的整个元代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
综合上述内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弘治碑》的碑文记载混乱、前后矛盾,而且只是一个孤例,在丰富翔实的中国史料环境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和其他旁证,所以,完全可以判断其碑文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刻意编造出来的伪作。
本页面二维码
© 版权声明:
本站资讯仅用作展示网友查阅,旨在传播网络正能量及优秀中华文化,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 联系我们 予以删除处理。
其他事宜可 在线留言 ,无需注册且留言内容不在前台显示。
了解本站及如何分享收藏内容请至 关于我们。谢谢您的支持和分享。
猜您会读:
-
 西方史读多了、入迷了,一定会变傻,变成二傻子。 谁若不信,我就举两个“古罗马史”的例子给大家看。 第一个例子。美国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西方史读多了、入迷了,一定会变傻,变成二傻子。 谁若不信,我就举两个“古罗马史”的例子给大家看。 第一个例子。美国学者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 无论古希腊史专家们如何努力地从“学术”高度去拯救,曾经横行一时的“古希腊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之类,都无可收拾地变成了童话、神话或者是茶余饭后的笑话。当然,...
- 基督教是佛教的分支吗?咱们看几副图。图一是欧洲现存最早的耶稣雕像,不但是张亚洲人的脸,他还穿了一副袈裟,看图二唐僧,耶稣袈裟跟唐僧同款。(欧洲现存最早的耶稣雕像)...
- 摘要南京博物院藏《坤舆万国全图》插图本的船舶插图全部悬挂中国特色的万字旗和牙边旗,没有欧洲船舶旗帜。明代中国海舶遍布沧溟宗(今误称太平洋),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
- 《奇器图说》也是伪史论者们经常“考证”的一本古籍,他们认为这本书是王徵所著。被西方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Terrenz)窃取,明朝人发明创造了自行车、自行磨,更有甚者号...
-
Deepseek认为埃及金字塔确实建于古埃及时代,不是近代人建造的
这几天经常看到关于质疑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年代问题,就想起无所不能的Deepseek,试着问问它怎么回答。问Deepseek:有人说埃及金字塔是近代人造的,但是我觉得金字塔里那么丰富的... -
傻子伪造的古希腊海战、海洋文明、地中海文明圈,被精英们当做高端知识
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因此,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成就了古希腊的科技文明、工商业文明、民主与开放的政治文明,进而成就了希腊帝国、希腊化,最终成就了西方文明。... - 这些年来搞西史辨伪,我经常十分疑惑:为什么有些人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我们,而且连生活常识、科技常识都不管不顾?为什么有些人在反对我们的时候,连脸都不要,总是要靠...
- 西史辨伪为什么总要揭露满清历史?因为西方伪史的总根源就是满清。现在的人们有一个误解,以为华夏古代是愚昧而生产力落后的,这是满清愚民华夏后的刻板印象。明朝军队的火器...
- 我们现在看到的《明实录》很可能被美国动了手脚。如今看到的明实录是民国时期根据红格本明实录重修的,红格本明实录据说是清朝明史馆的手抄本,最具权威。民国史馆决定以红格...
- 时至今日西方还在编造伪史,2023年7月10日,美国、加拿大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发现了一幅老虎追逐山羊得马赛克画(下图),年代在西元400年,距今1600年。发现的位置是在以色列一...
-

占豪丨华为把美国心态干崩了!中国大喜事让西方大失所望,决定对华复制乌克兰模式!
美国心态要被中国干崩了!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2018年发起对华贸易战,结果却是美国草草收场罢战。拜登政府本想上台后尽快取消特朗普强加给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结... -
 202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京东诉阿里“二选一”案有了一审结果。根据“京东黑板报”发布《关于京东诉阿里巴巴“二选一”案一审胜诉的声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
2023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京东诉阿里“二选一”案有了一审结果。根据“京东黑板报”发布《关于京东诉阿里巴巴“二选一”案一审胜诉的声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 - 在湖北省大悟县城关镇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内,矗立着鄂豫边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正面向西,镌刻着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亲笔题词:“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

湖南千万富翁被儿子送进精神病院事件:一场亲情与利益的“罗生门”
来源:海报新闻近日,湖南张家界市“千万富翁罗某忠在与儿子争执后被送精神病院”一事在网上引发热议。一方面,罗某忠姐妹们和媒体讲述“营救”罗某忠的经历;另一方面,罗某... - 因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的离世,随之而来农夫山泉就开始不断陷入争议之中。从香港上市公司农夫山泉公司是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外国离岸公司,相比注册地在中国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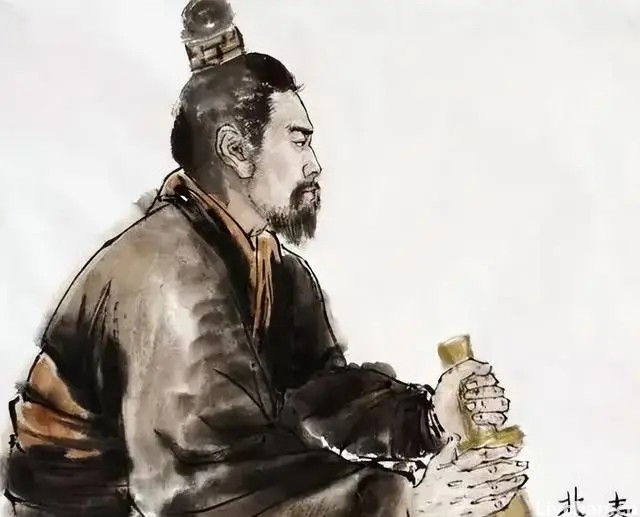 秦朝末年,楚齐等六国后裔与豪杰纷纷起兵反秦。除了燕国王室后裔因刺杀秦始皇而被灭族外,其他五国后裔纷纷复国称王。但除了齐国外,其他四国王室后裔基本上都是被人拥立的傀...
秦朝末年,楚齐等六国后裔与豪杰纷纷起兵反秦。除了燕国王室后裔因刺杀秦始皇而被灭族外,其他五国后裔纷纷复国称王。但除了齐国外,其他四国王室后裔基本上都是被人拥立的傀... - 转自大河报博览在亲人逝去之后,他的家族后辈会为他立一座碑,并在碑石上刻上追悼的话语。在去墓园祭拜时,我们常常会在墓碑上看到“故”“显”“考”“妣”等字眼,你知道这...
-

外蒙古独立始末及蒋经国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涉及外蒙古独立细节的回忆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代表王世杰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迫使国民政府坐到谈判桌前,和苏联商议解决外蒙问题的,还是国民党自...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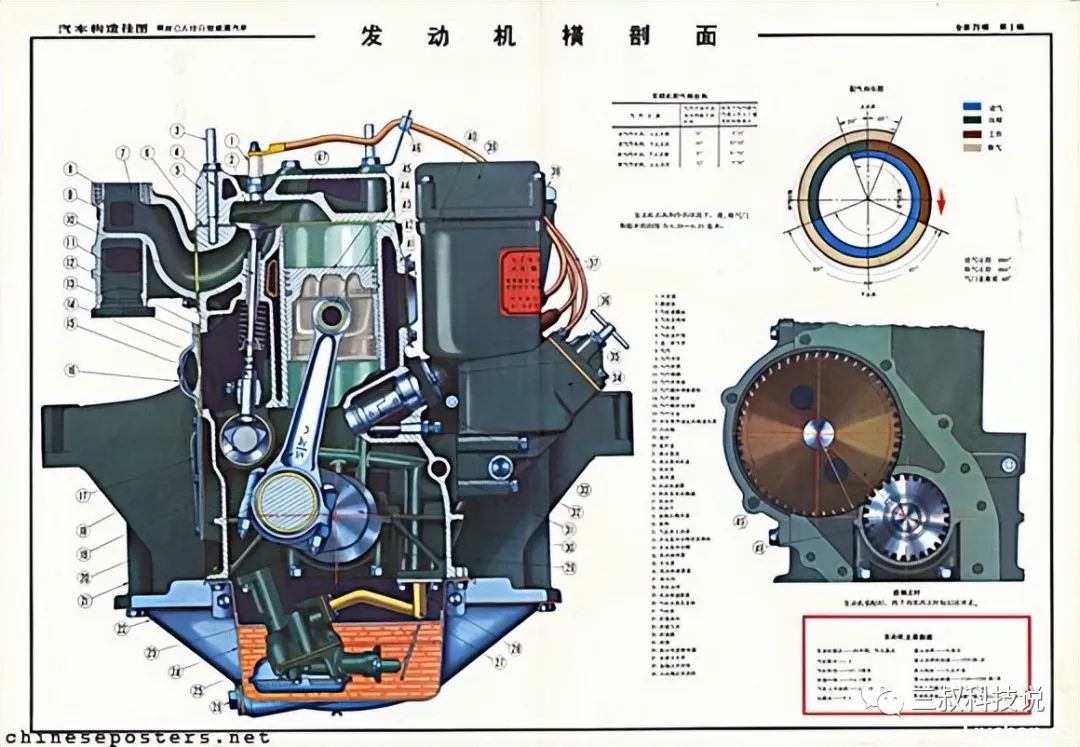
华为迎来“最重量级”合作者,“共和国长子”的信任:灵魂交给自家人
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长6.67、车宽2.46、自重3.9吨。见过这个大家伙的,估计都老了吧。小时候经常在不算宽的马路上见到,如今想再看估计要去博物馆了。“共和国长子”1953年6月... - 2024年12月,尘肺病晚期患者高春现,通过“尘肺病患者救助群”,联系到了曾“开胸验肺”的张海超。昏暗房间里充斥着制氧机运转的呼呼声。“我…我不治了…没意义…你…好好的...